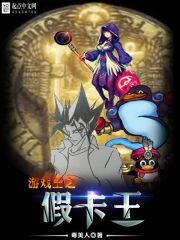危险游戏-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宁奕从自己带的果篮里挑了两个又大又红的蛇果,一个抛给床上抿嘴的人:“吃苹果啦,平平安安。”他笑着,率先啃了一口。
男孩看他吃得香,也小口咬起来:“好甜。”
见他还用眼睛的余光瞟空碗里的酱汁,宁奕问他:“除了那个,还想吃什么?”
男孩想了想:“师兄,我想吃一笼大翠楼的虾饺。”
咽下满嘴的酸涩,宁奕如同个宠爱弟弟的阔豪大哥:“十笼,等你出院,我们就去。”
男孩得了许诺,兴高采烈地展开眉头:“好!”
他笑得太开心,嘴角高高弯扬,左脸上百足蜈蚣般的紫色缝合疤都似活了一样,蠕动着隐约要将皮肤撑破爬将出来,十分恶心。
出了病房,刚才派药的护士小姐做完事,靠在护士台前和另一个馄饨帽咬耳朵。
“真是可惜,年纪轻轻,那么好一张脸。”
“差点脾脏破裂,有命就不错了。”
“听说他是UC(undercover:卧底),好大风险的。”
“所以我就说咯,不想守寡,嫁谁啊都不要嫁给差佬。”
“他伤成那样,以后不能再当UC了吧。”
“创面那么大,怎么当啊,植皮都没用了啦。”
食了酸苹果的余威泛上来,好像雨后涨水的暗沟,咕咚咕咚涌出头,宁奕难受得作呕。
探病的兄弟陆陆续续散了,门一会儿闪一会儿关,很快就空得只剩下孤坐的男孩。
他呆呆坐了一会儿,问隔壁床的病友:“不好意思,你有镜子吗?”
他们这间房的设施不差,但卫浴里没有安镜子。
“有啊。”同样穿病号服的人递过一面仪容镜。
伸到一半的手滞了滞:“谢谢,还是算了。”
宁奕一拳击在墙上,白刷刷的墙皮,抖下一层粉齑。
那夜恍惚如梦,关泽脩救下他,却没拦住一脚油门到底的飞车,才害了男孩。
听曾文浩说,他很勇敢,撞破车窗引来巡逻师兄的注意,可到底赔上好模样。
车轮在山林老道中飞驰,惊飞一群枝桠上栖着的鸟。
太阳在密密匝匝的树桠间播落零碎的光,木结构的豪宅落地的大窗上像贴了层跳跃的金箔。
举头,杉树高高的树桠在头顶交错,切割阳光,像盘在男孩开朗笑脸上丑陋的疤。
再回到山庄,再叩响手中铜制的门把,确实,一些事,远没有他想得那么难。
古旧的门把,并不如现代的电子门铃好使,隔了很久才有人应门。
开门的男人,今天也是极俊美的。
戗驳领对条的白色小羊驼西装,牛角双粒扣,他的身形极好,东方人很难驾驭的款型穿在他身上恰显宽肩窄腰,今天他没系领带,淡钢蓝的帝国衬衫只以一枚金色的领针装饰,却是优雅。
宁奕看他,像看神祇:“关泽脩,我们的赌,还算不算?”
他像个冒失的少年,清澈的眼睛一眨不眨,握着拳头和他对视,笔直的身姿是一种坚毅倔强。
关泽脩没有马上回答他,甚至没有让身请他进屋。
门槛楚河汉界一样隔开两个人,他们各执一方,不进不退。
没等到男人的回答,倒被别人抢了先:“门口是谁啊?”屋里一丛清癯的阴影出现在关泽脩身后,没见着人,先是一只白到刺眼的手,轻巧地搭上男人的肩膀。
丹凤眼的清俊男子在阴影中探出半边身子,薄眼皮拨了拨,往门外头的宁奕身上眈了一眼:“关少的客?”倒听不出多少情绪,但关泽脩否认得快:“不是,他就走。”
冲宁奕客气地点点头,白莲手从肩头滑下去:“二位说话,我回楼上房里等你。”宁奕再不懂,也听出其中意味。
“你的……客人?”话问得磕磕巴巴,脑子里过了许多词,一开口,宁奕还是犹豫了。
“啊。”关泽脩对他的第一句话,一个字,浅浅一声冷漠的平调。
斑驳的树荫藏不住脸上的表情,宁奕抿了唇,突然间有点不知所措。
刚才清俊男人看起来没什么没什么威势,却有种不可方物的贵气,宁奕是知道的,这个城里不少权贵表面山清水秀,其实人后日子身负重轭,常人眼里不正常的受虐癖,倒成了他们最好的放松。
而关泽脩,靠的正是这个吃饭。
“抱歉,宁警官。”似乎不愿多耽搁,关泽脩摆出送客的姿态,“今天我有些不方便,如果宁警官不着急的话,我们的事,改日再谈。”
这是眼下最好的结果,关泽脩没有一口拒绝他,他还可以适时收了傻气择日再来。
可是今天他做不到。
反手绊住将阖的门,宁奕盯着关泽脩:“那个赌约?还算么?”颤颤的声音,几乎是在求他。
却没能打动铁石心肠的人:“我以为,我们两个打的赌,早就已经作废了。”
“要我怎么做?怎么做你才肯帮我?”宁奕不甘心,百足的蜈蚣不仅爬在男孩脸上,也爬到他心上,利剪撕了绫罗,白墙生了罅隙,到这一步,他已经无法回头,“关泽脩,帮帮我,璀璨之星的下落,我一定要找到。”
睫毛阖张,男人笑了:“怎么做都可以,我相信宁警官自有方法,完成任务。”
山中天气多变化,前一刻还阳光出云,后一秒起了风,大片的云和湿气拢近来,温度霎时降了好几度。
宁奕守在机车旁,没走,直到松枝上松鼠啃落一颗松塔落在鞋跟前的湿泥上,哈出的气儿在黯淡下来的密林里飞出几道白烟,车头灯照亮空气中乱舞如流萤的尘粒,往山下开,他才搓了搓冻僵的双手,走向山庄。
没敲门,登着房子一侧的排水管,宁奕攀了几脚,翻身跨进二楼阳台。
房间里没开灯,只有水花声哗哗传来的浴室内亮着一点樱草色的淡黄。
约莫有一刻功夫,水声停了,关泽脩没穿衣,长浴巾擦着湿发开门走出来。
背光,床上隆起一团黑影。
漫进屋里的月光勾描一具线条精干利落的男性身体,不见夸张的肌肉,紧实漂亮得叫人挪不开眼。
同样寸丝不挂,宁奕双手交叠垂于两腿间,别开灯,他小声,却无比坚定地说。
“愿赌服输,我来履行承诺。”
第08章 (下)
热唇贴过来的时候,肌肉绷得死紧,好像碰在一片润到滑手的脂玉。
关泽脩掐着他的下巴,没让他让:“后悔了?”
是双桀骜的眼睛,哪怕落了窘境,都透着股英气和骄傲。
也不知道谁的呼吸先乱飞,嘴皮上发烫,四瓣唇就磕在了一起。
宁奕像个不会接吻却惯要逞强的在室男,粗糙地占据主动,比起吻,他更急着要作证一桩决心。他的动作是鲁莽的,不带一丝情欲和讨好,连抿着的嘴唇都没张开,只一味用蛮劲啄他。吻法太拙劣,宁奕自己也感觉到,关泽脩纯然无动于衷。他有点恼,肺里缺氧,头昏沉沉的,怎么吻都不得要领,和女人鲜少的接吻经验对付眼前人,掂不上一张废报纸的斤两。更何况,宁奕清楚地知道,此刻和自己唇齿撮磨的人,是和自己一样强壮有力的男人。
这想法一旦窜上来,脖子就往后缩了。才动,后脑上的手按紧了他,一条柔软灵活的东西楔着两瓣唇之间的缝隙探了入来,扫着一排白牙滑过细嫩的牙肉,又往更里头钻摸,戏过舌尖,蛇似的卷过舌苔和上颚,脑子瞬间就被吮麻了,足有五秒钟,宁奕发懵地张着嘴,任凭嘴里那条湿软的舌头放肆地在他口腔了的感敏带品了个遍。
拇指指腹按在唇角上抹去一滴晶莹,气声勾着笑:“悔也晚了。”呼吸粗了,关泽脩重新吻住他,力道大的简直要将他啃进肚子。
临界窒息,宁奕几乎稳不住身子,心脏是块沁饱热欲的海绵,每跳一下,就似一双主宰欲念的手挤压,血管里淌动的只剩本能的依寻,鼻息见偶生的一点细枝末节的轻吟都是干柴在一年蓬的草地上炸开的火星,真是疯透了。
宁奕慌着去推他:“意思意思够了,伸什么舌头!你是GAY么,要不要这么当真?!”
是种厌弃,像躲某场疫病,关泽脩看在眼里,淡声提醒:“你不当真,可文先生会,想要寻回那颗钻石,全取决于你能不能吸引一个GAY。”
“摸过吧。”他虚着眼,很多余的一个问题,宁奕没搭腔,“摸过,就玩给我看。”
宁奕额头的青筋凸起,经络在手背的皮肤下一下一下跳:“你玩我?”
似乎故意放水,关泽脩给了僵直的人一次机会:“还愿赌服输么?”看不见笑,比冬雪压弯枝桠还轻的问询。
月光像枚笔直的银箭斜着射下,撕开黑暗的一隅,映出一双比夜更沉的深邃眼眸。
宁奕闭上眼,无法想象仅是多了一个观众,手里的感觉就毁天灭地的鲜明,好像头一次打手枪,他张了嘴,泄出一丝痛苦中满含快感的呻吟。
并不满意似的,屁股被人啪啪扇响:“快一点,这么磨蹭,还是你就爱有人看着?”
拇指微微粗糙的指节抵住亮晶晶的马眼逆时针揉了揉,宁奕的哼声倏地拔高,寻不到一丝赘肉的小腹收缩出利落漂亮的肌肉,湿了关泽脩一手掌。脏都脏了,所幸抓起宁奕的脚踝把人往怀里带,腿架着腿,枪头对枪头,肉紧贴肉,四只手握到一起。
耳边是宁奕低吟的哼声,有一调没一调的,他偏嫌不够,唇皮虚吻脖侧绷紧的线条啄,在皮肤上留下一层绒绒的酥痒,酸到耳根子里:“别光顾着自己,也摸摸我的……”语毕,也不待宁奕反应,直接抓紧湿软的指头撸捻揉弄,两条活龙同时在手里醒转,耀武扬威地缠着,竞斗,要不够的从彼此身上找快活。
宁奕的东西很快就涨红,憋大了足足一圈,战抖个不停:“呃……”他仰了脖子,嗓子眼里叹出一声绵长的气息,射了。
关泽脩玩着他喷在自己下腹的白精:“宁警官,多久没弄了,你的东西可真不少……”
黏黏叽叽的浊液声滑溜溜的,宁奕红着一张脸,狠狠瞪他:“够了,我已经照你说的做了。”
呼吸还没喘匀,后背就给人一压,头冲下,鼻尖堪堪顶到一个大家伙,烫的,发热。
样子俊雅不可言的男人,底下的玩意儿却生得偌大剽悍,刚才只是摸着觉大,这会儿近到眼前,宁奕都吓了一跳,就算在雄性扎堆袒胸比鸟的警校浴室,他也没见过这么壮的东西,只是半勃,就是一副要人命的尺寸。
将他的惊讶悉收眼底,关泽脩低声笑了:“这么看着,没见过?”
用狠力气搓了搓鼻子,宁奕甩开后背上的手腕子:“见过人的,没见过驴的。”
这句话把关泽脩逗笑得更厉害了,腹肌颤抖,底下的东西也跟着晃:“不光让你见,还叫你碰。”
他大大方方张开腿,抓过宁奕的手往那柄枪上按,掌心最软的那点皮肉贴着耻毛下更软的活肉,指尖游过的地方,阳茎上的筋脉都争相搏动了。宁奕的手往后使劲,他缩了,明明摸的是别人的东西,却比给自个儿撸还羞于启齿。
关泽脩虚着眼享受他眉角眼底的青涩,作弄人地催促:“你爽完了,我还远着呢。”
轻飘飘的口气,火辣辣扇脸,宁奕往那根粗长的玩意儿上溜了一眼,张手,包住了它。像给自己自慰一般,由下往上,从头到底,一点点捋,一寸寸搓揉。他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穿防爆服拆弹都没有这般小心谨慎,给另一个男人打,他做得近乎仔细。
可关泽脩扣着他的手腕,顺着湿滑的阴茎退开,五指拔过鹅卵大的龟头,湿哒哒啵的一声。
“宁奕。”唤他名字的声音带电,关泽脩沙哑低沉的嗓子要求,“用嘴。”
五指在暗处咯咯拧紧,就算看了,摸了,弄了,也不代表他有勇气像个男娼似的给人含。
“宁奕,我问过你的。”
关泽脩恢复了初见的温柔,宁奕迷离中听闻他给了四个字。
“愿赌服输。”
在森林里蹲着,在树与树之间辗转取暖的每一步,都没有这一刻从脚底跟上蹿上一股凉气将灵魂冻住。
他为什么来这里?
为什么把自己送到男人床上?
凭什么放任他做到这一步还妄图停下?
口腔在高潮的喘息中干燥,他吞咽下口水润了润唇皮,弯塌下腰,后背绷直的线条像只臣服的猎豹优美,试探着,难为情的,睫毛颤栗如蜂鸟悬空的翼,认下这场较量。
第一次做这个,他根本不知道要收牙,动作也是单调的一浅一深,舌头死了一样无用,可关泽脩还是被伺候舒服了,懒洋洋哼出声。
捏着宁奕烫红的耳根,他像把玩一颗琉璃珠,鼓励用功的人:“很好……嗯……你看,一旦身体臣服于意志,一切也就不那么困难了……:浓重的情欲和喘息,啧啧的嘬嘴声交织,黑色的眼眸宛如盯住心爱的猎物。
关泽脩发出长长一声情喘,“你做的,棒极了……”
第09章 (上)
那夜之后,他们的关系恢复如常。
宁奕隔天收拾了简单的衣物搬入山庄,住进远离二楼主卧的西侧的一间客房,上楼时,几乎不会经过那个房间,关泽脩的房间。
关泽脩也没再做出任何一点出格的举动,当晚的荒唐事仿佛随清晨洒在床头的一缕光一起蒸发得无影无踪,穿起考究的衣服,别上精致的袖扣,他又成为一个体面优雅的绅士。
只是宁奕时常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