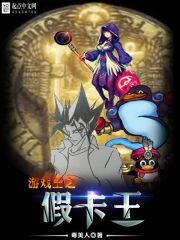危险游戏-第2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相比宁奕的悲伤,关泽脩平静得多,往事对他来说像潭盘不活的死水,宁奕想看,他揭开就是了:“还有什么想知道的?”他问他,“也许错过这次,我就不会再说了。”半真半假开玩笑。
宁奕呼吸紊乱,他极力压制战栗的肩膀,想让自己看起来无谓一些,但嗓音一出来,还是哽塞的。他在拔一根横在关泽脩心尖上的刺,可不这么做,他又无法看清他的真心:“林少朗为什么要跳楼?”
“这个问题,我回答过你了。”关泽脩收起笑容,静静看着宁奕,“他向我要一件我无法给他的东西,我拿不出来,所以文荣给了他。”
“是什么?”宁奕颤颤去迎他。
空气突然凝结,心跳大得好像鼓在耳膜上,花束绊开他们,令宁奕看不真,只依稀听到男人沙哑的嗓子,淡淡的妥协:“你知道的。”关泽脩说,“我不爱他,他想要的真心,我给不了他。”
像着了魔一样,宁奕居然被蛊惑着,差点脱口而出,那你的真心呢?他在哪里?
“那你爱谁?”宁奕抬起头,用比他更低哑的语音,问他。
“你要是还不知道,就说明你还不想知道。”关泽脩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自白色的蝴蝶兰后露出面容:“你的问题问完了,轮到我了。”他弹了弹桌上牛皮纸袋包裹的酒瓶,宁奕的眼中映入一张笑脸,“换个地方,我们谈谈昨晚的事。”
软皮质的手铐穿过床的四角,蜜色的四肢被呈一个大字型,牢牢固定在床上。
从起居室到卧房,宁奕不是没反抗过,拳头挥了,脚也踹了,丝绸的睡衣像片花瓣一样被剥离,他忘记了一切格斗的身法,想从男人手下赢得一招半式,但最终,还是被像一个陈列品一样展开在凌乱的白色床单。
“你做什么?!”宁奕还在无用地挣扎,“快放开我!”
“突然想起来,我们很久没有一起喝酒了。”关泽脩背对着宁奕,打开那瓶冰镇多时的酒,“来一杯好吗?”
“你松开我!你想喝,我陪你,用不着这样!”一条红的惊心的signalwhips指挥鞭横在眼前,阻止了宁奕的动作。
“别动,让我看看你的伤。”红色的马鞭,沿着宁奕的小腿,游上他腿裆破了皮的伤,旗形的鞭头绕着那块新痂打转,不自知地刮过胯下颤巍巍的一小团软肉,引来手铐猛地铮动,“别碰!”宁奕绷紧了小腹往弹性的床垫里缩,他快要被逼疯了。
“这会儿怕了?你剁文荣老二的时候,可不像是个会认怂的。”鞭子离了那处敏锐,改了上手,他按摩似的搓揉,那小小的肉团很快就充了有两倍大,“数数,你添了多少道伤口?”红鞭执在手里,沿胯骨往小腹去,在那里轻轻拍了拍,吃了文荣一脚的皮肉经过一夜泛出淤青,紫的红的一大片,像上了彩,关泽脩不认同的蹙眉,“当牛郎的人,除了爱惜一张漂亮的脸蛋,身上每一处皮肤都看得很重。有GV男星为了不在身上留下疤痕,即使阑尾炎也宁可选择保守疗法,你却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红鞭反手就是一道赤电,火辣辣地撂过娇嫩的乳‘头,横上胸口,宁奕疼得绷紧肌肉,红像朱砂洇透数层宣纸,一点点渗出来,关泽脩一点没克制力道,只一鞭就见了血。
宁奕仓促地啊了一声,四肢拉直又耷拉,无力地喘着气,眼睛湿了,无焦地眨。
“他碰你这儿了吗?”关泽脩重新包住畏缩的小小肉团,色色地搓,“像这样弄过了吗?”
是疼和刺激,一上一下磨折他,宁奕的喉咙里不断挤压出破裂的叫喊,像上刑,像过电,像恐惧,又像怕上了瘾的大喊:“没有!他没有!没有可以了吧!”宁奕大声否认了三遍,以向关泽脩证明他真的没干。他不想露怯,可更不想像现在这幅样子被禁锢和玩弄。
关泽脩不信任他,手抵在茎眼上,用力捋了把,宁奕从屁股到腿,打着抖:“他真的没有,我不让,没人可以碰我……”说第四次的时候,宁奕已经办虚脱。
关泽脩抓过酒瓶往下倒,芳馥的酒一点点往他渗血的伤口,青紫的腹肌,左右点头的性器上浇:“考考你本事,用你的耳朵、鼻子、直觉,告诉我这款酒的芳名?答对了,我放了你。”
冰凉的液体顺肌肉拉抻的纹理淌落,分不清是疼是辱,宁奕同男人商量:“先放开我,只是品酒的话,我会配合的。”
又是一鞭子,贴着大腿打在床上:“你不信我?”黑色的眼睛危险地眯起来,“宁奕,你还不明白么?这不是惩罚,也不是游戏,如果你相信我不会伤害你,就回答我……”
第三鞭落下耳根前,宁奕仓促地吼出:“是唐佩里侬香槟王!”
男人笑了,红鞭在手上掂了掂:“的确,唐佩里侬的香味独特,浓郁而强烈。但你太不细心了,忽略了她香味中混合而又沉淀的复杂性。”关泽脩扔开鞭子,举起酒杯,“答不上来不要紧?我允许你尝一口?”他含了一口酒到嘴中,虎口卡住宁奕的下颚,嘴对嘴的渡到他口里。
“咳咳……”宁奕被呛得咳嗽不止,来不及咽下的酒,顺着唇角滑下脖子,留下一道晶莹莹的痕迹,关泽脩舔过那层水光,双手搭上他的两胯,向后,将绷出形状的两瓣紧致屁股分开,狠狠往中央插入一根手指:“宁奕,我想上你……”
身体好像被楔入一枚长钉,滚烫的,撕裂开,直嵌最深处。伴随可怕的搅动,浑身的肌肉全都拉抻到痉挛:“关泽脩!”宁奕嘶吼,“你说过不会逼我!”
“我是答应过你,但别人没有。”手指已经增加到两根,有酒液做润滑,紧涩的窄道敞开一个小口,吮嘬般收缩,“如果是文荣,你猜他接下来会怎么做?”拉链声磨着耳朵,一把钢硬的东西顶在他的肛门上,关泽脩不急着进去,滚烫的肉头堵住瑟缩的入口,画圆似的磨蹭,关泽脩吁了一口气,“我得提醒你,我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
宁奕哭泣了,他甩着头,声音从肺里拔高:“滴金酒庄的贵腐甜白,文先生最喜欢的酒!!!”
阴茎恋恋不舍地从缩成小点的后’穴上挪开:“对了。”抱着遗憾的口吻,男人调侃道,“真希望你答不上来。”可转而,他又将头贴在宁奕砰砰跳的心口,轻声要求,“答应我,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信我。”
另一边,邢砚溪照例在开业前盘点酒库的酒,那瓶昂贵的唐培里侬还在,乖乖待在酒架上。他笑笑,怪自己的神经兮兮,不过马上,他就屈服于自己的第六直觉,离香槟王不远的位置上亮着一束灯光,那支他花大价钱拍下的贵腐甜白酒,早已不知所踪。
第22章 (上)
穿黑马甲小领结,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领班笑意吟吟冲宁奕点头:“关少,知道你带朋友来吃饭,给你安排的老位置。”他在前头引路,将他们请到一个光线好,又清净的角落。
关泽脩貌似是这里的常客,也不须菜单,直接问:“今天的花蟹怎么样?”
领班用两手比了个手势:“下午刚到的蟹王,这么大,满黄。”了解男人的喜好,他又推荐,“海方脷也不错,一共到了两尾。”
“就要这两个,炒一道豆苗。”他看向宁奕,片刻后,“再加一份雪糕,现在上。”
鱼和蟹都是活的,现点现做,需要时间,但自制的雪糕一入了口,宁奕的眉头就舒展了,嘴角向上,眼睛亮晶晶的活络。
“这是什么?”勺子不断送进嘴里,要不是怕吃相太难看,宁奕都想捧起碗,他是舍不得碗底那一层融化的雪白。
“枸杞桂花雪糕。”关泽脩喜欢他现在这个表情,不锋利,不敌对,有点小小的天真,和从骨子里流出来的欣喜,关泽脩将凉了一会儿的热茶递给宁奕,氤氲清香,刚好适合入口的温度,“喜欢的话,一会儿可以再吃一个,但现在不行。”
宁奕撇撇嘴,收起那把眼神往墙上的挂画上瞟,一双腿也不动声色地往后挪,他有点负气,为轻易被对方看透心思,更多的是尴尬,隅席之地,白色的桌布盖上小小的四方桌,俩个男人皆是手长脚长,也不知道谁先挪动,桌布盖着的地方,他们的膝盖贴碰到一起。
宁奕犯了个错误,到底上了关泽脩的套,这爿小店,他原本不应该来的。
可关泽脩无声的邀请太犯规,仿佛宁奕不答应,他就会一直用一种稠密的,祈盼的目光长久地凝视他。宁奕甚至错乱地想,他并不急着获求一个答复,或许这种凝望本身就是他的目的。
为了不让他如愿,宁奕坐到了这里。可看见男人那张笑脸,宁奕又恍然,似乎还是他赢了。
菜陆续上齐,都是清淡简单的做法,但很考究功夫。尤其是鸡油花雕蒸的红壳大花蟹,蟹盖一掀,橘红的膏油滚落金汤里,蟹黄像橘子瓣一样鼓突饱满。
宁奕是真饿透了,这几天在酒店,他就没有好好吃过一顿像样的饭,关泽脩以养伤为由,叫的客房服务尽是清粥小菜,他倒是吃得安然,可委屈了宁奕。
宁奕狼吞虎咽的时候,关泽脩认真对待起那只生猛花蟹,他拆蟹的样子很优雅,不徐不疾,修长的手指好像在进行一场预先演练过的表演,只为一朝用精巧的技艺留住人艳羡的目光。
他做到了,宁奕看痴了,脸颊微微的红。
那双手像个弹琴的,也为他料理过食物,更在他身上做过恶。受鞭子那天夜里,正是这双修长的手指,铁钉似的往他身体里钻,他哭着求饶,头胡乱地摇,不假思索地承诺了一堆昏话,才阻止了更可怕的进犯。
男人伏在他身上粗重的喘息,宁奕差点以为他要变卦,但他翻身下床,挺着一杆悍枪,一身整齐的衣衫进了浴室。有水声哗哗的响,先是噼里啪啦打在瓷砖地上,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
雪白晶莹的蟹腿整条码放在蟹盖上,送到宁奕碗里:“在看什么呢?”关泽脩笑着问他。
“没,没看什么。”他盯着他的手指楞了两秒,做贼心虚地挪开眼。
所幸男人没有深究,抽回了手指,一顿饭的时光,吃得倒也舒心。
上了车,关泽脩突然靠近:“你干嘛?!”
宁奕以为他要拉安全带,可手指偏又朝向嘴唇:“别动。”指尖在唇角上摸了摸 ,又在唇珠上捻开,腻腻的,奶油的甜味,“嘴上沾到雪糕都不知道。”
宁奕耳朵一烫,借着扣安全带,挥开他的手:“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你什么时候带我去黑门?”宁奕之所以乖乖养伤,全因为关泽脩承诺,会为他安排一个进入黑门的身份。
手拍在手背上,男人没让,倒是宁奕自己烫伤似的抽回手:“亲我一下。”男人垂着浓丽的睫毛,倒下一片如羽的阴影。 ”什么!”宁奕的背抵在冰凉的车窗上。
关泽脩挑眉,眼底浮上一点光,明亮又狡黠。他戏弄一样揉了揉宁奕的耳垂,当他企图拨开他时,轻轻落了一个吻在宁奕脸上,掠过的感觉像一滴露,还未飘到水面,就被风撵着,散了。
鼻息卷着,掠过那一小块皮肤,底下的热才泛涌,收不住的,如同醒了的火山。
“等你不来,我亲也一样。”男人的笑,似一枝斜柳荡过映满桃红的小潭,几道潋滟的水波,颤颤拨在心间上,“坐好。”赶在宁奕回神发作前,关泽脩发动了汽车,“我们现在就去。”
城市的霓虹也醒来,像返校节舞会上的年轻女郎,誓要将所有好看的颜色都堆上,肆意地在车窗上旋转起舞,瑰丽千千万,宁奕的眼睛却越过斑斓,落在一张寂默的侧脸。
光景是艳的,但不及男人俊美,人群闹哄哄的,更衬显车窗上的面孔,是沙漠上缥缈的海市蜃楼,美好到叫人心动,遥远得令人心碎。
前头的车尾灯亮了,车子逐渐停下,宁奕一个瞬目,再度睁开眼,发现车窗中的人也正看着他。宁奕突然不敢回头,他形容不出这双眼眸中蕴藏的东西是什么,大抵和脸颊上那个吻一样柔软,或许转头就是一片绿洲,可他选择躲避,飞快地看向更远的地方。
前车动了,宁奕松了口气,闭上眼靠进车座里,在下一个红灯时,他错过了关泽脩投向他的,爱恋的目光。
中途,关泽脩特意绕路去了趟酒庄,两瓶顶级的酒王放在黑门灰色大理石质的吧台上,调酒师才不情不愿地赶人,为他们让出两个位置。他给了宁奕一杯马天尼,但给关泽脩的却是两排点燃的B…52:“一口气,我就原谅你。”邢砚溪夹根烟似的夹着一根吸管,送到关泽脩嘴边。
宁奕很难想象,男人露出个痞气的笑容,竟然衔住了:“你就别喝了。”他对宁奕说,“一会儿还得送我回去。”一转眼,五个杯子都空了。
“行了!”第六杯的火焰熄灭前,宁奕夺过来,比喝了一口烧红的刀片好不到哪儿去,从嗓子到胃,无一处不疼,“跟他提,我进黑门的事。”他张开手臂,在男人滑倒时撑住他的身体。
也不知真的假的,关泽脩醉了,倚在宁奕肩膀上:“何必麻烦,你想进黑门不难。”手碰到他的后腰,借力似的,软软贴着。
有酒作怪,宁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