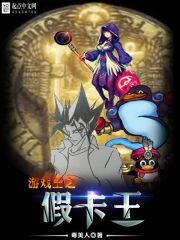爱国者游戏-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瑞安以前从未上过法庭,连行车超速罚款单都从来没有收到过。他的生活平淡无奇。这一点他自己也觉得好笑。杰克周围还有六七个证人。杰克没同他们说话。有人特别告诫过他,互相之间不能交谈,哪怕有一丁点表示,都会引起辩护律师怀疑证人是否都串通好了。起诉方面尽了最大努力要把这件案子当成正确执行法律程序的范例。
对这个案子的审理是在矛盾的背景上进行的。伏击发生后才过了四个星期,而审讯已经着手进行——就英国风格来说,其速度之快实在罕见。安全工作亦无懈可击。严格控制了旁听人数(他们从大楼的那头进来)。但与此同时,案子被严格地掌握为刑事犯罪。没有提到“北爱尔兰解放阵线”这个名称,检察官也一次都没有使用过恐怖分子这个词语。在公开场合,警方回避案子的政治性。两个人死了,这就是一级谋杀——其他没什么可说的。甚至连报纸也持合作态度,渲染被告为单纯的犯罪,而不列为政治犯。瑞安不知道这样一来,同案件有关的政治和情报活动会如何对待。然而没有人提到这些,而且辩护律师说,要是他的委托人是恐怖集团成员的话,他就不辩护了。无论从宣传舆论角度,还是从法庭角度,这都是一起谋杀案。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但人人都心照不宣。瑞安精通法律,他知道律师们是很少关心事实的。裁决更为重要。因此,不必涉及王室,官方就已经对犯罪的动机深信不疑;根本不必也无法去查证活着的同谋,由此也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证词可言。
这不要紧。从报纸的报道看,十分清楚,审讯安排得滴水不漏。整个审讯过程不摄像,而且凯茜不出席作证。加上前天作了证的法医专家,王国政府共有八名证人。瑞安是第二个。此案预定最多审理四天。就象欧文斯在医院对他说的,同那小子没什么好扯的。
“瑞安博士,请随我来。”一位穿短袖衣服系领带的法警走过来,领他从边门走进法庭。一位警察开门后,接过他的计算机,“要亮相了。”瑞安悄悄地对自己说。
伦敦中央刑事法院二号审判庭保持着十九世纪的木结构式样,十分豪华。宽敞的房间里镶嵌了许多坚硬的橡木。在美国,用这么多树木去建造一个房间,会引起山林俱乐部的抗议。然而楼面的实际使用面积却出乎意外地小,简直同他家的餐厅那么一点点,更使他惊讶的是,房间当中也象餐厅似地放着一张桌子。审判席挨着证人席,木头堡垒似地占据了房间中的主要地位,后面有五张高背椅,尊敬的法官先生惠勒坐在其中。他身穿深红色的长袍,挂着深红色的绶带,马鬃制的假长发披散在窄窄的肩头,看上去光彩夺目,象是另一个时代的人。陪审席在瑞安的左边,八位妇女和四位男子坐成两排,脸上都充满期待的神情。瑞安的右边,隔开点距离,便是律师坐的地方。律师身穿黑色长袍,系十八世纪式样的领带,假发稍短一些。这一切形成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宗教气氛,以致当瑞安宣誓的时候,心中稍觉不安。
起诉人是王室的法律顾问威廉·理查兹。他同瑞安差不多年纪,身材高矮胖瘦也差不多。他先问了一些通常要问的事情:诸如姓名,住所,职业,何时到伦敦,来干什么,等等。理查兹显然有一种表演才能,问着问着,就引到枪击问题上去了。瑞安不用去看,就能感觉到听众脸上的兴奋期待之情。
“瑞安博士,您能亲口描述一下接下去发生的事吗?”
杰克不歇气地足足讲了一分钟,脸始终半对着陪审席,他尽量不去看陪审员们的脸色。瑞安感觉到,这个看来古里古怪的地方,登台讲话是让人觉得胆怯。叙述事情经过的时候,他的目光越过陪审员的头顶,盯着橡木镶板。一切都象更新经历了一遍,叙述完后他觉得心跳加快。
“瑞安博士,您能否为我们确认一下您首先攻击的那个人?”
“可以,先生。”瑞安手一指,“就是被告,先生。”
这是瑞安第一次仔细端详他。他名叫肖恩·米勒——照瑞安想来,这个爱尔兰名字毫无特别之处。二十六岁,矮子,纤细,西装领带穿着整齐。瑞安指认的时候,他正朝着旁听席上的某个人,可能是个亲属,在微笑哩。接着他扭过头来:了,瑞安第一次仔细端详了他。瑞安曾经猜测了好几个星期,什么样的人才能筹划和实施这种罪行?他身上缺点儿什么?或者说他身上多了些什么有教养的人所庆幸没有的可怕东西?那张瘦削的、粉刺斑驳的脸完全是普普通通的。米勒完全可以在梅里尔·林奇公司或者其他财团接受行政管理训练。杰克的父亲已经同罪犯打了一辈子交道,但令瑞安困惑不解的是罪犯仍然存在。你为什么与众不同?是什么使你变成了现在这种样子?瑞安想问一问,尽管他知道即使能得到答复,这个问题也仍然存在。然后他盯着米勒的眼睛。他想寻找……诸如生命的火花和人性之类能表明他确实是人的东西。只不过盯了短短的两秒钟,但瑞安却觉得似乎有好几分钟,他看到,那双灰白茫然的眼睛里……
什么也没有。空白一片。杰克开始有点懂了。
“记录在案。”法官大人拖着长音对书记员说道:“证人,确认了被告肖恩·米勒。”
“谢谢,阁下。”理查兹结束了盘问。
瑞安抓紧机会擤了擤鼻子,上星期末他感冒了。
“您不舒服吗,瑞安博士?”法官问道。瑞安这才意识到。
他一直依在木栏杆上。
“请原谅,您——阁下,这石膏筒有点儿麻烦。”
“法警,给证人搬个凳子。”法官命令道。
辩护律师风度蹈朋地站了起来,好象胸有成竹。他叫查尔斯·阿特金森,大家都叫他“红色的查理”,是个嗜好处理激进事件、打暴力官司的律师。据说直到最近他进议会之前,他一直都是为工党效力的,而工党却对他大伤脑筋。
“阁下,可以开始了吗?”他一本正经地对法官说。随后,手拿一页写了字的纸,慢慢地朝瑞安走来。
“瑞安博士——或者得称呼瑞安爵士吧?”
杰克挥挥手,“随您的便,先生。”他满不在乎地说。他们已经提醒过他,说阿特金森是个聪明的家伙。在商业经纪人中,瑞安认识不少聪明的家伙。
“我想,您曾经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尉官吧?”
“是的,先生,您说得对。”
阿特金低头看看手里的笔记,又看看陪审团,“美国海军陆战队可是一帮嗜血成性的家伙啊。”他咕哝道。
“您说什么,先生?嗜血成性?”瑞安问道:“不,先生。据我所知,大多数海军陆战队员是喝啤酒的。”
旁听席上发出一阵轻快的笑声。阿特金森朝瑞安刻薄地、不怀好意地微微一笑。
“请原谅,约翰爵士。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我的意思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以惹是生非而闻名。这肯定是真的吧?”
“海军陆战队是轻步兵部队,专门用来水陆两栖袭击。我们受过良好的训练,但要是彻底了解的话,就会知道它同其他士兵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我们在特别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了专门化的训练而已。”瑞安答道,希望打他个措手不及。
“是袭击部队?”
“是的,先生。大致是这样。”
“那么,您指挥过袭击部队啰”
“是的,先生。”
“别太谦虚啦,瑞安爵士。什么样的人才被挑选去率领这种部队。敢做敢为?果断的?勇敢的?比起一般士兵来,他当然更加具备这些素质啰。”
“事实上,先生,依照《海军陆战队军官指南》的说法,认为军官的首要品质是诚实正直。”瑞安又笑了笑。
阿特金森皱起眉头,事情没朝他想的方向发展。
“那么,他们怎么训练你们的?”阿特金森追问着,不知是生气了还是假装生气了。
理查兹抬头看看瑞安,眼里透出警告的味道。他强调过几次,认为杰克不该同“红查理”争斗。
“不错,有过一些基本的指挥技能训练,教我们如何在战场上带兵打仗。”瑞安答道:“给你一个战术形势,要求你作出反应,如何使用排里的武器,以及如何在较小的范围内配置一个连的火力,如何请求炮火和空中力量的支援……”
“做出反应?”
“是的,先生,这是一部分训练内容。”瑞安注意保持语调的平稳、友好。他象提供消息似的,一面拖长回答,一面想着如何摆脱开去,“我从未经历过任何格斗场面——当然,除了我们现在正在说的那件事——但是我们的指导教师非常清楚地告诉过我们,枪子儿乱飞的时候,是没有思考余地的。你该知道怎么干,而且还得快干——否则你自己的人就要死在你手里。”
“妙极啦,约翰爵士。您受过对突发性刺激作出快速反应的训练,对吧?”
“是这样,先生。”瑞安认为他看见了逼近的伏兵。
“那么,在那次不幸事件中,当爆炸刚开始的时候,您刚才说过您正望着别的方向?”
“是这样,我望的不是爆炸的方向,先生。”
“过了多久您才看见发生的事情的?”
“噢,先生,我刚才说过,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妻子和女儿隐藏起来,然后我再抬头去看。您问这花了多少时间吗?”他翘起头想了想,“至少一秒钟,可能有三秒钟。很抱歉,但如我刚才说的,要回忆这种事情可不容易——我的意思是说,谁也不会随手操着秒表。”
“所以当您最终抬头看时,并没看清直接发生的事情?”
“是的,先生。”好,查理,接着问吧。
“这就是说,您没看见我的委托人在用手枪射击,也没看见他扔手榴弹。”
漂亮,瑞安心想,很奇怪他玩了这么一手。好,他还得玩下去,“不,先生,我刚看见他的时候,他正跑着绕过小轿车,从另外那个人那儿跑过来,从那个已经死了的人那儿——就是拿冲锋枪的那个。转眼问他就跑到了劳斯莱斯轿车的右后方,背对着我,右手拿着手枪,比划着,好象……”
“从您的角度假设,”阿特金森插嘴说:“好象要干什么这会有好几种可能。到底是哪些可能呢?您怎么知道他在那里干什么呢?您没看见他从那辆后来开走了的汽车里出来。您所知道的不过是他可能象您似的,也是个跑去营救的过路人,是吗?”
这么说,杰克有些发楞了。
“假设?不,我认为应称之为判断。要是如您所说,他是跑去营救的话,他就得穿过街道。我怀疑有谁能不论场合如此快速地做出反应,何况那儿还有个端冲锋枪的家伙得让你再考虑考虑哩。另外,我看见他是从那个拿AK47型冲锋枪的人那儿跑过来的。如果他是去营救,为什么反倒从那个家伙身边跑开呢?如果他有枪,为什么又不打他呢?当时我来不及想到这种可能性,现在看来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先生。”
“又是一个推论,约翰爵士。”阿特金森象是在对一个智力低下的小孩说话。
“先生,您问我问题,我尽量回答,而且要说明我的理由。”
“您希望我们相信您这瞬息间的闪念?”阿特金森转过身来看陪审团。
“是的,先生,事情就是这样。”瑞安十分肯定地说:“我的回答就是——事情就是如此。”
“我的委托人从未被拘捕过,也没被指控犯过罪,我想投人告诉过您吧?”
“我想这次是他初犯。”
“这得由陪审团来决定。”律师反咬一口,“您没看见他开枪,是吗?”
“没有,先生。但他的自动手枪应该有八颗子弹,却只见三颗。等我打了第三枪,枪就空了。”
“这能说明什么呢?您也该知道可能有别人用过这支枪。您没看见他打,是吗?”
“没看见,先生。”
“那么这支枪可能是小轿车里的谁掉下来的。我的委托人可能捡了起来,我重复一遍,他干的事情是同您一样的——这可能是真的,但您却不知道,是吧?”
“没看见的事我不能作证,先生。不管怎么说,我看见了街道,看见了来往的车辆和别的过路人。要是您的委托人的所作所为如您所说,那么他是从哪儿来的?”
“严格地说——您不知道,是不是?”阿特金森大声问道。
“先生,我看见您的委托人时,他正从停着的汽车那个方向来。”杰克在证人桌上比划着,“他要是走下人行道,捡起枪,再出现在我看见他的地方——除非他是个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