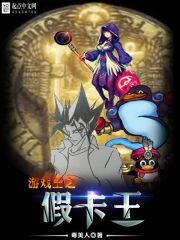爱国者游戏-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明白了,先生。谢谢您。”
轿车往左拐上了威斯敏斯特桥。杰克不知道医院的确切位置,只知道它离一个火车站很近,离威斯敏斯特教堂也不远,因为他能听见议会大楼的钟塔鸣钟报时。他仰头去看那哥特式建筑的石雕,“您知道,我除了调查之外,确实想看看你们的国家,先生。可惜时间不多了。”
“杰克,您真的以为我们不让您体验一下英国的殷勤好客就让您回美国?”公爵大吃一惊,“我们对自己的殷勤好客十分自豪,当然,恐怖分子是不会来这儿看这些的。”
“噢。”
瑞安得想一想才辨认得出他们到了哪儿,来之前看过的地图给了他提示。这叫伯特凯奇路——离他被枪击的地方才三百码……那是萨莉喜欢的湖。越过坐在前排左边的保卫人员的头,他看到了白金汉宫。尽管他知道是去白金汉宫,但现在王宫隐隐约约一出现,仍激起他感情的波澜。
他们通过东北方向的大门来到王宫前。杰克以前只是远远地看过王宫。四周的防卫看来并不引人注目,但中间空空的方阵设计几乎把一切都隐蔽起来了,在外面是看不到什么的。里面很容易设置一个连的部队——有谁猜得出来?
天太黑了,看不清更多的细节。劳斯莱斯轿车驶过一条拱道,开进王宫内院,来到一座挑棚前。站在那儿的卫兵按照英国人常用的干脆利落的三步分解动作,嚓地敬了一个持枪礼。车一停下,便有个穿号衣的男仆过来拉开车门。
瑞安逆时针方向转身,往后退一步,拉出手臂。男仆扶住他的手臂,杰克本不愿意有人帮忙,但这时候是不好拒绝的。
“您还需要练习几次。”公爵说。
“我想是的,先生。”瑞安跟他朝门走去,门口又有一个仆人在尽其职责。
瑞安曾经想过,王宫也许不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他还是为之倾倒。几个世纪以来,王室接受的世界各地所送的礼物,所到之处,都能看到宽敞的回廊里装饰着数不胜数的油画和雕塑之精品。墙上贴的大多是象牙色的用金银线织成的浮花锦缎。深红色的地毯显然是为了代表帝国的庄严,铺在大理石地面和硬木拼花的地板上。杰克曾经理过财,他想估算一下这一切的价值,但算了十秒钟就算不清了。单油画一项就够了,只要你想卖掉,就会使得世界高级艺术品市场如痴如狂。他几乎跟不上了,便想法控制使自己的书呆子气,同年纪比他大的公爵保持同样速度。瑞安越来越狼狈。对公爵来说,这就是家——可能这么大的家也有点麻烦,但总归是家呀,习惯了。墙上挂着的鲁宾斯的那些风景画,他熟悉得就象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的妻子儿女的照片一样。对瑞安来说,所到之处都给他造成了一种影响——财富和权势可以摧毁一切——这种影响要把他压缩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在街道上能抓住时机——说到底是海军陆战队训练的结果——但现在……
“到了。”公爵说着便往右拐,走进一道敞开的门,“这是音乐室。”
音乐室同瑞安家的卧室兼书房差不多大小,到此为止,这是他见到的唯一同他花了三十万美元在佩里格林克利夫置办的家可以同日而语的地方。天花板很高,点缀着全叶形的装饰。屋里大约有三十来人,他们一走进去,便都安静下来,转过身来看瑞安——杰克认为他们已经同公爵照面过了。他很想偷偷溜走。他得喝杯酒壮壮胆。
“要是您能原谅的话,杰克,我得离开一下!很快就回来。”
谢天谢地,瑞安边想边客气地点点头。现在该怎么办呢?
“晚上好,瑞安爵士。”一位身穿皇家海军中将服的人朋他打招呼。瑞安尽量不显出拘谨之态。显然,这又是一个保护人。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来王宫。当他们想到这是在王宫里的时候,便都想找点儿依靠。他们握手时,杰克仔细端详这个人。似曾相识,“我叫巴兹尔·查尔斯顿。”他说。
啊!“晚上好,先生。”他到兰利后的第一个星期就见过这个人。据给他当警卫的中央情报局的人说,他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首脑。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您一定渴了吧?”又有一个人拿着一杯香摈走过来,“您好,我叫比尔·霍姆斯。”
“你们两位在一起工作?”瑞安喝着泛泡沫的酒问道。
“穆尔局长告诉过我,说您很机灵。”查尔斯顿说。
“请原谅,您在说谁呀?”
“干得好,瑞安博士。”霍姆斯笑着喝完了杯里的酒,“我知道您过去玩过足球——当然是美国式的足球。您在乙级队呆过,是吧?”
“甲级队和乙级队都呆过,那只是在中学,我还够不上大学队的水平。”瑞安说,想要掩饰慌乱之态,“乙级队”是虚构的说法,实际是以此为幌子将他叫到中央情报局去商议事情。
“有人写过一本《间谍和间谍机构》,您是否碰巧知道他?”查尔斯顿笑着说。杰克僵住了。
“将军,我设法说,没有……”
“编号十六的那一本就放在我的办公桌上。那位好局长要我告诉您,关于‘无意义的文字分析器’,您可以随便谈。”
瑞安松了口气。这个说法一定是从詹姆斯·格里尔那里听来的。当瑞安向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提出“金丝雀笼”的建议时,詹姆斯·格里尔上将开了个玩笑,用的就是这句话。瑞安可以随便谈。可能是的。他在中央情报局受到的安全训练的确没说过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请原谅,先生。从来没人告诉过我,说我可以随便谈这些事情。”
查尔斯顿立即由愉快的逗笑转为严肃的谈话:“不用道歉,小伙子。每个人都应该严格地执行分级保密制度。您写的那份东西对侦探工作很有用。我们碰到的问题,诚如有人告诉过您的,是接到了这么多情报,现在怎样来条分缕析。要开挖这堆垃圾,找出闪光的金子,可不容易呀。您的报告是第一流的。在这方面还是第一次。我不清楚的是局长为什么称它为‘金丝雀笼’。他说您能解释得比他清楚。”查尔斯顿招招手又要了一杯香槟。一个男仆端着盘子过来,“当然啰,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是的,将军。去年七月我在局里看到过您。那时您正好从七楼的电梯出来,而我则从办公室出来,有人告诉过我您是谁。”
“好。现在您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了。这‘金丝雀笼’到底是什么鬼名堂?”
“您当然知道中央情报局泄密的那些问题哆。我完成报告初稿时,想到了一个主意,每个问题都搞它个出奇不意。”
“他们这么做已经好几年了。”霍姆斯说,“只要故意弄点小差错。这是世界上最简便的方法。要是报界的人笨得可以,刊登文件的照片,我们就能识别出泄密与否。”
“是的,先生,但公布泄密消息的记者们也懂得这点。他们学会了不刊登从各种渠道搞到的文件的照片,是吧?”瑞安答道:“我想到的是一种新的编排方法。《间谍和间谍机构》分四个部分。每部分都有一段小结,每个小结都用非常惹人注目的形式来写。”
“噢,我注意到了。”查尔斯顿说:“读来一点也不象中央情报局的文件,倒象是我们写的文件。您知道,我们的报告是由人写的,而不用计算机。请说下去。”
“每段小结有六种不同的提法。把这些段落合起来,按照文件的编号不同,每本都有其独特之处。这样就超过了一千种排列,但是只有编号第九十六的那本是真正的文件。小结的段落——呃,如此渲染,我想——其原因就是诱使记者逐字逐句引用在公开的宣传品上。他只要摘引了两三个段落中的某些文句,我们就知道他看的是哪一本了。这样就知道是谁泄密的了。他们现在已经搞出一种更加精致的方法来设圈套。可以用计算机。用词典的程序把问义同调来换去,这样每一本文件都有独特之处。”
“他们是否对您说过这办法已经采用了?”霍姆斯问。
“没有,先生。我同局里的安全部门没关系。”真得为此多谢上帝。
“噢,使用过了。”巴兹尔爵士停了一会儿,接着说:“这主意真简单——又真高明!然而又保存了文件的真面目。您的报告几乎所有细节都同我们去年的一次调查相符,他们告诉过您吗?”
“没有,先生,他们没告诉过我。就我所知,我写的所有文件,材料都来源于我们自己。”
“那么您完全是自己搞出来的啰?了不起。”
“我有什么地方弄糟了吗?”瑞安问将军。
“您应当对那个南非人多留点神。当然,这是我们管的,可能您也没有充足的情报去搞。目前我们正密切注意他的行动。”
瑞安喝干了酒,心里想着这件事。关于这个马丁斯先生,已经有许多情报……有什么地方疏忽了?他无法打听,现在不能打听。但他可以问问——
“南非人是否……”
“我想他们同我们的合作现在不如以前了,而依立克·马丁斯先生对他们是相当有价值的。您知道,他不责备他们,而且的确有办法搞到他们所需要的军事装备,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他的政府想施加给他的压力。”霍姆斯指出了这一点,“还要考虑到以色列同他们的联系。他们常常偏离轨道,但我们——秘密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为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要去大大地搞一家伙。”瑞安点点头。以色列的保安部门命令尽可能多地获得收益,这偶尔会和同盟者的愿望背道而驰。我记得马丁斯的各方面联系,但我肯定疏忽了某些重要的……是什么呢?
“请别把这当成批评。”查尔斯顿说:“作为首创,您的报告很好。中央情报局肯定要让您回去。象这样使我睡不着的报告太少啦。要是投别的事,您大概还可以教他们的分析员如何写报告。他们肯定问过您愿不愿意留下吧?”
“问过的,先生。我认为对我来说这并不好。”
“请再考虑一下。”巴兹尔爵士温和地建议道:“这个乙级队也是个好主意,那形式就象七十年代的B代表队。我们也这么做的——把外面的一些会员吸收进来——对来自正常途径的大量材料进行新的分析。你们的新任局长穆尔是个真正呼吸自由空气的人。干才。非常精通业务,但他丢得太久了,少了些新点子。瑞安博士,您应该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您属于这个事业,年轻人。”
“我不太敢肯定,先生。我的专业是历史和……”
“我也一样。”霍姆斯说:“什么专业无关紧要。在情报业务中我们看思路是否正确!您表现出了这一点。噢,对了,我们不能对您强求,是吧?要是阿瑟和詹姆斯不再劝您,我将会感到遗憾。一定要再考虑一下。”
我会的,但瑞安没说出来。他沉思着点点头,顺着自己的思路去想。我喜欢教历史。
“当代的英雄!”另外有个人来到他们中间。
“晚上好,乔弗。”查尔斯顿说:“瑞安博士,这位是外交部的乔弗·瓦特金斯。”
“就象内政部的戴维特·阿希利?”瑞安同那人握手。
“事实上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这儿。”瓦特金斯说。
“他是外交部和王官的联络官,处理简报,涉猎外交议定书,一般来说,给自己弄点麻烦事儿。”霍姆斯笑着说:“这样有多久了,乔弗?”
瓦特金斯皱起眉头想了想,“刚满四年,我想。看来倒还象是刚开始干。这不象别人想的那么充满魅力。我主要是想拿着装公文急件的盒子,躲到角落里去。”瑞安笑了笑,他想象得出来。
“瞎说。”查尔斯顿表示不同意,“外交部里脑子最好使的就有你一个,要不他们也不会留你在这儿啦。”
瓦特金斯做了个为难的手势。‘够我忙的。”
“这倒是的。”霍姆斯说:“你好几个月没去网球俱乐部了。”
“瑞安博士,王宫的工作人员要我代表他们向您表示感谢。”他懒洋洋地说了一阵子。瓦特金斯比瑞安矮一英寸,近四十岁,黑头发修剪得很整齐,两鬓微霜,皮肤白得象许久不见阳光。他一看就象个外交家。笑起来完美无缺,一定是对着镜子练习过的。这种微笑表示各种意思,也可能什么都不表示。
“乔弗可是位分析北爱尔兰形势的专家。”霍姆斯说。
“谈不上专家。”瓦特金斯摇摇头说:“我是一九六九年开始在那儿的,那时我还在军队里,是个副官——呃,现在那活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