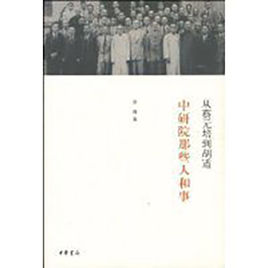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祷裱铑苯鹬拢⑸诳拐绞逼谠谒拇ǖ睦钭鞘钡亩樋晌椒缁馄绶ⅲ母咂粒笥薪羲娓邓鼓辍澳靠仗煜率俊钡钠啤?上於视⒉牛毖跏乱档氖⒛瓴恍一剂烁伟茨苷跬阉郎竦恼倩剑煤笕宋笸蟪ぬ尽�
据石璋如回忆:“到11月23日,董作宾先生也过世了,恰逢美国总统甘乃迪(按:肯尼迪)遇刺身亡日,我们说董先生是大人物,能与甘乃迪同日过世。董先生的身体底子并不坏,只是不爱运动,而且董先生既忙着《大陆杂志》社的事,又担任所长,去香港任教回台又担任甲骨文研究室主任,事情非常忙,因此同仁曾劝他装假牙,但他忙到没有空去。牙齿不好就吃不好,连带消化不好影响建康。董先生要是早日治好牙齿的问题,身体就容易养好了。”作为同乡兼同事,一起共事几十年的石璋如,可谓对董作宾具有深透的了解,但世间的事往往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董作宾可能意识不到一个牙齿的问题竟能引来这么多麻烦,且引得死神找上门来,最后把老命丢掉。不过,石氏之说也只是一家之言。据董作宾的儿子、曾给蒋介石当了几十年御医的董玉京说,董作宾在此前许多年就已患有“高血压”、“心绞痛”、“心肌梗塞症”和有家族性遗传的“糖尿病”等等,正是这成堆的疾病综合征,导致董在不该中风的年纪就已得过一次轻瘫,而且一直未能复原,直至去世。
从董玉京编写的年表可知,在1959年,也就是董作宾从香港返台8个月后的5月10日,就“忽膺中风,不能言语,入台大医院治疗三月而愈,然自后语言即告蹇涩”。其后,董氏的身体每况愈下,直至再度心脏病复发和中风不治。前往医院探视的石璋如等人看到:“董先生嘴巴歪了,也无法言语,当时大家医学知识有限,均不知是何毛病,后来才晓得是中风(脑溢血)。董先生住院期间,女儿常在旁照顾,董先生经常昏迷,神志不清,连拉出屎都浑然不觉,吃得也很少,偶尔才神智清醒,还能说笑,这时症状应该是稍有改善了,吃得也比较多。特别是11月22日,董先生清醒过来,交代了一些话,我们都稍微安了些心。没想到23日董先生就过世了。像他平常是这么痛快的一个人,身体要是不好,也不能拖这么长时间,在卧病住院近八个月期间,想必受了不少罪,难受之至。”
1962年,董作宾在台北青田街寓所1962年11月23日,董作宾于台大医院病逝。举殡日,即以台大、“中研院”、“教育部”、亲朋故旧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其规格与胡适去世时基本相同,治丧主委同为“教育部部长”黄季陆。治丧委员会决定把胡适、董同龢等中研院学者安葬的墓地正式命名为“南港学人山”。当天公祭时,黄季陆、钱思亮、王世杰、孔德成、李济等为主祭,蒋介石亲自书写挽额致赐。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莫德惠、叶公超以及“副总统”陈诚等大员参加,学术文化界同人哀悼,执绋者千余人,有20余家机构,6辆小车,4辆大车,一路浩浩荡荡,从殡仪馆送到南港,葬于“学人山”高山之阳,与胡适墓为邻。一代甲骨学大师就此安息在这里。
李济的旧梦新愁(1)
李济的旧梦新愁
胡适遽归道山不久,国民党当局再度任命李济为“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李推辞不过,只好从命。
李氏自1948年底拒绝了他的学生陶孟和等人三番五次的劝阻,毅然决然地押着他视若生命的国之重宝毫发未损地渡过波浪滔天的台湾海峡,在基隆安全登陆后,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一批批官僚、政客、奸商、投机分子、散兵游勇等等,像蝗虫一样蜂拥而至这座孤悬于汪洋大海中的岛屿谋求新的生活。
因地小人多,时局混乱,赴台人员大多无处安身。李济率领押船的部分史语所人员,勉强在台大医学院的教室中搭个简单的床铺暂住下来。据石璋如回忆:史语所人员来台后,因没其他地方可住,暂时被安置到台大教室。“人多的可以住一间教室,人少的就两家住一间教室,我就跟萧纶徽家共住一间教室。教室有前后二门,萧走前门,我走后门,两家中间用帐子拉起来隔开。公家只给一家做了一张方形大床,上头可以搁两张榻榻米,全家人就挤在一起,睡在上头。这就是我们的住。”又说:“李济先生比我们早来一段时间,家眷多,也住在台大医学院。虽然我们到这里很苦,可是我们从基隆下船一早来到台大安顿行囊之后,休息到第二天,史语所三组的同仁就在李济先生的带领下,步行到圆山作遗址调查去了。”
在迁台的最初几年,尽管孤悬一岛,前程堪忧,曾有过“心情迷乱,考古兴趣伤失殆尽”的情绪,但李济以一个国际级学者的风范和文化传承者的良知,很快振作起来,重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这一时期,李济除领导并参加了著名的圆山贝冢发掘,还参加了台中瑞岩泰雅族的体质人类学调查,组织对桃园尖山遗址发掘、环岛考古调查,整理安阳殷墟出土陶器、青铜器等等事宜。此时的李济以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人类学者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狭隘的考古专家的身份,再度展现了学术上的磅礴大气与深刻洞见。他在台湾大学为其重刊的文章后记中说道:“治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同研究中国现代政治的学者一样,大概都已感觉到,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政治的北方,结果是现在的灾难。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一类的古史,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
李济所说“现在的灾难”,当是指晚清以后的军阀及蒋介石集团没有注重中国北部的经营,因而有了外蒙古在苏俄的扶持下独立,国民党受共产党军队的重击而败退台湾的事实。对此,他告诉他的同行们,越是在这样的境况中,作为学术中人就越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与开阔,不要拘泥于一个小小的台湾岛或中国大陆。“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如此学术见地、历史境界与文化史观,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很少有人与之相匹,诚如李济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考古人类学家的张光直所说:“除了个人的胸襟,更代表了在上古史研究中的一种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
1953年秋,李济在菲律宾举行的第八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上所作专题报告《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中再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因而这片土地上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是大陆规模的。中国的文化和种族史的宏大堪与整个欧洲的文化和种族史相比拟。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并以此为依据来研究,才能在中国古代史及其考古遗存的阐释上取得真正的进展。”对于李济思想的光芒和学术上的造诣,多年后,台大毕业生李敖曾作了这样的评价:“在中国考古家由早到黑发掘古物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这种'无聊的'乌龟壳研究会有什么用,但是这三四十年来的古史研究,竟使我们发现我们民族的脐带究竟在什么地方,使我们民族的心胸遥远的跑到长城以北、玉门关以外,这对民族自信心的鼓舞,总比空头口号家的'大哉中华'来得实际有效吧?”而“这种想象……一个以国家为基点的学术研究的想象,在中国学人中是凤毛麟角的,因为这需要一种博大的透视力、远景的描绘、计划的构想和对纯学术以外的热情。在这些条件上,李济是现存老一辈学人中比较接近的一个”。对此,李敖举例说:“他在四十年前就注意到中国民族的移动问题;三十九年前就注意到中国苦力的劳动量问题;三十八年前就注意到外人发掘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的问题;二十九年前就注意到古物一律不得私人藏有的问题……这些观点和构想,都是很博大的,都是超乎一般普通学者教授们的'管'见的。这些博大的观点,自然使具有它们的人,逐渐能从本行的专业,发衍为'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再从而在中国全面的有组织的推进科学思想,以使中国真正达成现代化。”在谬论充斥的李敖言论中,这些评论算是少有的实在话。
李济的旧梦新愁(2)
早在1934年,李济在发表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中,就向世人展现了这一思想脉络和文化精髓。纵观李济的一生,作为一个学术大师之“大”的体现,除了他对考古材料缜密的考证,主要还是体现在他的胸襟、学术眼光与对整个人类文明过去与未来的清醒认识上,他极富创建性地提出:一、古物国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二、设立国家博物院,奖励科学发掘,并有系统地整理地下史料;三、设立考古学系,训练考古人才。为实践这三项主张,李济早在西阴村发掘时就做出了“古物国有”的示范性表率。从他涉足古物那一天始,直到去世,据他的同事、亲友及弟子们说,家中没有一件古物,晚年书房里只有五只木雕的猴子,生前藏有近二万册图书无一善本,死后分别捐赠给北京和台湾两岸的科学、教育机构。③有人认为李济正是为了实践他的第二个主张,在史语所创办的早期,才积极协助傅斯年筹办中央博物院,并一度出任筹备处主任。只是其间遭逢八年抗战和颠沛流离之命运,使这一理想未能充分实现。所幸的是,来到台湾后,他的第三个主张和理想得以顺利实施……这就是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在朱家骅、傅斯年等人的支持下,李济于1949年创办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并于秋季正式招生。李氏除继续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之职,还兼任该系系主任,并聘请史语所的同仁芮逸夫、董作宾、石璋如、凌纯声、高去寻等到该系任教。……这一创举,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把训练职业考古学家列入大学计划之内,从而开创了大学教育体系设立考古专业的先河。尽管这一学科创办之初,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大众对这一“乌龟壳研究会”的陌生与偏见,招生很少,但却为考古学的未来播下了种子。当时除一个叫乔健的学生自动转系来到考古人类学系外,首届毕业生仅有李亦园、唐美君二人。第二届学生共招收三人,分别是张光直、林明汉、任先民。以后学生渐多,有许倬云、宋文熏、尹建中、连照美等等。这些学生走出台大后,随着岁月的淘洗磨练,大多数都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其中张光直、李亦园、许倬云等,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尤其是作为后起之秀的张光直,在专业上的成就以及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声誉,甚至超过了他1953年前后,李济与张光直合影的业师、号称“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面对如此光芒四射的成就,李济生前曾不止一次颇为自豪地对他的好友费慰梅等人说:“我平生认为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一个是张光直。”后来李济的这两位得意门生,一位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位出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台湾中研院副院长,都为中国和世界考古人类学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贡献。
1954年9月22日,李济致信刚从台大毕业,正在台湾凤山接受军训的张光直,诚挚真切地说道:“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地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在那里排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有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又说:“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