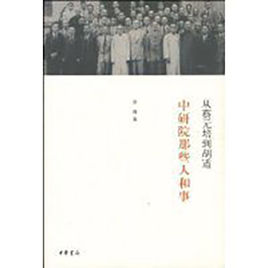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买菜,陶孟和整天闷着头不太爱说话,沈师母人长得漂亮,有风度,看上去像是大家闺秀。只是那时生活不好,精瘦精瘦的,脸色也黄黄的,听大家闲聊时说她有病,具体什么病,当时不晓得,后来才知道是肺的事。”①
尽管生活艰苦,夫人沈性仁又患病在身,但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陶孟和于愁苦中只能咬牙勉力支撑。想不到仅仅一年之后,因“进军西北”一事,陶孟和与傅斯年又闹得不可开交,直至割袍断义,成为学术界一大憾事。
陶、傅二人李庄交恶,与当年兴起的“西北考察热”紧密相连,而这个热潮最早的源头要追溯到抗战之前。
1937年4月,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到北平,召集一班对于西北问题有研究的学者商谈西北教育补助事宜,因弄《古史辨》而暴得大名的顾颉刚亦在召集之内。未久,该董事会聘请陶孟和、顾颉刚、戴乐仁(英国人)以及刚从德国归来的王文俊为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计划赴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对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摸底考察。9月,陶孟和一行抵达兰州,陆续考察了当地和西宁的教育状况。由于绥远沦陷,宁夏临近前线,故未克行。在一两个月内,几人在兰州和西宁两省城考察后写了一篇考察设计报告,陶孟和等三人便乘飞机回南京交差去了。此时上海已经沦陷,顾颉刚的家乡苏州已沦于日人之手。面对北平不得返、家乡不能回的境况,顾颉刚继续留在该会在兰州贤侯街45号租赁的地点,开始邀集一帮同志深入边地农村继续开展工作。1938年6月29日,顾颉刚致函杭立武,在汇报自己考察成果的同时,指出甘肃“各县所需不同,除办职业、师范、女子诸教育外,又需办社会教育,以消除强烈之种族宗教成见,避免祸乱”。杭立武表面颇具诚意,在函中批示“计划周详,条理绵密”,但一条也未采用,最后采用了陶孟和等人的设计方案,在兰州办了一个科学教育馆、西宁办了一所湟川中学便草草了事。
顾颉刚通过考察,有了另一个发现,即西北地区不仅是教育状况极劣,更潜伏着政治危机。整个西北到处都有外国传教士,没有汉人之处也有他们的工作站,有的传教士已到西北数十年,语言、装束完全与当地人一样,暗中挑拨蒙、藏、回等少数民族与汉人以及中央政府的关系。据顾颉刚在后来撰写的《自传》中说,他曾在一位到边区做县长者家中看到一张地图,是从一个传教士旅行时遗忘之物中检出来的,名为“TheMapofGreatTibet”,即所谓的“大西藏地图”。这张地图将喇嘛教所达到的区域,除了满洲、蒙古之外都算作西藏。顾颉刚看后大吃一惊:“日本人造伪满洲国,称为'民族自决',这种事大家知道是假的,满洲国有几个满洲人?但是这个'大西藏国'如果真的建立起来,称为'民族自决'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血统、语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块整齐的疆土,再加上帝国主义做后盾,行见唐代的吐蕃国复见于今日,我国的西部更没有安宁的日子了。”1938年9月上旬,顾颉刚乘飞机离兰州抵成都,下旬到重庆,向中英庚款董事会汇报调查情况,强烈建议对于不怀好意的外国传教士立即采取措施,并说道:“这次的国难是东北问题造成的,诸位不要抗战期间,吴文藻、冰心夫妇与孩子们在燕南园寓所前合影留念。未久,一家人离开北平,前往昆明
以为这次国难终止之后就没事了,须知西北和西南的问题更严重的阶段在后面呢!”又说:“因为我到西北去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复元气,许多的乡镇满峙着秃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遗憾的是,没有哪位官僚政客乐意倾听顾氏的警世之言,皆匆匆敷衍一番了事。
1938年10月下旬,顾颉刚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赴昆明云大任历史学教授。未久,为避敌机轰炸迁居昆明北郊浪口村。差不多在此前后,早年毕业于清华,后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文藻、冰心夫妇也来到了云南大学。吴在云大创办了社会学系,并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招收了费孝通等几位助手。费孝通在2005年接受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访问时,曾断断续续地提到过这段生活,说:“在燕京,吴文藻同他们都不对的,他是清华毕业的,应当回清华的,因为冰心到了燕京。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这样,吴文藻是被爱人带过去的,在燕京大学他没有势力的,在燕京靠老婆。后来出了燕京,他才出头。吴文藻的一生也复杂得很啊。我们燕京大学是跟老师的,一个老师带几个好学生,我是跟吴文藻的。”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2)
在谈到当时燕京与北大、清华相互之间的关系时,费孝通明确表示北大、清华与燕京有很大不同,“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搞不到一起的。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得比较远,想从这里面打出一个基础来,通过Park这条思路创造中国这一派。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培养学生。”又说:“云南大学校长是清华的熊庆来,他请吴文藻去组建社会学系……但到了云南大学没有办法发展。后来冰心不愿意在云南,她的朋友顾毓琇想追冰心,没有追到。冰心厉害,看中吴文藻,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
最后,费孝通总结性地说:“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因而,1949年之后,费孝通竭力主张要给这些不能“治国平天下”的旧知识分子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造。后来,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进了牛棚,而有幸得到费氏“欣赏”的知识分子如曾昭抡等亦未能幸免,后来被赶出京城,于凄风苦雨中告别了人世。再后来,费氏自己也落入政治圈套而不能自拔,成了不折不扣的“牛鬼蛇神”。当然,在费孝通看上的人物中,只有冯友兰是个异数,他以御用文人“梁效”掌门人的身份,跟随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腾云驾雾好一阵子,在得以保全性命的同时,也给这纷乱的世界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生哲学命题标本。
费孝通成为吴文藻的得意门生后,和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唯吴的马首是瞻,从费氏的谈话中知道吴与傅斯年不和,但他没有明确列举不和的原因,只隐约透露了吴到云南大学之后要建立社会学系,但又遇到强大阻力,最后只得放弃云南赴重庆工作云云。这一点,从台北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与顾颉刚、朱家骅等人的通信中,可窥知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隐秘。
却说顾颉刚离开西北辗转来到昆明后,“出于排解不开的边疆情结”,便在《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集合许多朋友来讨论边疆问题。想不到这一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傅斯年的警觉。
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流动量大增,“外来户”与当地土著或私下称作“土包子”之间不团结,闹矛盾,或暗中较劲儿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国民党统治的西南边城昆明如此,而共产党控制的陕北黄土窑洞依然若是。当时的左翼作家茅盾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就曾叙述过抗战期间自己在昆明与顾颉刚、朱自清、闻一多、吴晗等人交谈的情形。据说茅盾曾让朱自清派人去找过冰心,正好冰心外出不在家,未能参加。谈话不久,茅盾就发现所谓的“外来户”与“土包子”之间不团结的问题,遂当即决定“把话题转到外来文化人与本地文化界如何联络感情加强团结的问题”。参加谈话的顾颉刚在发言中曾说:“大家步调一致是对的,但把单方面的意见强加于人就不对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傅斯年通过对昆明社会各阶层思想现状分析,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从团结的大局出发,针对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创办的那个《边疆》周刊以及登载的文章,毫不客气地给予批驳。傅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曾这样说道: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3)
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夫“边人”自昔为贱称,“边地”自古为“不开化”之异名;此等感觉云南读书人非未有也,特云南人不若川粤人之易于发作耳。其次即所谓“民族”。犹忆五六年前敝所刊行凌纯声先生之赫哲族研究时,弟力主不用“赫哲民族”一名词。当时所以有此感觉者,以“民族”一词之界说,原具于《民族主义》一书中,此书在今日有法律上之效力,而政府机关之刊物,尤不应与之相违也。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夫云南人既自曰:“只有一个中国民族”,深不愿为之探本追源;吾辈羁旅在此,又何必巧立各种民族之名目乎!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广事传教。即迤西之佛教,亦自有其立国之邪说。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是一个”耳,此间情形,颇有隐忧。迤西尤甚。但当严禁汉人侵夺蕃夷,并使之加速汉化,并制止一切非汉字之文字之推行,务于短期中贯彻其汉族之意识,斯为正途。如巧立名目以招分化之实,似非学人爱国之忠也。
针对这一论点,傅斯年正告顾氏:要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又说:“日前友人见上期边疆中有名干城者,发论云:'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争斗史。在今日,边地夷民,仍时有叛乱情事。'所谓鲜血史,如此人稍知史事,当知其妄也。友人实不胜骇怪,弟甚愿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实有利也。”
傅斯年与顾颉刚原是北大同窗好友,此前在广州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时产生矛盾,进而割袍断义,想不到十几年后二人又在昆明相遇。为民族大义计,顾颉刚接信后,听从了傅斯年的劝说,即作《中华民族是一个》发表于周刊。顾氏如此做法,当然不是屈服于傅斯年的压力,而是一种外力警醒下的自觉。当时中国云南的政治情形正如本地出身的学者楚图南在后来回忆中所言:除蒋介石的“中央”与云南省掌门人龙云的“地方”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之外,在文化教育界,已经产生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云大与联大之间的隔阂”,以及“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如留美派、留欧派、洋教授和土教授等门户之见”。正是鉴于这一错综复杂的局面,顾颉刚才在文中主张:“中国没有许多民族,只有三种文化集团……汉文化集团、回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中国各民族经过了数千年的演进,早已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尤其是'汉族'这名词,就很不通,因为这是四方的异族混合组成的,根本没有这一族”云云。
后来顾颉刚在《自传》中回忆:文章发表后,“听人说各地报纸转载的极多,又听说云南省主席龙云看了大以为然,因为他是夷族人,心理上总有'非汉族'的感觉,现在我说汉人本无此族,汉人里不少夷族的成分,解去了这一个症结,就觉得舒畅多了”。顾文的刊发,令当地土著和省主席龙云等甚感满意舒畅,傅斯年当然也乐意看到这一结果,写信谓顾氏深明国家民族大义并加以赞扬。为此,二人的心又拉近了一步。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陈寅恪也同意傅、顾的观点,认为外来的知识分子不要乱说一些夷汉籍贯之事。云南史学家方国瑜请陈寅恪以及顾颉刚、姚从吾、向达、方豪等学术界名流吃饭。席间,方豪问方国瑜,云南的方姓是从哪里迁来的。方国瑜答:“我桐城方氏的后裔。”饭后,顾颉刚告诉方豪:“方国瑜是么些人(按:云南少数民族称呼),说是桐城方氏后裔,只是面子好看些。”陈寅恪提醒方豪:“我们万不可揭穿他,唐代许多胡人后裔,也用汉姓,也自道汉姓始祖何处。”就在学术界以抗战团结为重,尽量避谈夷汉民族之别,并对傅、顾的学术观点群声叫好之时,却惹恼了另一个山头的派系,为首者乃吴文藻,马前卒乃吴的弟子费孝通。
吴文藻是属于中英庚款基金会派往云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