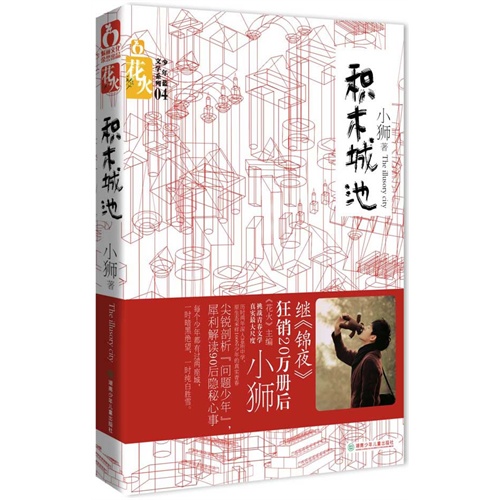积木城池-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借题发挥?为什么?”
郑松轻蔑地哼笑一声,说:“虽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次保送之争肯定暗藏一大把猫腻。”
尽管这个解释比较合情合理,但是我还是不太理解,被保送的话除了不需要高考,还可以减免学费,她怎么可以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我思前想后,又得到一个新的猜测,难道是她对陈浩太失望,宁可放弃名额也不愿意和他同行吗?
我现在终于知道她为什么得到保送名额后反而更加刻苦学习了,她早就觉察到自己是暗箱操作的牺牲品,首次受挫时的委屈压得她无法承受,重获名额后她就没有准备接受,以这种极端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抗拒与不满。我的怒气渐渐地消散了,不再责怪她擅自放弃名额的事情,因为我知道,这就是她的行事风格,不欠人一分一毫。后来卫薇问我找简洁干吗,我随口敷衍道:“买个蛋糕而已。”
既然她不想被人知道,我也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和她一起向着高考冲刺着,尽管学业繁重,考试无休无止,但是我感觉十分愉悦。去年学校运动会时章鱼报名参加五千米长跑,他奋力奔跑着,要在全校女生面前展示一下他的雄风,最后他得了第一名。然而,出尽风头的不是他,而是我,因为我为了鼓励他奋勇前进,全程陪跑着。他跑完全程后累得七魂六魄丢掉了一大半,而我只是面红耳赤,微微喘息。现在与其他人相比起来,我的心理压力不是很大,也很少抱怨,因为这并非是我不得已才走上的道路,我有我的理想——与简洁在一起。
“你这叫玩票,是一高考票友。”章鱼这样定义道。
“票友?”我觉得这说法挺新鲜的,笑着继续问道,“那你呢?”
章鱼想了想,语气十分坚决地说:“炮友,我们都是高考的炮友,真够倒霉的。”
正如动画片《海绵宝宝》里的派大星一样,章鱼平日里傻兮兮的,关键时刻却能说出各种深邃的哲理,令天朝学者们为之汗颜。每天我憋在教室里学习,很少外出活动,有时接连端坐半天,偶尔抬头活动一下脖子肩膀,看见周围同学一张张麻木得狰狞的脸,都会不寒而栗。从五六岁进入幼儿园开始至今,我们一直泡在学校里,不停地考试学习,好不容易混出大学,进入社会,又要被乌烟瘴气的社会蹂躏,半生的财力都用来供养房子。按照一些竞技游戏的说法,这是一套连环招数,被盯住的目标几乎没有翻身的机会,更悲剧的是,它还是群体范围的攻击,最好的解救方案是投胎投得好,譬如在下。
'二十四'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
离高考仅剩几个月时间,每天的生活都枯燥到极点,无非是做完试卷再讲评,讲评完了继续做试卷。有一次班主任老师希望活跃一下气氛,讲课的时候插播一条冷笑话,然后一个人站在前面傻笑,台下众人木然地看着他,他笑得如此尴尬,以至于我都替他脸红了。白痴永远不止一个,教物理的周老师捧来一沓试卷发下来,我们花了三节课搞定,讲评到最后一道题的时候他嘀咕了一句:“这道题不是挺难的吗,怎么你们都会做呢?”
立即有人回应道:“好像前天你已经拿给我们做过一次了。”
老周愣了一下,生气地说:“那你们怎么现在才说?”
几个脸皮厚点的起哄道:“我们刚刚发现。”
这种憋屈得让人想造反的生活,连老师都被整疯了,看来大家都不容易。老周今年五十二岁,这么多年来反反复复地带着毕业班,生活像驴子拉磨一样枯燥。有一次和早几届的一个学长聊天,他问道:“老周讲到杠杆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把他小时候和他哥哥用扁担去抬东西的事情拿出来讲?”
“是啊,你怎么知道?”
学长笑了笑,说:“我高中物理也是他教的,据说他这个例子已经举了十来年了,每一届学生都听说过,真是执著啊。”
话说我真是一个物理天才,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高中普通物理试卷上的题目我都能够解答出来,我觉得我应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当然,简洁背书功力堪称一流,长达千字并且晦涩难懂的先秦古文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塞进脑袋里,她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手拉着手,心连着心,肩并着肩,一起奔赴诺贝尔颁奖现场。
学校公告栏又贴出红榜了,是本次全市毕业班模拟考试的成绩,理科班状元正是在下,而文科班状元依然是简洁。尽管在公众眼中简洁和陈浩都是保送生,但是现在很少有人说他们是金童**了,因为简洁如今像挥师过江的解放军,而陈浩则沦为偏安一隅而纸醉金迷的太平天国,只能放在一起作为对立面来比较。我十分期待有人造谣说我和简洁是金童**,可是现在大家都这么忙,谁也没空扯这些花边新闻,看来只能我自己造谣给自己听了。
出人意料的事情比比皆是,兆宁高中积极配合招飞工作,终于有了振奋人心的回报,学校一共有五个人继续入围下一阶段的筛选,其中就有唐明煌。他行事风格比以前更加谨慎,原本精心设计的发型都给处理掉了,理成一个平顶头,竟比以前好看多了。他们下一步就要去省会城市统一接受最后一次体检,政教处一个老主任和郑松两人带队,我和章鱼去超市买饮料的时候刚好看见他们上车,章鱼撇嘴嘀咕道:“怎么就被他赶着了呢,他打架打得过我吗?”
“打架?连颜色都分不清的人闭嘴!”
章鱼立即不说话了,色弱的毛病是他心中的一块痛,他经常分不清蓝色和紫色,看不出浅粉和米色,更看不出**图上画了什么东西。他曾经给一个漂亮的学姐写情书,却不敢亲手送过去,只得让一个小弟去送死。偏偏当时一袭蓝裙的学姐和她的闺密一起走着,章鱼对小弟说:“去,交给那个穿紫衣服的。”
于是小弟把情书交到学姐身边那位紫衣闺密手里去了,当天傍晚他们在学校体育馆浪漫约会,紫衣闺密的目测体重七十多公斤,她看着章鱼这个水灵灵的学弟,幸福地流下口水。一般来说,当红明星都会宣布自己患有某种先天性疾病,虽然这些病一般不足与外人道,不影响日常生活,但能引来众人一片怜爱。章鱼原本就以自己色弱的毛病为荣,每次提到此事就会一脸哀怨,实则得意扬扬,不过经历紫衣闺密风波之后,他一改往日观念,对色弱讳莫如深。
向省会派遣的小分队偶尔会传回消息,譬如谁不小心有点感冒,谁被查出来身体有点毛病,谁的反应速度不过关,谁确定被淘汰了。这是一场残酷的淘汰赛,有时我们觉得那简直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他们就是被淘汰了。五人中有一个家伙是兆宁镇和我一起混的本地小子,他自认为此行十拿九稳,不料在跳绳环节出了差错。对方要他用尽可能多的花式来跳绳,他跳了六种常见花式之后就跳不出来了。什么正跳反跳,什么交叉正反跳,什么连环正反跳。
他被请出去了,唐明煌则留了下来,他的常规跳绳花式仅有正反跳两种而已,但是他的非常规花式就多了,譬如左手抓着绳子在身体左侧乱舞,右手抓着绳子在右侧乱舞,然后举在头顶乱舞假扮直升机。他这样跳大神似的乱跳一通,连旁边的军医都愣住了,不过他们还是将唐明煌留了下来。
四天以后他们终于返回学校,一个个都昂首挺胸的,倒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凯旋而归,而是因为他们至少公费旅游了一趟。碰巧的是,他们下车时又被我撞见,刚好唐明煌从面包车上跳下来,他看到我以后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对我微微一笑。正如我爸所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即使我对唐明煌的印象仍然很差,我也不能冷眼相待。我也点头笑了笑,问道:“回来啦?体检结果怎样?”
他的同行者听到我的询问,搬行李时都慢了半拍,似乎在窃听谈话,唐明煌对此有所觉察,保持笑而不语的姿态。我们转到走廊圆柱后面,他从包里翻出一个牛皮纸包,鬼鬼祟祟地递到我手里,我好奇地问道:“什么玩意儿,三尺红头绳啊?”
他摇了摇头,居然一本正经地说:“不是。”
我小心地打开察看,发现纸包里摆着两支小雪茄,周身都是由整片烟叶卷成的,闻上去气味很独特。虽然我经常以见多识广自居,但是我没有正儿八经地接触过雪茄,这次久仰大名幸会幸会,我还真蛮稀罕这玩意儿的。他看着我,恭维道:“这个是我偷偷买的,一共六支,给你两支。”
“为什么?”
“这个嘛,兄弟情谊。”他讪讪地笑道,“谢谢上次你给我解围。”
“嘿,那点小事你还记得干吗!”话虽如此,我还是将雪茄放进口袋里,反正是不花钱得来的稀罕玩意儿,不拿白不拿。看来我与唐明煌之间算是达成和解,即使没有成为朋友,至少也不再是敌人,我感觉兆宁高中的空气都干净了许多。我猜唐明煌给我两支雪茄是有意图的,我擅自揣度一番,决定将其中一支郑重其事地赠送给章鱼——即使他不是这个意图,我也照样分一支给章鱼。
章鱼的立场也没有那么坚定,当他知道这雪茄来自唐明煌的馈赠,只是稍稍犹豫一下就收了下来,真是有我的“遗风”。他现在已经认清现实,知道我在努力修复与唐明煌的关系,夏维宜的那点破事也过去那么久,何况人家姑娘那也是挥泪弃暗投明的。
体检结果很快就出来,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唐明煌光荣过关,接下来面临的就是所谓的政审之类的事宜。政审过程的细节我不太知道,不过其中一小部分我不但了解,而且参与其中,因为有人召集部分学生代表举行畅谈会。
学生代表大都有备而来,无非是一套洋洋洒洒的粉饰之言,什么忠君爱国什么助人为乐什么讲文明树新风,听得组织者都差点打哈欠。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泼脏水,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决定当一回好人,这样一个派送顺水人情的机会我不能轻易放弃。
“我与唐明煌同学不太熟悉,不过听其他同学说,他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对身边的人和善友好,即使对陌生人也是彬彬有礼的。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唐明煌的朋友,他是一个相当挑剔甚至刻薄的人,但是他曾经认真地说,交朋友就要交唐明煌这样的。”
在场的学生代表中有一两个曾经是唐明煌麾下的爪牙,他们听到我这一席话后都偷偷地瞅我,但是我深情演讲的功力让他们自惭形秽,他们必然扪心自问:人常言明煌与小泽有隙,今观小泽泣血死荐,始觉小泽哥气度之洪量,明煌之辈不可望其项背也!
天气渐渐炎热起来,高温与蝉鸣让人昏昏欲睡,而临近的高考更让人喘不过气来。我妈也对我的高考大业开始重视起来,她让陈姨住下来照顾我的起居,而她自己看上去极力督促我的学习,实则毫无积极向上的作用,反而把我正常的学习计划打乱了。一道化学题刚弄出一点眉目,正要豁然开朗时她跑来在我后背猛然一拍,高声喝道:“坐直了!”
我吓得魂飞魄散,呼之欲出的解题关键点也不翼而飞,好吧,我继续重复刚才的思路,终于摸到一点线索,她又端了一杯我叫不上名字的营养冲剂放到我手边,说:“喝掉!”
那条线索又一次滑入无边无际的脑海中去,再也找不到踪迹,我十分窝火地抱怨道:“能不能不要打扰我,让我自己做点事情?”
我妈立即暴跳如雷,她在我脑壳上重重地敲了一下,骂道:“你这个小白眼狼,怎么跟你爸一样忘恩负义?我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拉扯大,现在你翅膀硬了就敢对你妈大呼小叫!我供养你读书你读到猪狗身上去了?”
她越说越愤怒,可惜她的坚强没有坚持下去,她说着说着就抹起眼泪,摔门而去。我当时十分郁闷,为人父母的怎么可以如此阴晴不定,有本事你等会儿别去打牌。据说,这是青春期与更年期的战争,可是我宁愿歌颂和平。
我妈在客厅里怒我不争,陈姨在旁边哀她不幸,幸好这样的局面只持续半个小时就结束了,因为有人打电话喊她去打牌。在她看来,打牌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就像我们上学一样不能迟到旷课,她收拾了一下东西就迅速开车赴约去了。我站在楼梯口,陈姨站在客厅抬头看着我,两人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陈姨说:“下来,把饭吃了。”
我其实不饿,却还是顺从地去吃饭了,尽管陈姨只是保姆,可是我对她尊敬有加,她把我对母亲的敬畏之情中的“敬”划分走了。说实话,我妈在母仪全家这方面做得确实不太好,我特别希望她能像章鱼老娘一样贤良淑德,每天琢磨着弄些什么点心出来,而不是到处逛荡打牌搓麻将。我自认为心理素质比较好,很少出现临考综合症,可是这次完全不同,毕竟是平生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高考。
“不怕,”我自我劝慰道,“还有出国这条路呢。”
这样一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