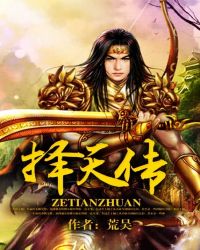列异传-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喘口气,又喝了一口咖啡。
他动了动眉梢,笑着说,“你对曹丕评价很高嘛。”
“是他应该的。”我不加思索脱口而出。“世人唾骂曹丕,不过是因为一篇子虚乌有的七步诗。而要是真正看过他的诗作,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让人心痛的文人,”停了一下,又说,“或是一个让人不忍靠近的剑客,兼而有之。”
他笑笑,不置可否。
“以前同学写作文,总喜欢说他是个无情的帝王。但是我觉得,他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是一个浪漫主义剑客,最后,才是一个帝王。”
“这么说,曹丕也太不称职了吧。”他耸了耸肩,“他的职业是个皇帝,而做诗,顶多算是业余爱好。”
“三曹都是业余爱好者。”我说。
“做诗人,曹子建是本职。”他说。
“曹植是个王爷。”我坚定自己的立场。
他还是微笑,没有再和我争辩下去。
“他们两个都是诗人。”静默了良久,他突然下了结论。“一个恣意汪洋,狂放不羁,像李白;而还有一个,沉郁清婉,精思逸韵,有几分李商隐的影子。”
“说得好。”我会心一笑,“我觉得,一个像貂禅,一个像西施。”
“怎么说?”
“貂禅闭月,华光初上,锋芒毕露;而西子捧心,顾盼摇曳,掩映动人。”
他的笑,张乐于野,泠风善乐。
“谢谢你的座位。”他站起身,像一阵烟云般,消失在忙碌的人群中。
冰凉的座椅,好像从没有人来过。
“Hey,中国小伙子!”隔壁桌的意大利美女走过来跟我打招呼。烫成波浪卷的红发,烟熏妆的眼影,性感妖娆。我注意到,从我坐在这里消磨古籍开始,她就已经坐在那儿了。
“一个人坐了一个下午,不闷吗?”
她涂着CD烈焰蓝金的嘴唇,笑得性感,而浓烈。
第四章 初吻
虽然是下午,大学里的走廊却显得空荡荡的,没有多少生气。
我拐上一截楼梯,暗自嘟哝这几百年的校舍若是在晚上该多么阴森恐怖。要不是把手机忘在了教室,我绝对不会一个人跑上来。
寂静的迷雾中,隐约,传来水珠滴落的破碎声。
黑白键盘的敲击,从走廊转角的那一边传来。
从来不知道,学校会在走道摆钢琴;更不知道,在21世纪的今天,还有人能弹奏出如此纯净的音符。
破碎的水珠,不是用手,而是用心。
我拐过弯,又看到,那个粉妆玉琢的红衣小男孩。
长长的刘海,遮不住他灵动的大眼睛。红衣小男孩安静地坐在钢琴凳上,双脚悬空,用他稚嫩而纤白的手指,在黑色的镂空雕花三角钢琴上,跳跃着一个个单音。
是《托斯卡》的咏叹调。
我惊呼。一个绝美如斯的孩子,竟能演奏出如许的深沉,悲哀,和绝望,好像这具躯体,已在哈底斯的宫殿,忧郁了数百年,让我不由深陷其中。
似乎听到了我心底的深呼吸,他抬起头,看向我。
如钻的黑眸,一丝愁绪,盈光点点,却是让世界霎时明亮。
我肯定,自己见过这么一双眼睛。
很多人不知道,我认识他,比甄宓早。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诸侯争霸,连年战乱,生灵涂炭,十室九空。辗转进入曹家为婢的那一年,我十一岁,他八岁。
那时我在他眼里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而他,却是那种让人轻轻一瞥就过目不忘的孩子。洁白透亮的肌肤,乌黑润泽的长发,一双大眼睛,水光潋滟可怜无比,配上一身如火的红衣,就是一个真丝织成的娃娃。
在那一群侍婢中,我的年龄和他最为贴近,因此,成为了他的贴身侍女。
他叫我嬛姐姐。
发“姐姐”这个音的时候,他的嘴角总会微微向后打开,眼睛弯弯的,像在笑。
他笑起来很好看,像三月的风,轻柔又腼腆。于是,我便一直想看他笑。
红衣小男孩笑了。但眼前的笑,却隐隐让我心悸;不是和风细雨的温软,而是在蛊惑人的大眼睛中,透出丝丝灵黠与邪气。
可是,只要他笑,无论怎样,我都会驻足。
似乎是知道自己的胜利般,他唇边的笑更浓了些。转过头,用双手,演绎出涓致的曲调。
如梦似幻的旋律,令人迷醉。
从他指尖流淌开的,是电影《初吻》的主题曲,“Reality”。
耳边似乎有人轻声哼唱,带我走入那个夏日的梦境。新月,星空,蝉鸣,画廊,如此清新的记忆;仲夏夜之梦中,少女,和红衣少年,初吻的回甘。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 of real fantasy
Illusions are a mon thing
I try to live in dreams
It seems as if it's meant to be
Dreams are my reality
A different kind of reality
I dream of loving in the night
And living seems alright
Although it's only fantasy
Dreams are my reality
The only kind of reality
May be my foolishness has past
And may be now at last
I'll see how a real thing can be
Dreams are my reality
A wonderous world where I like to be
I dream of holding you all night
And holding you seems right
Perhaps that's my reality
柔和的月色下,那双总是动盼的大眼睛,盈满了泪水。
“大哥走了…”群芳缭绕的凉亭中,他躲在我怀里,抽泣。
他仍是个孩子,而我,已经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娉娉袅袅,豆蔻梢头。
一瞬间,突然有种冲动,不顾身份,不顾年龄,只想轻轻俯身,吻去他的泪水。
那时的我,并没有太多的顾虑,而捧起他脸的一瞬间,触碰到他含着泪光的大眼睛,已忽然像中了蛊惑般,对这张脸,着了迷。
正处于童年与少年交界处的他,透着一种独特的稚嫩青涩和栀子花般的香气,嘴唇红艳艳,湿漉漉的,醉人。
像我最钟爱的锦缎娃娃。
没有犹豫,我印上了他的唇。干燥的清洁,那是我的初吻,亦是他的。曾经,无数次,对初吻,梦想过,憧憬过,只是没想到,是今天那个王子带着淡淡泪痕的花瓣。忘了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只记的,青涩懵懂的空气中,伴着一点心悸、心慌、心动的花蜜,丝丝缕缕的甜,和甘香。
我只轻轻碰了一下他的唇,便知道自己的僭越,慌忙放开;低头,却看见那个王子抬着头,水灵灵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泪滴凝固在眼角旁,颤颤巍巍的,有点好奇,有点羞涩,有点慌张,又有点不知所措。
他伸出手,遮住自己的大眼睛和大半张脸,好像害怕,又像羞涩;半晌,又用食指和中指间的缝隙透出一小条缝,悄悄打量着我。
灵黠的慧目,流波婉转。
呵!我笑了。他不过是个孩子……
Dreams are my reality
A wonderous world where I like to be
Illusions are a mon thing
I try to live in dreams
Although it's only fantasy
Dreams are my reality
I like to dream of you close to me
I dream of loving in the night
And loving you seems right
Perhaps that's my reality
初吻的记忆,只是别样的芬芳。
我望着眼前的红衣小男孩,发怔。
他没有再弹琴。看着我,只是笑。
“我要去找宓姐姐了……”
他轻轻一笑,转身,轻化作空气中的尘埃。
我用力揉了揉眼睛,校园的悠长的走廊,从未出现什么黑色的镂空雕花三角钢琴,亦没有过纯美动人的红衣娃娃。
只有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这里发愣。
我记起来了。那个孩子,叫子桓。
第五章 安娜
在异国他乡的小镇,尽管初到时新奇万分,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邮筒都能嗅到不同寻常的味道,但新鲜劲一过,时而也觉得时光的索然无味和难以打发。于是,又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当终于享受惯了永远不知疲倦的骄阳,流连够了芳香宜人的薰衣草,甚至已经拜访过了海边风姿摇曳的迷迭香,同学便在房东家的旧影碟堆里翻箱倒柜,并在发现新大陆似的找到苏菲?玛索版的《安娜?卡列妮娜》后一个劲地催促我坐下陪他消遣。
《安娜?卡列妮娜》在影史上有诸多经典版本,如费?雯丽版,嘉宝版,我小时候都曾经看过。至于苏菲?玛索这一版,虽然在国内一直捧得很红,而且一个文艺的译名《爱比恋更冷》也具备足了吸引眼球的潜质,但我因为对苏菲?玛索的个人偏见一直没有去观膜。今天面对同学盛情,实属无奈。
我不喜欢苏菲?玛索,尽管她被称为所有中国男人心目中的法兰西情人。
她很美,我知道,而且是雪肤花貌国色天香的美,但我就是不喜欢。
她总是让我想起什么人,随之而来的总是一种不好的感觉,压抑,而且刺眼。
好像我以前也见过这么个女子,雪肤花貌,国色天香,兼带着眉眼中冷冷的桀骜与不驯。很美,称得上绝色倾城,然而每次见到她,我都觉得心里并不十分舒服,好像她漂亮的眼睛正戏谑地嘲笑着我。
她确实是在嘲笑我。
即便后来她死了。
我知道,她高傲的眼睛在对我讽笑,提醒我:仲达,子桓的心。
她有,真实的拥有,像赵飞燕拥有汉成帝的心那样牢固地拥有,而我,却真的不知是否曾经得到过一瞬。
所以我不喜欢她,一点也不喜欢她。说不上嫉恨,但或许,又是。
而苏菲?玛索,从骨子里像她,从眼睛,到灵魂。
其实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喜欢苏菲?玛索,总之,就是不喜欢。
不过,《安娜?卡列妮娜》确实是经典佳作,值得一看。
我并不是那种看到能让人直飙眼泪的文艺爱情片就坐不住的文艺青年,可这部片,我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有些动容。
诚然,当渥伦斯基坠马时安娜惊呼的神态让人喟叹,冰天雪地的火车外两人的相遇让人长息。然而,我的感动,却不是因为安娜的感情,而是渥伦斯基。
当影片的结尾,看到渥伦斯基一心已随安娜离去,落寞地倚在开往土耳其前线的火车车窗时,忽然觉得心里有股被针扎了一下缓缓流血的痛。爱情,有时无需像安娜?卡列妮娜表现得那般悲壮与轰轰烈烈,悲伤的桎梏,亦是永恒。
世人只知渥伦斯基是花花公子,却没有看见,西伯利亚的雪夜,渥伦斯基的凝眸,与安娜,一样真诚。
似乎许多年前,在中国,也有相似的这么一个男子,被人们误解了千年,却没人看见,在他的安娜离开后,作为一个帝王的他数次南征一心求死的决绝。他和主动前往土耳其前线枪林弹雨的渥伦斯基,只是一样的悲情。
我看见,那个身披青衫的男子,眺望着远方,口中,心中,都只嗫嚅着一个字,甄。
那是他的安娜。
他是她的渥伦斯基;只有他们,才可以了解的真爱。
“司马先生,即使是我们,也不能插足。”
似乎又有一个女子,站在我身边,和我一样,淡淡地看着他们,用着事不关己的语调描述着他们的深情。她的眉眼比“安娜”更加凌厉,也更沉稳,给人第一感觉如女中之王。
“仲达不明白娘娘的意思。”我谦卑地朝那个女子低头。
“先生何需明知故问?”那个女子笑了,笑得不屑而纤巧。
司马先生,您知道,子桓心里有一个角落,即便是我,亲近如妻子,又即便是您,尊贵如大将军,也永远无法介入。
一时间,甄,安娜,苏菲?玛索的影像交错重合起来。
“司马,我记得你好像是不喜欢苏菲?玛索的啊?”见我看完电影仍意犹未尽地坐在沙发上发愣,同学好奇地推了推我。
“现在也是不喜欢啊。”我动也不动地回答。
“那你怎么一副很enjoy的样子?”
“没什么。”我有些突兀地忽然站起来,“看得眼睛有些酸了,好困。”
不理一脸迷茫困惑的同学,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拍上门,蒙头便睡。
下雨了。很大很大的雨,如几百支长箭同时穿破人脸颊的滂沱大雨,溅起巨大的水声。霎时间,天地,都是昏昏沉沉的暗。
洪水将一切渲染成一片透白,浓重的雨帘中,一个青衣长袍的男子,依稀可辨。
他撑着一把画有腊梅图案的油纸伞,安谧地孑立与风雨中。在这种雨天,其实撑不撑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而他却执意撑着,保持着挺拔的站姿,似乎在为某个他等待的人树立这个显眼的路标;只是这么静静地伫立,好像这吞噬天地间的大雨与他毫无瓜葛。
“仲达。”
他忽然看到了我,转过头,朝我微笑。
即使是在厚厚的雨幕下,他的面庞,依然清晰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