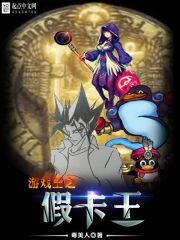君臣戏-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下面传来的只有痛,别的什么也感觉不到,可他从来不让我看,那是我自己的腿脚啊!看一看还要得到别人的允许吗?
他说:“现在包得跟两根大木棒子一样,看了要吓到你,等好的时候再看好不好?免得以后好了想起现在的样子,可能还会后怕呢!”
“就真的成了木棒子有什么好怕的!反正你不给我看就是了。”
“嗯!”
我愣愣望着他,他居然还敢承认!我坐一会也累得慌,连杯水也抬不动,别说要揭开被子看腿上的伤了,对我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
过了几天,我已能坐上几个时辰了,那两个丫鬟伶俐得很,达尔罕不在的时候她们就变着法子哄我开心,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把个本该寂寞的时候吵嚷得热闹起来。
我躺了这么久,奇怪身上怎么没有一点怪味,连达尔罕身上的汗味也比我浓得多,难道是药味熏坏了鼻子吗?
后来她们不在跟前的时候达尔罕才告诉我,我喝的药都是定神的,睡着便不易惊醒,换药洗身都是她们乘着我睡着时候做的,我听了这些,此后见她们便免不了脸红。
她们是两个大姑娘,又不是宦官!
可惜,什么都由不得我说了算。
有一天,她们把我收拾出来,梳头、换衣,却没有给我盘发髻,只在两边耳后各扎一条小辫子,发稍末端倒转过来扎好,结了一个琥珀环在底下。
没有一件是汉人的衣服,不过料子摸起来却都是上好的丝料,只有宽大的外袍像是皮质的,却又是白色的,拦腰扎一条掌宽的红腰带。
她们还在给我小心的套长皮靴,我已经热得要出汗了,忙问:“这是要干什么?”
我又不能走路,穿靴子做什么?
一个丫鬟笑眯眯的说:“单于要抱你上车啊!就是这里到车上的几步路,可他怕你冻坏了脚,所以还是要穿齐。”
上车?去哪里?我想我的脑子也被水泡坏了,总是看到才会跟着想出那么一点来。
她见我不解,误以为是别的,忙解释:“你的脚啊!被冷水冻伤了,不过你别担心!你不是叫痛吗?痛就是还没断了要紧的脚筋,我们鄂族啊最善治疗冻伤的了,每年冬天都有一大堆牛羊要被冻坏……”
“子含又不是牛羊,弄好就一边去。”达尔罕说着走进来,眼光落在我脸上就挪不开了。
两个丫鬟把毡帽塞给他,跑到一边嘀咕:“他和牛羊一样,也是属于单于的嘛!”
我低下头看脚上的靴子,他走到面前半跪下来,摸了摸我垂在胸前的发辫,又把琥珀环捏在手里把玩,“叫她们赶着把衣服做出来是对了,汉人的衣服不耐寒,外面正下雪呢!你以前穿着汉人的衣服我就觉得看着不大好,单薄得跟梨花瓣一样,手一碰就要散开飞到风里……”
我不敢看他,手摸在自己领口,隔着几层衣服还是能摸出来下面有个钱币大小的东西。
他把我的手握住,笑着说:“喜欢我鄂族的衣服吗?穿在你身上怎么也穿不出鄂族汉子彪悍的样子来,倒像个细白皮的小包子……”
“达尔罕!你说谁是包子!?”谁要被这样形容也要气的,牛羊也就算了,我知道在牧民眼里牛羊是最珍贵的,可他!
“就是你爱吃的那种啊!角门外东向那第一家包子铺的,两个铜钱一个,别家的你只吃一个,这家的你可是要吃三个才满足。”他恬脸笑着。
“你……”怎么还会记得那么清楚,那是几年前的事了。
他揉了揉额角,费神道:“就是记不清是叫福记包子铺还是叫……富记包子铺了。”
心里暖暖的,和身上一样,我抚开他皱着的眉心低笑道:“走吧!不是要上车吗?走吧……”去关外,去鄂尔林的草原,不是被抓去的,是我自己要求的。
他给我戴上毡帽,抱着我出了门,门外的台阶、草木上都落满了厚厚的雪,我眯着眼睛看,下水牢的那天离下雪还早,那天的月季开得正艳,不像今日,都压折在雪下了。
院里院外站着很多和他打扮差不多的人,身形都一样高壮,满头的小辫子,却没有谁像我一样挂着琥珀环。
他们看我的眼里只有好奇,别的什么也没有,见我望过去只会不好意思的扭开脸,还有一个咧开嘴笑,露出满口黄黄的牙齿。
我靠在达尔罕肩头回他一笑,他们就都对我笑了。
车上还是比不得屋里,虽然挂上了挡风的毯子,又烧着一个暖炉,但我的唇色泛紫,达尔罕不用问就知道我冷得慌。
车内垫了厚厚的被褥,车子动起来我只能感觉到轻微的晃动,毫无记忆中的颠簸。
走了半天就歇下来,是在个路边的客栈里,达尔罕不和我同车坐,他骑马,抱我下车时我看到了他的马,那马的头竟比他还要高出一些去!
“想看看吗?”
他转过身,让我对着那匹马,我细看了那双眼睛——温柔得近乎怜悯,于是大着胆子伸手去摸,它突然喷一个响鼻,我“啊”的缩回手,周围的鄂族人都笑起来。
“畜牲!你们这些鄂族的蛮子……啊——”
突然传来骂声,我寻着声音望,却望不透周围铁桶样围着的人群……
突然间我意识到了,这些不是牧民,站得那么整齐,人人腰间都挂着马刀,他们是鄂族的勇士,破雁州关的那些士兵。
达尔罕关切的问:“冷吗?”
耳边还清楚听到别处传来的打骂声,以及鞭子划破空气的尖啸,我把手缩到袖子里说:“嗯,很冷。”
邯州的冬天什么时候这样冷了?
那两个丫鬟跟我同车,早就跳下车跑进去了,等我进去火也生好了,还有满满一桶热水,蒸腾的热气在屋子里迷漫,还真想连头泡进去。
达尔罕脱了他身上的那一大件狐裘,两个丫鬟拿着出去了。
我看她们关门,心里沉了一下,他忍不住了吗?
他蹲在地上小心的脱我的靴子,问我:“早上换衣服的时候她们给你看你的腿了吗?”
我摇摇头,他低着头很专心,我看不见他的神情,只觉得他摒住了呼吸,绒里的袜子慢慢的褪下去,我看见了……不像是活人的腿,从脚到膝盖,全是青灰色的,像石头一样。
他轻轻的用指头戳,还一边问:“疼吗?这里?那这里呢?”
“疼……都很疼,别碰,好疼!”
我还在想办法挪一点,好躲开他的手,他的唇就贴了上来,我的和他的都还带着外面的冰冷,冰冰的贴在一起厮磨。
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忽然大力压过来,我以为我要倒下时碰到了椅背,忙闭上眼,唇上烫起来。
他的呼吸愈发急促了,我抓着他的手臂,绵软的皮袄下,那臂上的纠结肌肉鼓胀着……
太强势了!我受不了的,我这样的身子怎么能承受得住……
正慌着,他放开了我,又低头查看我的脚。
“我以为我来晚了,子含,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一幕,我破了雁州,二十万大军入了关但没有再前进一步,我只想拿雁州跟魏朝皇帝换你,虽然我回去鄂尔林的这几年年年好气候,牛羊都长满了肥膘,积下的粮食足够我们打到邯州的,但是,我怕兵荒马乱的伤了你,我好后悔,要是我没有在雁州停下,要是我一直打进来,在你被关到水牢前就进邯州,你就不会这样了。”
我差点失笑,我可是为了要挡他的大军才闹得下了狱,他不怪我吗?
不会怪的吧!他以前就那么纵容我胡闹,他和昼锦都是这样想我的,只会胡闹而已。
他还在说:“我得到邯州的探子传出消息才发兵,只带了两千人,每人备两匹马,用了十天赶到邯州,跑死了几百匹马……”
他抬起头看我,目光从眉端慢慢的移到唇,不愿遗落了一处。
“还好城里的探子机灵,见你被下狱,一面放了鹰传信给我,一面向魏朝表明了身份,他们要活命的话就不敢杀你。”
原来是这样,照他说的,我在水牢里关了至少十天……昼锦那么恨我吗?那和杀我有什么区别,只是没有写下圣旨而已。
达尔罕又自责起来,好像亲手做错了什么不可挽回的事一样。
“我忘了,在草原上的几年让我忘了邯州人是多狡猾无耻的东西!是没有杀你,可我撞开牢门看见你的时候,你离……已经只有一步了。”
他的眼眶发红,就像我生气时那样,不过我知道他不是在生气,我捧着他的脸吻他长出了胡渣的下巴,再吻他的唇,已经不冷了,我的和他的都很烫。
那些硬硬的胡渣扎着我的手心、手指,我一直睁着眼睛,看他眼瞳里刻下的那一幕。
烟尘滚滚的两千铁骑,慌乱的邯州,火焰里闪烁的皇宫,然后是一重比一重深暗的天牢,最后,是被他撞烂倒进水里的牢门,渐起的水花和荡开的水波碰到了火把下变成灰色的衣裳……
这些都是动着的,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到了那里就静止了,好像被那些会妖法的道人施了定身咒一样,全都静止了——
那是我,已经失去知觉不知多久的我,被绑在黑色发霉的架子上,手腕已经勒得血肉模糊了,却还承担着全身的重量,散乱的发和下面掩盖不住的苍白脸颊,怎么看都像是尸体。
……只要托起脸,就能看到死人才有的黑色血迹,从嘴角蔓延到下颌。
如果爱我,怎么会想这样杀死我……昼锦……
我埋头在达尔罕怀里,死死的抠住他的手臂,比昼锦还要强壮的手臂,要是靠的是达尔罕,再也不会让人那样对我的,他们不同。
他拍着我的背,像是在给我说,更像是在给他自己说:“过去了,子含,都过去了,再也不会有水牢了,你活着,还会皱眉还会说痛,你知道我有多高兴,我以为你的腿保不住了,那时候看着真恐怖,连我都不敢多看,现在慢慢的好起来了,等到开春,我保证你可以下地走路了。”
我在哭,却没有泪水,我不会残废!真好。
达尔罕没有碰我,他帮我脱了衣服抱我到澡桶里,又加水又添火,让我舒舒服服的泡了个够。
他也有不理我的时候,我穿着里衣在床上痛骂:“不要!啊!好痛……不要……”
他自顾自的往手上倒一种味道辛辣的酒,然后很卖力的搓我的小腿和脚,好像拿火在烤一样,痛得我连“死蛮子”都骂了出来。
骂得狠了,外面就传来低沉的笑声,他们别是想到哪里去了吧?
脚上又是一阵剧痛,我忍不住叫:“轻一点唉!用那么大力……啊!住手!啊……”
达尔罕崩着张脸,对我的叫骂毫不理睬,等他弄完,我出了一身细汗,他给我盖上用手炉滚热了的被褥,匆忙的,来不及问罪及抱怨,我睡了过去。
后来在车上才听两个丫鬟说了,那天因为风雪太大,前面的路马车走不过去才停下来的。
也是在那天,她们拿了达尔罕的狐裘改了改,给我在车上御寒,那是以前的大单于给他的唯一东西,本来刚合他用,她们想了办法,把系的带子往下挪了几寸,我用的时候就正好了,把上面的皮领子竖起来还可以挡吹到脸上的风。
我穿得比她们还多,却还是时不时的抖,好生不解。
等到了雁州,又停下来休息了一次,还是达尔罕帮着我沐浴,也还是没放过我,直搓掉了剩下的半瓶酒才撒手,我觉得我是疼晕过去的。
出了城继续向北,在山坡上的时候我坚持要停车看,丫鬟下车问了达尔罕,她们可抱不动我。
达尔罕策了马过来,外面白茫茫一片,可是没有风,也没在下雪。
“外面很冷啊!还是车里好,你受不得风的。”
我不信的瞪着他:“又没有风,况且,我哪会受不得风。”
“固执!”他骂了一声,无奈的跳下马到车边抱我,“要是觉得冷了马上说,这时候再病可是病不起的,前面还有好大的一段路要走。”
我拼命点头,旁的人见我那殷勤的样儿大笑起来,达尔罕把我放到马背上,我紧张得不行,抓着他的肩不放,左右的人靠过来,一边一个扶住我,我见他们笑得脸上发红才撒了手。
他又从车里拿了手炉,才跨到我身后坐着,还不算完,我已经穿着原本他的那件狐裘了,他还扯了他毛毡的披风把我整个儿包在他怀里。
除了眼前的一片地方,我什么也看不见……
“我想看看雁州,没有来过。”我拉他的衣襟,提醒他。
他这才想起来为什么把我从车里捞出来,于是驱马小跑出一截,拉开披风让我看。
“那就是雁州?四四方方的像块砖。”还从来没有在这种地方看过整一座城,我顺着雁州城朝里望。
白茫茫的,哪都是白色的一片,看不出什么界限来分关内关外。
他在我头顶说:“汉人的城不都修得四四方方的吗?”
外面凉凉的,我打了个喷嚏,他立即就把披风拉上了,我大叫:“闷死了,这才像个包子呢!”
他拉开披风把狐裘的领子竖起来,戳着我的脸说:“你啊!身子不好还要折腾,身上冷不冷?头疼不疼?”
哪来那么多毛病?我摇头再摇头,眼睛还朝雁州那边望。
几十万的鄂族骑兵蜿蜒成了一条长龙,在空旷平坦的雪原上缓缓前行,应当不是为了我一个人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