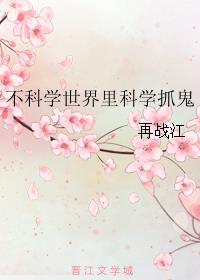科学史及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作-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男睦硐肮摺�
最大的变化是在重新发现亚里斯多德著作的时候发生的。1200至1225年间,亚里斯多德的全集被发现了,并且翻译成拉丁语;与其他希腊著作一样,起先是从阿拉伯语译出,后来才直接由希腊语译出。在后一翻译工作中,最出色的一个学者是格罗塞特(Robert Grosseteste)。他是牛津的校任,林肯区的主教,著有讨论彗星与其成因的论文。他邀请希腊人到英国来,并输入希腊书籍,而他的门徒、方济各会修士罗吉尔·培根则写了一部希腊语法。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文学,而在于神学与哲学,他们想要把圣经和亚里斯多德原著语言的锁钥打开。
这些新知识不久便对当时的争论发生了影响。唯实论仍然存在,但不如从前彻底了,而且稍微离开了柏拉图主义。人们认识到,经过亚里斯多德修改后的唯实论,可以用心理学的术语来加以表述,使其接近于唯名论。但在比较大的问题上,亚里斯多德却为中世纪思想界展开一个新的思想世界。他的一般观点不但更加富于理性,而且更科学,与历来充当古代哲学的主要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大有差别。他的知识领域,无论在哲学方面或自然科学方面,都比当时所知道的宽广得多。要吸收这些新材料并且使其合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而且在从事这个工作时也不能没有疑惧。人们已经深信教会作为天启的接受者与解释者,在学术上是至高无上的,而代表世俗学问的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则是与天启相符合的。因此,要接受新发现的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以及这些著作里包含的科学的或准科学的知识,并且把这些知识与基督教教义调和起来,在学术上需要真正大胆的努力,在最初研究亚里斯多德的时候一时发生惊慌,是不足怪的。起初,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是经过阿拉伯的途径传到西方的。在这个途径中,他的哲学和阿维罗伊派的倾向混合起来,结果成了神秘的异端。1209年巴黎的大主教管区会议禁止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后来,又再一次加以禁止。但是,1225年,巴黎大学就正式把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列到必读书籍的目录里去。
在这个时期里解释亚里斯多德的最主要的学者是多明我会修士科隆的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 of Cologne,1206…1280年)。他也是中世纪里最富有科学思想的一人。他把亚里斯多德、阿拉伯和犹太诸要素组成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当时的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与医学各种知识。在这一工作中,阿尔伯特本人与其同时代的植物学家鲁菲纳斯(Rufinus)等人作出了肯定的贡献。
当时流行的思想倾向可以从阿尔伯特教授亚里斯多德的胚胎学以后发生的情况看出来。亚里斯多德认为一个生物的成胎,母体给它以质,父体给它以形。中世纪的心理注重事物的价值,因而断定男质特别贵重,后来竟形成一种神学的胚胎学,于是灵魂何时进入胎里,就成了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问题。
阿尔伯特的工作,一方面表现出他同他的同时代的青年人牛津的方济各会修士们、格罗塞特斯与培根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直接引导他的有名的门徒圣托马斯·阿奎那形成更有系统的哲学。虽然阿奎那的头脑不象阿尔伯特那样富于科学精神,可是在哲学史及科学起源方面他却十分重要。他继承阿尔伯特的工作,把当时知识的宝藏,不管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加以理性的解释,因而激起人们对于知识的兴趣,并使人们感觉宇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阿尔伯特与阿奎那共同促成了一场思想革命,特别是宗教思想的革命。从柏拉图经过新柏拉图主义到奥古斯丁,人们一向认为人是思想着的灵魂与活着的肉体的混合物,其中两者各自形成一个完整的实体。上帝在每个灵魂里植上一些天赋的观念,其中便有神的观念。这种体系很容易同个人灵魂不死,人们可以直接认识上帝等基督教教义调和起来。
但是,亚里斯多德对于人和认识的问题,提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肉体或灵魂单独都不能是一个完整的实体,人只能看做是两者的复合体。观念也不是天赋的,而是按照几个不证自明的原则(如因果原则),根据感官材料建立起来的。对于上帝的认识,不是天赋的,必须通过理性的与辛苦的推理方能达到。亚里斯多德的体系,虽然在解释宗教问题的时候有种种困难,可是对于外部世界却作出了比较好的解释,因此阿尔伯特与阿奎那接受了它,托马斯更是勇敢地和巧妙地起来把它与基督教教义加以调和。
不过,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虽然同柏拉图的哲学比起来要合乎科学一些,可是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新知识仍然是抵触的,因此当他的著作被人接受、成为权威的时候,它们就在许多年代中阻挡了科学思想从神学桎梏下解放出来,因为学院的世俗学术和罗马教会双方所以都对现代科学的初期发展抱着突出的仇现态度,主要是由于圣托马斯的亚里斯多德主义的缘故。
托马斯·阿奎那
托马斯是阿奎农(Aquinum)伯爵的儿子,1225年左右生于意大利南部。十八岁时他加入多明我会为修士。他在科隆从阿尔伯特求学,在巴黎和罗马教过书,辛劳一生,死于1274年,只活了四十九岁。
他的两大著作:《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与《箴俗哲学大全》(Summa Philsophica contra Gentiles)是为了向无知者阐明基督教知识而写的。他认为知识有两个来源:一是基督教信仰的神秘,由圣经、神父及教会的传说传递下来,一是人类理性所推出的真理——这不是个人的难免有误的理性,而是自然真理的泉源,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就是它的主要的解说者。决不能把这两个源头对立起来,因为它们都从一个源头——神——那里出来。因此哲学与神学必然是可以相容的,一部《神学大全》应该包括一切知识;就连神的存在也可以用推理来加以证明。但是在这里,托马斯·阿奎那就和他的前人分手了。伊里吉纳和安瑟伦在比较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下,要想证明三位一体及化身等最高的神秘。但托马斯在亚里斯多德与其阿拉伯注释家的影响下,认为这些神秘不能用理性去证明,虽然它们可用理性去检察和领悟。因而这些教义从此脱离哲学的神学的领域,而转入信仰范围之内去了。
在他的一切工作中,阿奎那的兴趣都属于理智方面。任何由神创造而具有理性的人,其完全的幸福都在于运用其智慧来默念神。信仰与启示乃是对真理的命题与表述的信念。如果我们以为经院哲学及后来由它产生的正统的罗马神学反对或轻视人的理性,那就完全错了。那是早期的态度,例如安瑟伦就害怕当代唯名论者使用他们的理性。但后期的经院派并不贬低理性。相反地,他们认为人的理性原是为了解和检验神与自然而形成的。他们自称要对整个存在的体系给予理性的说明,只不过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前提有问题罢了。
阿奎那的体系是按照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与科学建立起来的。他的逻辑学,通过它的纲要早已为人熟习。在人们对知识尝试进行理性的综合的时候,他的逻辑学的影响就更深远了。在三段论法基础上,逻辑学可以根据公认的前提,提供严格的证明。这方法自然使人们觉得知识的来源,一方面是直觉的公理,另一方面是权威,即天主教会的权威。这个方法很不适于引导人们或指导人们用实验方法去研究自然。
阿奎那还从亚里斯多德和当时的基督教义那里接受了一种假设,说人是万物的中心与目的,世界可以按照人的感觉和人的心理来描绘。这一切都是亚里斯多德的物理学使然,因为物理学是他的科学中最弱的一门学科。德谟克利特早在现代物理学的见解形成之前就惊人地预言说:“按照通常说法,有甜有苦,有热有冷。按照通常说法,有色彩。其实,只有原子与虚空。”这一理论是与现代客观物理学相符合的。它要透过浅薄的感觉,发现与人无关的自然界的法则。但是,我们知道,亚里斯多德却摒弃了这一切,拒绝了原子的概念。在他看来,物体并不象德谟克利特所说的那样,是许多原子的集合体,或者象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是有质量、惯性及其他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理的特性的东西。物体是一个主体或实体,具有归入某些范畴的特性。首先它是本质,“这不是指一个主体具有的,而是指一切其他东西都具有的东西”;例如人、面包、石头;不过,亚里斯多德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一种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本质性质。其次它有重、热、白等特性;还有不那末重要的是,它存在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这些都属偶有性,比起本质来,没有那样根本的意义,不过在一定的瞬刻内,却都是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十九世纪看来,这一切都好象是无益的,差不多是无意义的,虽然我们可以把这一切说法改造成为一种比较具有现代气味的形态。但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的观点在中世纪的人看来也是同样地奇怪,而他们的心理态度,是产生了重大历史后果的。如果重是一种和轻相反的自然特性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亚里斯多德怎样达到天然位置的学说,按照这个学说,重的下沉,轻的上浮,所以物体愈重,下坠愈速。在这一点上,经院派同史特芬和伽利略发生了争执。不但如此,由于亚里斯多德把物体的根本性的本质与现象、偶有性或种区别开来,在中世纪的人看来,化体理论——1215年以来的一个信条——也就显得很自然了。即令在神秘的新柏拉图主义已经被理性的亚里斯多德派的托马斯主义代替了的时候,中世纪的人仍然这样想。
阿奎那接受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它仅当做一个工作假设——“这不是证明,而是假设”。但是,圣托马斯的警惕却被人忽略了,而地球中心说竟成了托马斯派哲学的一部分。人既然是创造万物的目的,地球使该是宇宙的中心,围绕它旋转的有充满气、以太与火(“世界的火焰墙”)的同心圈,这些圈载着太阳、恒星与行星运行。中世纪的末日审判画说明这种见解怎样自然而然地引导人们想象出这样一个景象:天堂在苍穹的上面,地狱在土地的下面。人们是在基督教教义与亚里斯多德哲学所提供的前提之内,细致而巧妙地制订出这个体系的,只要我们接受这些前提,这个体系就是一个没有矛盾、令人信服的整体。
亚里斯多德的世界永恒说,因为同上帝在时间中创造世界的教义不调和而遭到阿奎那的挨斥,但在其他方面,阿奎那对于亚里斯多德的科学,就连细节也设法使之与当时的神学相符合。亚里斯多德认为凡是运动都需要不断地施加力量。从这一见解中阿奎那推出了一些与当时神学相符合的结论,例如说“天体被有智慧的本质所推动。”这些推论既然被视为业经证明,前提也就更加可靠了,于是全部自然知识就和神学结合成为一个坚固的大厦;在这个大厦中,各部分是互相依赖的,所以对于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或科学的攻击,便是对于基督教义的攻击。
在托马斯派的哲学中,肉体和心灵同为实在,但它们中间并没有笛卡尔首先加以表述,在后来的年代为人们所十分熟悉的那种鲜明的对立。阿奎那根本没有想到去研究现代形而上学所遇到的一些困难,如这两个表面上无法比较的实体之间的关系,或与此有关的问题:人的心灵为什么有可能认识自然。那时还不需要这种分析;四个世纪以后,才产生这种需要,因为当时伽利略已经从动力学的观点证明亚里斯多德的物质及其特性的概念,必须由运动中的物质的观念来代替,偶有性如色、声、味等,并不是物质固有的特性,而仅仅是接受者心中的感觉。十三世纪时这些还是不可理解的观念,其中所包含的困难当然也是毫无意义的。
经院哲学在托马斯·阿奎那手里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这种哲学深入人心牢固而持久。文艺复兴之后残存的经院哲学家是反对新的实验科学的,但是,他们的学说的彻底唯理论却造成了产生近代科学的学术气氛。就某种意义而言,科学是对这种唯理论的反抗;科学诉诸无情的事实,不管这些事实是否与预定的理性体系相合。但是,这种唯理论却有一个必要的假设作基础,那就是,自然是有规律的、整一的。怀德海博士指出:不可抵抗的命运的观念——希腊悲剧的中心题材——经过斯多噶哲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