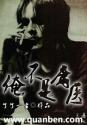八十年代访谈录-反思人文热潮-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事情总要有个过程。八十年代文艺和无产阶级文艺还是个父子关系叔侄关系,与其说是叛逆,不如说是纠缠,同质的东西太多了,非要到九十年代,一种“祖孙关系”才出现。
你比如英达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一百集,其中有个爷爷,退休老干部,语言和思路太经典了,逗极了,所有晚辈都调侃他,这是我见过咱们文艺中第一次以“孙子辈”的角度表述革命前辈,说那是“调侃”、“消解”,其实是老牌意识形态终于被“对象化”了,剧中所有角色,包括那位爷爷,其实全是九十年代对八十年代的“戏仿”。
这部喜剧当初出来时一片批评误解,大家仍然停留在“八十年代”——其实就是七十年代——的集体意识中。英达很聪明,他把这种极度政治化的作品弄成喜剧,弄成家庭剧,国事当家事,可是非常准确。“第五代”导演一点都没有这种敏感,因为他们全是“儿子”辈,长得跟“父亲”太像了。
查建英:《我爱我家》其实是梁左写的。梁左是我的北大同学,可惜英年早逝,不然可能会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当年他算我们班上年纪小的,但有一种人情世故的透彻,绝顶聪明。他父亲是《人民日报》副主编,专写社论的,没人比他对官样八股更熟悉了;他又在北京大杂院住过很多年,对市井小民、胡同串子那套语言也很熟。他的很多作品都是用后者来戏弄前者。《我爱我家》我只看过两集,还是在梁左家他给我放的录像带,我看过他这类作品里最典型的是一个相声,他在那里头一边贫着嘴一边就把天安门广场变成农贸市场了——那还是八十年代写的呢,多前卫啊!他平常说话就这样,比如九九年“十一”前夕我从香港来北京,五十年庆典那天下午,他打电话来聊天,上来就说:“不是我批评你啊,你一个境外人士搞什么爱国主义嘛,这全城封锁咱们也不能出去玩,你在哪儿不是看电视啊,非往这儿扎!”
过一会儿又说:“唉呀国家领导也真够累的,他们肯定站在城楼上心里正犯嘀咕呢,也想跟咱俩这样在家里待着,穿着家常衣服跷着腿嗑着瓜子聊聊天儿,多舒服!”
这是典型的梁左语言。不过我又觉得,在油嘴滑舌的幽默背后,梁左其实有一种掩藏极深的感伤,他有点像个沦落江湖、看破人生的旧文人,对人性极为悲观,这种东西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他的作品里就先要了他的命。他是没有太经过西化洗礼的,生活习惯一概中国式,泡茶馆、打麻将、吃夜宵……生前最迷恋的书是《红楼梦》,你跟他聊天会发现他好多句式都是从怡红院搬来的,把清代破落贵族的白话直接和北京后革命时代的调侃很随便很家常地拌在一起,风趣之极。走前七年他一直在积蓄材料写一本小说,想从民国年代直写到现在;为此他去潘家园淘了不少民国人的日记啊文物啊等等,有一回忽然对我叹息:七万字了,还是觉得不行,但是心力不支,写不动了,得放放。那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我觉得会和他的相声、电视剧不同。我非常怀念他,他本人的性格要比大家看到的那些搞笑作品复杂得多;他太可惜了……
//
…
《八十年代访谈录》之陈丹青(6)
…
我这有点儿说跑题了。我的意思是说,就梁左这一个个案来讲,他五七年出生,血统、经历其实是“儿子”辈,表现形式却是“孙子”,所以有点拧巴,有点人格分裂。王朔的好多作品也有这种感觉。你接着说。
陈丹青:《编辑部的故事》更早进入这种“对象化”,在那部连续剧里,“官样文化”的所有表情姿态成为戏仿对象。
只是等我新世纪回来,很快发现“个人”又被融化了,变成一个期待被策划、被消费的状态,譬如“双年展”啊,出版商啊,音乐包装系统啊,一切变成兑换、交易……真正的,在他周围没有支持系统的“个人”,又变得稀有、脆弱。同时所有人都关心自己的利益,巴望自己尽快卖出去。
美国的个人主义不是这样的。美国盛产包装,商业化,可是美国青年个人就是个人,纯傻逼。我写过两位纽约艺术家,一个从来没成功,一个很有名,可是他们身上没有半点中国艺术家那种群体性格,那种动不动就意识到自己代表什么什么的集体性格。
查建英:好吧,咱们已经说到九十年代来了,这时候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出来了:钱、市场、消费,这一套和八十年代比呢?
陈丹青:事情需要对比。当九十年代的性格出来后,返回去想,八十年代那种集体性、那种骚动——如果咱们不追究品质,那十年真的很有激情,很疯狂,很傻,很土——似乎又可爱起来。
查建英:你倒是借着九十年代才又看到了八十年代的好处……
陈丹青:我当时回去已经不可能在中国地面上感受八十年代那种质感,有质感的是九十年代的种种变化,我第一次回去是一九九二年底,就是我离开中国十一年了,第一次回去,那时整个景观跟八十年代差不多,生活方式也差不多,很穷,住房、车、城市状况,都和现在非常不一样,但我模模糊糊地感到些东西,比如见到崔健、刘晓东、王朔等等,这些新人让我感到一种跟我八十年代同龄人不一样的东西……
之后到了一九九五年,我每年回国,直到二○○○年整个儿回国,这时,九十年代的城市景观、文化景观,渐渐成型,大家发生新的交往方式——直到那时,我才慢慢意识到八十年代:那种争论、那种追求真理、启蒙,种种傻逼式的热情,好像消失了。群居生活没有了,个人有了自己的空间,出路多了,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多,大家相对地明白了、成熟了,也更世故了。似乎有种贯穿王朔作品的,对上一代集体主义文化的厌烦和警觉。你知道,看透爷爷的都是孙子,爷爷们再也管不了孙子了。你仔细回想,长期政治运动时期的人际关系——那种紧张、侵略性、人我之间没有界限——终于被九十年代的人际关系逐渐替代了。
比较让我沮丧的反而是二○○○年以后,那年我回来定居,进入体制,我对九十年代的幻象又破灭了。
查建英:是啊,那回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你,感觉你很激愤,怎么回事?
陈丹青:我发现内在的问题根本没变,那种权力关系根本没变,只是权力的形态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各不一样。我说是个幻象,因为九十年代我接触的实际上是一批个体户,一批幸运的、提前塑造自己个人空间的艺术家。可是二○○○年回来一看,体制内的情形甚至比过去更糟糕:过去集体生活的保障和安全感消失了,自由、自主,更谈不上。所谓竞争机制进来了:西方的竞争是无情,中国式的竞争是卑鄙,是关于卑鄙的竞争。那些成功者的脸上都有另一种表情,关起门来才有的表情。他根本不跟你争论,他内心牢牢把握另一种真理,深刻的机会主义的真理。
当然我还接触不少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他们完全没有八十年代情结,那时他们还是孩子,而我能接触的正好是一些优秀的文艺个体户,受惠于九十年代的社会变化,但整体看,二○○○年以后的中国,无论是体制内体制外,八十年代可爱的一面荡然无存。我曾经嘲笑的东西忽然没有了。生活的动机变得非常单面、功利。
查建英:北京已经不是村子了。
陈丹青:但还不是真正的大都会。
查建英:大省会吧,一种杂七麻八、不伦不类的状态。
陈丹青:在文艺创作中,八十年代文化激进主义那种好的一面,已经消散了,我向来讨厌文化激进主义,但那种激情,那种反叛意识、热诚、信念、天真……都他妈给大家主动掐灭了,活活吞咽下去了。
查建英:为什么?
陈丹青:表层原因大概就是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查建英:表层和底层是连着的。
陈丹青:社会结构变在哪里呢?八十年代那群人其实全是各种“单位”里的官方艺术家。一切都是体制内的吵闹、撒娇——政治撒娇——这种“单位形态”甚至和“文革”时期没有太多不同,国家单位大大小小的悲剧都透着一股子喜剧性。可是九十年代,即便是体制内的文艺圈也受惠于太多体制外社会空间的好处。就是说,体制更强大了,空间更多,更有钱,它同时既是单位又是公司,既是官员又是老板,当然我指的是体制内把握权力资源的角色……在经济层面你很难划分体制的界限,整个体制整过容了。到了新世纪,所有官家早有了私产,所有官差同时是私活儿……
//
…
《八十年代访谈录》之陈丹青(7)
…
房子、手机、车、宾馆、酒吧、小姐、歌厅,这一切重新塑造了大家,情形却反倒和“文革”初期很像:一大群新面孔,新的权力分配,新的秩序和格局:一群人得道了,一群人出局了,我发现许多八十年代的正宗左派失落了……总之,牌理牌局全变了。
查建英:嗯,老树开新花,有时候会给人一种奇怪的妖艳感。老左失落,新左脱颖而出,带着第二代——或者按你的看法应该是孙子辈——的精明、阴柔,老马变新马,在新牌局上驰骋起来了——我可能有偏见,我总觉得其中有些人的身姿看上去更像甩马蹄袖。实际上,在很多后社会主义或者叫后集权国度里,苏联、东欧,都发生了类似情况:社会转型使得人文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有一种普遍的失重感,他们的工作原先在政治化的、社会变革的环境下获得过一种夸张的意义和重要性,他们一度是站在广场中心的社会良心和公众代言人。但在新的技术官僚、消费文化、经济专家的时代里,他们突然感觉靠边站了,不在舞台中心了。这时候,性格的力量凸显了,出现分化,有人会坚持,另一些人会调整,还有人会寻求新的资源,抓过一副新牌来打。整个九十年代你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迷惑、变脸、转向,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生态。
陈丹青:我一点不愿说九十年代不好,真正的变化在九十年代发生了,目前的空间非常珍贵,但这一切对国家、社会,都好,对艺术不好。艺术家的呼吸应该不合实际,不然他会在“实际”中闷死。我在美国、欧洲看见的情形是:人家也经历大变革、大时代,各种形态更替变化,也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相对美国六七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美国称八十年代是他们的现实主义时期),但社会始终会留空间给艺术家继续做梦,会有一小群知识分子贯穿自己的人格,不被闷死,他可能再也不是主流,但不会像中国知识分子这样忽然中断,集体转向,集体抛弃不久前的价值观,接受新的价值观。
我觉得中国常会有这样阶段性的发作:同一群人,忽然颜色变掉了,难以辨认了。
在西方,社会留给知识分子的路其实也相当窄,但它会让你延续下去,只要你愿意疯狂、傻逼,你会有空间、有可能。在纽约有很多小众,他们完全是选择自己的方式生活,和时代格格不入,但在中国你跟社会与时代格格不入?你敢吗?你做得到吗?
中国人非常会自动调节,中国人的自我调节、自我蜕变的能力真他妈厉害,特别会对人对己解释调节的理由。我回去见到的大部分人还是八十年dai kao相识,都完成了自我蜕变,他们未必自觉到这一点,但变得非常世故,非常认输认赢。有人会变得很消沉、很懒、无所谓,有人蜕变得十分漂亮、彻底:他变成官,变成商人,其中最能干的既从政又经商,名片头衔是双重身份。我在美术界的同龄人或晚辈,凡是八十年代比较聪明的,几乎都是大大小小的官员。没当成官的,要么是年龄到了,要么曾经明里暗里争取过,败下来,郁郁寡欢,看得很破。
查建英:正是这种潮起潮落之时,最能见出一个人的真性情。就像古代贵族养士,一大群门人、侠客,快马轻裘花团锦簇时大家一个样,可一旦这家族倒了血霉,立刻你就看得出谁是忠义之辈、谁是投机分子。我在《乐》编辑部开会时谈“八十年代”这个选题,有人就说:八十年代的人到现在有两种,一种是悲壮,另一种是得意。
陈丹青:两种我都不认同。为什么不能有第三种——你还是你,你和社会一起蜕变,但值得珍惜的品质你一直带在身上,我得说,很少还能见到这样的人:他在成长、变化,但不会到了一个不可辨认的地步。你说的悲壮、得意,都属于不可辨认:用不着这么消沉,用不着这么得意。人格健全,起码的品质是“宠辱不惊”,悲壮、得意,都是“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