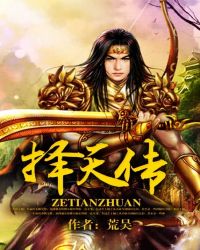爱因斯坦传-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个孤独的和向往孤独的观察者也是社会正义的狂热捍卫者。在同人们交往时思想开朗、诚挚爽快,同时又急不可待地渴求人们(无论是偶遇的交谈者、朋友、家人)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去。爱因斯坦的形象显得非常矛盾。可是就在这些矛盾中,你总可猜测出一种深刻的和谐。
首先,把“观察者”一词用在爱因斯坦身上要有重大保留。这个词可能更接近于“纯粹描述”的维护者,尽管不完全相同,事实上,每个学者都不是停留在现象论的立场上。爱因斯坦是一个“严格实验”的大师,他对自然界施行穷根究底的盘诘,强调科学概念的能动性,他不是通常意义的观察者。不是克服直观的“显然性”,不是深入到只有借助于积极的实验才能加以判断的诸过程的世界中,还算什么相对论呵!对爱因斯坦来说,认识过程——这就是干预自然界的过程。它同用人们生活的理性和科学的方法进行的改造是不可分的。追求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是探索世界的客观的理性、秩序性、规律性、因果制约性的结果。从对宇宙和谐的强烈追求中生长出一种“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但是,日常交往和对人们的日常帮助很少使这种兴趣和这种感情得到满足。还在20年代,爱因斯坦本人就说过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看出他对孤独的向往已经同爱因斯坦的巨大的社会积极性结合在一起了。
科学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交错结合,对科学的新的社会功能的广泛理解或者即便是感觉,在科学界还是属于未来的事,其实是不太遥远的未来。也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就像在物理学本身的问题上一样,爱因斯坦在20年代和30年代同数百个物理学家打过交道,这些物理学家在本世纪中叶比这大得多的程度上对早在20年代使爱因斯坦感兴趣的问题感兴趣。
爱因斯坦一生中的普林斯顿时期有一个特点,就是明显地缩小同“亲者”的直接联系,并同样明显地扩大同“远者”(远离爱因斯坦职业兴趣的环境)的联系。在30、40和50年代,爱因斯坦对占压倒多数的物理学家感兴趣的问题置身事外。他在搞极其复杂的数学理论,然而它们是服从于一个在普遍性和困难性方面硕大无比的任务。爱因斯坦致力于建立统一场论,在这种理论中根据统一的规律得出粒子的所有的相互作用以及粒子自身的存在。这一想法的实现得不到物理学家们的赞同,外行人又一窍不通,并且整个说来连爱因斯坦本人也不满意。但这一想法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在彼此更替的具体的解题方案十分复杂的情况下,始终存在一个普遍公式:世界是统一的,世界是合乎理性的,世界服从于存在的统一规律。爱因斯坦的这一公式是同范围硕大无比的物理和数学理论概括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并不妨碍广大公众猜测这个想法之伟大。
爱因斯坦对这个非常广大的听众的感情越来越强烈了,这些听众不理会细节和专门问题,但追求宇宙和谐的思想。
相反,爱因斯坦的直接意义上的“亲者”却越来越少了,在这方面,爱因斯坦感到自己非常孤独。
到普林斯顿后不久,艾尔莎的大女儿伊丽莎在巴黎去世。自从大女儿死后,艾尔莎一下子变得老态龙钟,她撇不下女儿的骨灰,把它带回了普林斯顿。玛戈尔陪着她。不久,艾尔莎的双目出现了病态。
这是心肾严重疾患的症状,艾尔莎卧床不起了。玛戈尔曾离家几天去了一趟纽约,回来后发现自己的母亲完全变样了。爱因斯坦非常沮丧,本来苍白的脸色更加苍白,眼神充满无限哀伤,他对玛戈尔说:
“你离家这几天,她差一点就放下武器,离我们去了。”
艾尔莎的病情越来越坏,爱因斯坦整日陪着她。艾尔莎对此倒感到欣慰。她对友人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对于他这样珍贵,现在我为此感到快乐。”
爱因斯坦在离蒙特利尔不远的湖滨租了一幢美丽的旧房屋度过夏天,他又开始扬帆游弋了。艾尔莎在美丽的加拿大森林中觉得身体稍好一些,她的全部心思像往常一样全放在丈夫身上。她写信给友人说:
“他处于最佳状态,最近又解决了一些重要课题。过许多时候,人们将掌握他所作的一切,并开始加以利用。他自己认为,新的成果是他所创造的一切东西中最宏伟和最深刻的东西。”
后来,艾尔莎的病情急转直下。1936年12月20日,艾尔莎去世。
爱因斯坦继续过着像从前那样的生活。他常在普林斯顿用红色砖块建造的房子之间的林荫道上散步,这些房子使人想起古老的英国。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研究统一场论的数学工具。但爱因斯坦变化很大。有一次,还在普林斯顿,艾尔莎就说过:“由于受内心渴望与外部作用的支配,我们全部与年俱变……。相反,阿尔伯特却犹如童年时一样。”但实际上,爱因斯坦在30年代初已丧失了往昔的生活乐趣,而现在,艾尔莎死后,他更时常流露出孤独感和忧伤感。
这种感情在40年代更增加了,爱因斯坦在致朋友们祝贺他1949年3月70诞辰的回信中,充满了这种感情。当时,他做了胃部大手术后刚康复。幸好,手术引起了各种疑虑没被证实,但是他长期都很虚弱。爱因斯坦的身体状况并不妨碍他惯常的幽默、诚恳、对周围事物以及首先是全力以赴地研究统一场论的具体问题的兴趣,但总的情绪是忧郁的。
1949年3月底,爱因斯坦在回复索洛文对他的贺信时说:
“您那由衷的来信使我十分感动,同由于这件令人烦心的事寄给我的无数别人的来信相比,您的信完全不同。您以为我心满意足地回顾着我一生的劳作。靠近看却不然。没有任何一个概念其稳定性是我深信不移的。一般说来,我并没肯定我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当代人认为我是一个邪教徒,同时又是一个反动分子,真是活得太长了。当然,这是一种时髦和短见而已,但确有一种不满情绪从我内心不断滋长。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一个人有批判的头脑并且是诚实的,而幽默和谦虚将不管外界的影响经常制造一种平衡……”
上述信件,既可以说明在写成它的瞬间爱因斯坦的情绪,又可以说明思想家整个一生中内心和创作的一般特点。主要一点是:对研究统一场论的结果不满,但同时,这封信也说明了爱因斯坦的全部创作道路。爱因斯坦不仅同那一劳永逸地阐明绝对真理的先知的模样相距甚远,甚至他的科学思想的内容本身就排除了它们的绝对化。批判的头脑、诚实、谦虚和幽默——所有这些反教条主义的力量与这一内容是相吻合的。因此,在这个普遍重新评价价值的时代,爱因斯坦的理论所引起的共鸣才如此广泛。
但是,对价值的重新评价并不意味着抛弃价值,相对性不是绝对的相对主义,它本身也是相对的,批判的头脑、谦虚、幽默不会导致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似的否定。真正反教条主义的思想不会使否定本身教条化,它创造着永恒的价值,不是静止不动意义上的永恒,而是在变化着的形式中守恒意义上的永恒。
爱因斯坦的这个总的立场就其本质是高度乐观主义的,但站在这立场上不可避免地产生动摇、怀疑、不信任——一切把活生生的、探索的思想与刻板公式区别开来的东西。爱因斯坦欣赏的是单值的和清晰的反映世界。他理解世界图象中的中间色和半阴影,但不是它们,而是精确的画图给他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当半阴影闯入画面的时候,画图就不再是可信的、单值的和精确的了,这就使他不满。相对论的精确画图和量子力学的半阴影之间的冲突的心理方面就在于此。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爱因斯坦由于一再失去亲人,心理上的张力松驰下来。他们使他回忆起早在30年代去世的朋友们和战友们。爱因斯坦这时常常追忆起1933年自杀而死的埃伦费斯特。爱因斯坦坚持认为,埃伦费斯特的自杀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两代人的科学兴趣之间的冲突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乃是科学向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和科学家能够找到的答案之间的冲突的结果。埃伦费斯特自杀的直接原因纯系私人性质,但更深刻的原因却在于科学家的悲剧性的不满足。
与埃伦费斯特相比,爱因斯坦是乐观的。科学的要求——建立统一场论——和单值的、清晰的答案的可能性之间的脱节并没造成像任务和解决之间的脱节在洛伦兹、尤其在埃伦费斯特身上那样的悲剧。爱因斯坦的乐观主义是深刻有机的。它是同坚信世界的和谐与可知性相联系的。在1916年建立相对论所克服的困难,和建立统一场论的更加艰巨的而且是没有克服的困难,给爱因斯坦带来了不少痛苦的感受,但是他有不可动摇的信念:科学的道路无论多么复杂、紊乱,它们终将达到与存在之实际和谐相符的认识。爱因斯坦的精神世界不像一个平静的湖面,它更像海面,在它上面翻动的不只是涟漪的鳞波,而且还有汹湧的骇浪。在海面底下大洋深处,潜藏着尚未被任何风暴掀起的深流。这些风暴曾有过,爱因斯坦不可能是永远安祥的天使,就像人们有时把歌德看作是天使那样。当爱因斯坦写下在建立统一场论中碰见的“数学烦恼”和在不可能使统一场论达到可以同观察进行比较的程度的时候,这不仅是紧张的思索,而且是意识到了的问题,然而又是找不到答案的真正的思想烦恼。在普林斯顿时期,爱因斯坦一再回忆起埃伦费斯特悲剧的原因就在于此,并且常常和人谈起埃伦费斯特的事。有人回忆说:
“他怀着激动而宽容的感情说起这件事,因为他自己的也感受过类似的冲突。在同现代思想相联系的幸福年代里形成的悲剧,现在愈来愈突出了。这不是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其中一代人代表大胆的思想,而另一代人维护旧的东西,像一块被舍弃在道路边上的静止不动的石头。爱因斯坦的悲剧是这样一个人的悲剧,他不顾年迈体衰走着自己的愈来愈荒僻的路,在这期间几乎所有的朋友和青年都声称这条路是不会有结果的,并且是行不通的。”
正是这种感觉使爱因斯坦追忆起已故的友人们。其中也包括居里夫人,在她逝世以后,爱因斯坦曾写道,她的道德面貌也许比发现镭对科学的影响更大。爱因斯坦说:
“领袖人物正直的道德品质对于当代和历史进程来说,也许比单纯的智力成就具有更大的意义。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伟大的品格,也远远超出了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
对已故的友人和对他们的精神上的悲剧的回忆,唤起的不只是安详平静的忧伤。这些精神上的悲剧是高度的道德纯洁性、对真理毫不动摇的忠实、对人们的同情的证明,这些品质令人对科学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信心。居里夫人属于那样一种人,他们在自己周围似乎形成了一个力场,它把周围的人们都引到共同的思想兴趣上。
“我有一种巨大的幸福,就是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毫无波折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向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少有的。她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极端谦虚,从不自满。人类社会的严酷和不公平使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她的这种严肃的外貌是无法用人为的努力来缓减的。”
现在,过了若干年,科学殉职者的名单上又增添了一个名字——同样崇高的思想力量的象征:1947年初,爱因斯坦获悉朗之万逝世。
爱因斯坦写信给索洛文说:
“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之一,他高尚圣洁而且才华出众。”
也是在这几年中,爱因斯坦不得不目睹自己的妹妹玛娅慢慢地衰逝。
玛娅长得极像爱因斯坦。她于1939年从佛罗伦萨来到了普林斯顿。玛娅同她的丈夫曾住在佛罗伦萨,为躲避法西斯迫害,玛娅的丈夫到了瑞士,而她决定去看哥哥。
在普林斯顿,人们惊奇的是,兄妹二人不仅容貌相像,而且说话的语气、面部的表情,甚至说话的方式——“孩子般的、但同时是怀疑的态度”——都惊人的相像。
1947年,爱因斯坦写信给索洛文说:
“我妹妹主观上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已经处于下坡路上,这是一条把她带到不可复归的地方去的路。”
在随后的一些信件中,爱因斯坦叙述了玛娅恶化了的健康状况。他在她的病塌前度过了许多时光,他读书给她听,其中有一些是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1951年夏,爱因斯坦的妹妹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