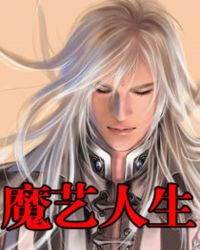季羡林先生-第6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有点形而上学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我的嘴。”季羡林这种关于坏人的看法,也许欠缺理论基础,也许会遭到生物学家、伦理学家们的质疑,但是它符合生活实际,尽管目前科学还不能证实它。而且许多人都会有同感,只是还没有人像他这样直言不讳地说出来罢了。
最后,再来谈一谈他做人处世的第三条原则:处理好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平衡的关系。
每一个与季羡林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性格的平和、宽厚与朴实。他从不疾言厉色,也从未见他发过火,骂过人,抱怨过什么事。一般人看见他平时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样子,会觉得他是一个刻板而枯燥无味的人,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正像许多了解他性格的人所说的,他就像一个“铁皮暖瓶”,表面上严肃得有点让人敬畏,内心却是滚烫的。同他谈话,你才会了解到他的睿智与幽默,听到他发出宛如孩子般天真的笑声,看见他露出宛如孩子般天真的笑容。从表面上,你永远不会看出他内心有什么痛苦与烦恼,似乎他永远安详、恬静,像一潭平静的池水。事实上,他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一点也不比常人少,甚至比常人要多得多,只不过他从不对别人说起而已。比如,1999年,他在一篇叫《世态炎凉》的短文中写道:
…
仁者寿(3)
…
我已到望九之年,在八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一波三折,好运与多舛相结合,坦途与坎坷相混杂。几度倒下,又几度爬起来,爬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可真正参透了世态炎凉的玄机,尝够了世态炎凉的滋味。特别是十年浩劫中,我因为胆大包天,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戴上了种种莫须有的帽子,被“打”成了反革命,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至今回想起来还毛骨悚然的折磨。从牛棚里放出来以后,有长达几年的一段时间,我成了燕园里一个“不可接触者”。走在路上,我当年辉煌时对我低头弯腰毕恭毕敬的人,那时却视若路人,没有哪一个敢或者肯跟我说一句话的。我也不习惯于抬头看人,同人说话,我这个人已经异化为“非人”。……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我不但“官”复原职,而且还加官晋爵,又开始了一段辉煌。原来是门可罗雀,现在是宾客盈门。你若问我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当然是有的,一个忽而上天堂忽而下地狱,又忽而重上天堂的人,哪能没有想法呢?我的想法是:世态炎凉,古今如此。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有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这就是他在遭到那么多大劫难后,仍然能够保持心理平衡的“秘诀”。这“秘诀”其实非“秘诀”,不正是孔子当年在回答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说的“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恕道”的永恒意义。孔子这句话,世人皆知,不是什么“秘诀”。但是,世人皆知,并不等于世人皆能做到。能做到的人,从来就是很少的,尤其在今天。
当然,一个人除了政治上受迫害,会使心灵遭受极大痛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同样会使人心理失衡,比如权力、地位、金钱、死亡等等。季羡林从不追求权力、地位和金钱,这是人所共知的。对于死亡,他的坦然和超脱,简直使人吃惊。他曾开玩笑说:“我是曾经死过一次的人。……从l967年12月以后,我多活一天,就等于多赚了-天,算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也就是多赚了三十多年了,已经超过了我的满意程度。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我随时准备着开路,而且无悔无恨。……我自己的确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极其自然的事。连地球,甚至宇宙有朝一日也会灭亡,戋戋者人类何足挂齿!”(《谈老年》)一个连死亡都参透了的人,还有什么事情能使他痛苦和忧虑呢?
中国古代的两位圣人:孔子和孟子,都是长寿之人。孔子活了七十三岁,孟子活了八十四岁。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寿命,算得上是长寿纪录了。这两位圣人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孔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知者乐,仁者寿。”季羡林长寿的“秘诀”,大概也就在一个“仁”字上吧!
…
辉煌的学术成就(1)
…
如果用百米赛跑来比喻季羡林一生的学术研究历程的话,那么,可以说六十七岁(1978年)以前,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和干扰,只跑了二三十米;六十七岁至今(2002年)的二十四年时间内,则跑完了最后的七八十米。而在最后的七八十米跑中,从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则是他最后的冲刺阶段。所以他说:“我的学术研究冲刺起点是在八十岁以后。”在这最后十年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学术著作:《糖史》、《吐火罗文译释》和《中国佛教史·龟兹与焉耆的佛教》。这三部巨著的完成,了却了季羡林平生的心愿,也可以说给他六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说到季羡林写《糖史》和《吐火罗文译释》两部书,倒有一些值得一提的事。
季羡林写《糖史》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引用别人的著作甚至观点,不可避免。引他人的著作和观点,必须注明出处,这是起码的学术道德,季羡林决不敢有违。可是,季羡林所需的资料都在古书中,这些书现在尚未输入电脑。他只能采用最原始,最笨,可又决不可避免的办法,这就是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砂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材料。为了写《糖史》,他用了两年时间,天天跑北大图书馆,查《四库全书》,硬是把一部《二十四史》翻了一遍,详细摘引出其中的宝贵资料。他在回忆这段工作时写道:
我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季羡林人生漫笔·我的学术总结》
在这两年中,季羡林一直沉迷于书山书海之中,不但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健康,也忘记了燕园的旖妮风光。他写道:“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燕园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人视为奇观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是书香。”季羡林这种忘我的治学精神真可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了。
《糖史》写作完成以后,他又着手《吐火罗文译释》的写作。这时,他把阵地从大图书馆移到家里。“运筹于斗室之中,决战于几张桌子之上。”《吐火罗文译释》也不是一座容易攻克的堡垒,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资料,而且多是国外的资料。没有办法,他只好向海外求援。现在虽然号称为信息时代,但是季羡林要的资料多是刁钻古怪的东西,一时难以搜寻,只好耐着性子等待。等得不耐烦时,心里经常像火烧油浇一样,却毫无办法,只能听天由命。如此又熬了一年,才完成了《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写作。
在完成《弥勒会见记剧本》后,他长吁了一口气,本想休息片刻,没想到《中国佛教史》的写作任务又找门来。其中“新疆卷·龟兹与焉耆的佛教”目前国内只有他一人能写,推辞不了。只好又拿起笔来,继续战斗下去。
耄耋之年的老人,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焚膏继晷”地进行学术研究“冲刺”,完成了几百万字的重要学术著作,这件事无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在世界学术史上,恐怕都是一个奇迹,不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从1978年至2002年的二十四年中,不计散文、杂文、序、跋、翻译,专就学术著作而言,约略统计,季羡林撰写了二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一部学术著作。这十一部著作是:《初探》《校注》(合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敦煌吐鲁蕃吐火罗语导论》《糖史》《吐火罗文译释》等。这些论文和著作涵盖的内容包括: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2、吐火罗文;3、印度古代文学;4、印度佛教史;5、中国佛教史;6、中亚佛教史;7、糖史;8、中印文化交流史;9、中外文化交流史;10、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12、德国及西方文学;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等。
看了上面长长的书单和广博的内容,谁都会惊讶不已。凭一个人的智力和精力,在二十四年里竟能写出如此浩繁而艰深的学术著作,简直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何况,其内容又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学、美学、宗教、文化交流,甚至科学技术,真是好一个“博”字了得!诚如周一良先生在《序》中所说:“羡林兄在十多个文化学术领域或层面的成就和乾隆皇帝号称‘十全武功’的军事成就相比较,不是光怪陆离、丰富多彩得多么?”
…
辉煌的学术成就(2)
…
在这里不可能对季羡林的学术成果作全面详细的评介,既为篇幅所限,也非笔者能力所及。只能举其荦荦大者,略加介绍而己。
1、《糖史》
《糖史》的写作始于1981年,最终完成于1998年,是季羡林至今为止用力最勤、篇幅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国内编;第二编为国际编;第三编为结束语,共计七十三万余字。
季羡林不是科学家,对科技可以说是个门外汉,为什么竟然写起看似科技史的《糖史》来了呢?他说:“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这是因为在“糖”这种全世界人天天食用的食品背后,隐藏着一部遍及五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史。这部历史非常复杂,非常曲折,又非常有意义。通过研究“糖”在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便可以揭示出人类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既然是写《糖史》,完全不讲科技方面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季羡林的《糖史》重点始终是放在文化交流上,在这一点上,他的《糖史》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有所不同的。
季羡林写《糖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包含了一些偶然性的因素。
早在1930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便开始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即所谓印欧语系的语言),表示“糖”这个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ere,俄文是caxap,其他语言也大同小异。这些字都是外来语,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a。根据语言流变的规律,一个国家没有某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从外国输入,常常连名字也带了进来,在这个国家成了音译字。在中国,此类例子就多得很,比如:咖啡、可可、啤酒、苹果派等,举不胜举。“糖”借用外来语,就说明欧洲原来没有糖,而印度则有。实物同名字一起传进来,这就是文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