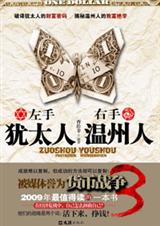温州评判-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烁鋈私赡苫狙媳O战鹬贫取�1991年3月底,温州市人民政府颁发了《温州市企业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1991年7月,温州成立社会保险事业局,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身份的企业和职工实行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制度、统一管理,提前实现国务院提出的“广覆盖、四统一”计划。多年来,在国家财力支持较少的情况下,依靠社会力量,开展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率先实行全社会一体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第三章 风流温州风流者九:打造信用温州
一段时间,温州货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皮鞋因质量问题在杭州武林广场当众被焚。乐清柳市被《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披露为是假冒机电产品的重要发源地。质量问题摆在温州人“二次创业”上最突出的位置。1994年5月,温州召开质量立市万人动员大会,不惜牺牲GDP,打假扶优。1994年10月7日,温州市人民政府制定了《温州质量立市实施办法》细则。这是中国第一个政府制定的质量立市法规。
在这个文件中,有“两招”被人们广泛引用:一是实行“连坐制”,企业出问题,同时追究各级政府、分管部门以及企业负责人的责任;二是对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者,一次重罚,再次则驱逐出“业主”队伍,五年内不准在温州注册任何企业。
如今,温州已经拥有15个中国名牌产品,7个中国驰名商标和42个国家免检产品。
在2001年4月召开的温州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上,当时的温州市市长钱兴中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信用温州”的说法,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企业信用、个人信用、政府信用为主要内容,以建立健全信用系统、信用制度、信用文化为工作重点的信用建设活动。市委、市政府通过了信用温州建设的总体方案,出台了《温州市企业信用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市人大、市政协分别作出了《关于加快“信用温州”建设的决议》,并建立信用温州建设领导小组、信用中心,成为中国第一个建立信用系统工程的城市。
第四章 家族温州温州一大“怪”
986年面世的法国年鉴派史学巨著《家庭史》上有这么一段话: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家庭是最古老、最深刻的情感激动的源泉,是他的体魄和个性形成的场所。通过爱,家庭将先辈与后代系列的利害与业务结合在一起。从这方面说,似乎可以将家庭与经纱相比,由天性在织布机上将它整理好,以使社会料子得以织成。”
家庭是一个组织。它编织着忠实性,并将一代又一代连接起来而成家族。
在中国这个古老的社会里,家族是棋局里的棋子。这是一盘永远没有结束的棋局。
对于“温州模式”这个从家庭工业里成长起来的经济格局来说,家族更是一个抹不开的话题。
随便走进温州一家企业,都能找到家族的影子。在温州企业的组织结构中,总有亲戚朋友这类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温州吴桥工业区一条弄巷里的挺宇集团,是一家生产阀门、防暴电器等产品的企业。这是一家非常典型而且非常有意思的家族企业。
在这家企业里,父亲潘挺宇是董事长,母亲徐文清是办公室主任,大女儿潘佩聪是总经理,儿子潘叶雷是副总经理,二女儿潘佩芳是财务经理,二女婿林肖是销售经理,大姨徐小清是办公室总务,外甥邵靖海是采购主管。据说唯一没有进入公司管理层的大女婿,是他自己家那间父子公司的总经理。
温州尔乐工贸公司,也是一家非常典型的家族企业。这家企业跨行业运作,涉及的行业有服装、面料、干燥设备、磁力泵等。其管理形式是主要家族成员分块管理:父亲王兴乐任董事长把握大方向,母亲陈光珍经营面料,大儿子王战胜管服装经营,二儿子王战文管服装以及面料等的进出口贸易,小儿子王战顺管服装生产,几个儿媳妇分别配合丈夫各管一块,管干燥设备的则是表弟潘定福,管磁力泵的也是沾亲带故的老朋友朱培元。王兴乐的几个弟弟也和这家企业有密切的关系。四弟是磁力泵的材料供应商,在杭州落户的三弟前些年也来到温州,管新厂房的基建。就连大儿媳的娘家人也参与了服装生产管理。
温州吉尔达鞋业公司,父亲余阿寿是企业的创始人、董事长,儿子余进华是接班人、总经理。
在温州拥有二十多家的连锁店的桂香村食品公司,丈夫马建伟是董事长,妻子陈建瑜是总经理。夫妻双方的家人都拥有企业的股份,并参与具体经营。
……
如此“父子企业”、“父女企业”、“夫妻企业”的例子,在温州比比皆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温州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家族企业集群”。
按照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对“家族企业”的定义——“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阶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人员的选拔方面。”——来看,温州的企业几乎都属于家族企业。
1993年,温州有关部门曾对3万多家股份合作制企业进行一次摸底,得出了83%企业是家族企业的调查结果。上述钱德勒概念中,家族企业并不是指由家族成员掌握全部所有权和经营控制权,而是一种大部分和基本掌握上述两种权利的企业组织形式。那么,后来温州众多通过公司制改造的所谓“有限责任公司”也难离家族企业这箩筐。
云南有“竹筒当烟袋”、“这边下雨那边晒”等十八“怪”,温州难找非家族企业,也真可算是温州一大“怪”。
第四章 家族温州温州家族企业的成长路径
“国之本在家”,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家族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国人的行为模式。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山地,“天高皇帝远”,历来宗族观念十分浓厚。在农村,一直有修宗谱的习俗。尽管在文革期间,破四旧之风极盛的时候,还有人偷偷摸摸去修宗谱。
温州人爱拉关系。不相识的人见面,总要套出一些亲戚关系来。远的、近的都无所谓。温州人骨子认定熟人好办事,亲戚好办事。
甚至,妯娌、婆媳之间吵架也会蹦出一句:“你欺负我娘家没有人呀!”因为娘家人总会帮自己的。
这就是温州人的“处世哲学”。所以,在农村,为了亲友的利益而引发的宗族之间的械斗也时有发生。
故而,从地域文化角度来分析,改革开放后温州形成壮观的家族企业集群也就不怎么怪了。
其实,家族企业也并没有什么好“怪”的。全世界企业中有80%是家族企业,特别在华人社会,更是枝繁叶茂、见怪不怪了。只不过,中国的制度使大多数企业都是从国有或集体企业起步,家族制特点不甚明显。而温州家族企业不仅数量大,而且规模相对较小,所以相比之下就显得另类了。
可以说,温州家族企业的崛起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但也绝非偶然。
温州模式的“细胞”在于家庭作坊,这种农村工业化过程是在整个经济体制转轨的同时进行的。由于体制上并未认可,所以,温州人只有暗地里做。他们在发展上首先遇到了资金的困难,无法取得政府金融机构的支持,首先想到的是谋求家族成员的支持。
瑞安韩田村是汽车摩托车配件生产基地。这里家家户户靠经营汽车摩托车配件起家,现在是有名的富裕村。在创业阶段,村民中90%曾向亲戚、房族、朋友借过钱。
在温州民营经济的起步阶段,家庭家族成员是企业启动资金的重要来源。
那时候,温州很流行“呈会”。这种“会”是民间融资形式,是建立在亲戚、朋友关系上的一种经济互助形式。很多企业在资金周转困难的时候,往往通过这种民间力量筹到了钱,解决了燃眉之急。但这种“会”不仅仅是纯粹的友情互助,还兼有市场成分。
另一方面,企业的成长和产业的扩散也通过家族这个渠道。温州的产业是轻工产业,具有很强的复制性,竞争激烈。当一个青年人在面临就业问题时,首先考虑到是学一门手艺,而最好的途径是向族内某个有手艺的前辈学习。从经营者角度来讲,他也不希望自己多一个竞争对手,而最好的办法是把手艺和经验传授给自己人。因此,温州每一家新的家庭作坊出现的背后,往往很多是向自己的亲戚学了本事后,才独立经营的。
吉尔达鞋业公司董事长余阿寿曾带出了16名徒弟,现在有15个徒弟都自己办了皮鞋厂。
韩田村一家企业的几个股东就曾达成一个默契:凡亲戚来厂学手艺,必安排关键位置,让老师细心教导,而一般职工则严禁接触核心技术;有亲戚到厂里进货开店,第一趟都赊货给他作本钱。
再从产业看,温州的轻工产品很适合家族企业生产,家族企业灵活的机制使产品进入市场的成本大大降低。温州的产品分工很细,协作很强。“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管理简单,仅凭家族的能力和经验就能驾驭。而且,“船小好掉头”。
同时,家族制治理机制有助于降低决策成本和协调成本。温州的家族企业大多“男主外,女主内”。正如盖尔西克所言,“家族企业从家族成员共有经历、身份及共同语言中汲取到特别的力量。当主要经营者是亲属,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和特权都来自于同一源头。口头的和非口头的信息能在家庭内迅速传递。所有者兼经营者能够更随意地决定解决某一问题,而不需向家人多作解释。配偶和兄弟姐妹们则更能懂得彼此说话的主要意义及隐含着的决心和犹豫。最重要的是,在整个家庭利益的名义下,可以要求承诺,甚至是自我牺牲。”
所以,有人把温州的家族企业比喻成“小鸟集合成的鸟群”,有如乌云般的形体又有小鸟的灵活性。“大鸟会被击垮,而鸟群却击不垮,因为它有形又无形。”
20世纪90年代,理论界认为家族文化制约了温州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许多人纷纷提出了促进家族企业摆脱家族束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议。原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马津龙却固执己见:“温州企业之所以大多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他说,“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都表现为家族制的原因,主要在于多数企业以‘小商品’为主的产品结构使得规模经济的作用不够明显,从而企业规模不大,所有权无需向家族之外扩散;企业的存在时间也不长,经营者仍然是创业者,并未面临领导权在家族内传递和向家族外转移的选择,而且绝大多数企业生命周期也未必长到需要解决领导权转移问题的程度,往往一代人的时间内企业也就消亡了。家族制不仅满足了企业经营所要求的决策的统一性和行为的一致性,而且由于家族成员之间天然存在自我约束、自我牺牲精神,使家族制较之依靠法律约束,更能节约管理成本。”
显而易见,从温州家族企业的成长路径来看,温州企业有必要“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
第四章 家族温州杯酒释“股”权
但是家族企业制度天生存在弊端。
尽管温州是家族企业制度的一片乐土,却不可否认也不可回避其局限性。
家族企业创业容易守业难。温州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宁为鸡头,不当凤尾”的思想。所以,一旦有了钱,立住了脚根,就想自立门户。
更重要的是家族企业文化上的排他性,即使是亲戚,如果不是核心家族人员,也是内外有别的。即使是请了职业经理人,也难批200元的报销单。这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另外,亲情关系代替了企业管理,带来机制障碍。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老子有了钱,儿子就挥霍。所以,温州现有企业中,能发挥创业者优势、跟得上前辈人经营策略的企业寥寥无几。
所以,当一些想有所作为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为了应付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便开始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尝试,酝酿着摆脱家族制的束缚。
1996年,浙江长江电子设备厂的老板以借钱资助其自办企业的方式,让家族成员全部离开长江企业,并向14家兄弟企业发出倡议,组成核心企业走股份联合道路。同年8月,一家规范化股份公司浙江长江电气股份公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