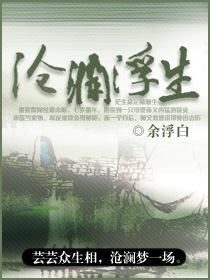但梦沧澜-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于是望向朕……”燮阳嘴角抽动,不知是哭是笑,“把酒壶递给了朕。”
“我是想……”
“朕知道你想什么,你想让朕将四王抓个现行:用媚药谋害朝廷命官,怎么样也能治他一治。”当年的感动已成了今日的讽刺,燮阳笑得肩膀耸动,“你为朕牺牲了自己,却不料,朕没有拿酒去验,反而自己也倒了一杯,喝了下去。”
“你……也许没有发现,或者是……”沐沧澜顿了顿,“觉得那个时机发难并不合适。”
“呵呵呵呵……”燮阳帝抬眼,“这么多年,你就是用这个理由欺骗自己?”
沐沧澜闭上了眼睛:“陛下,往事已了,又何必再提?”
“不,朕要提!朕要是现在不说,只怕今生今世都没机会再说了。”燮阳残忍的狞笑着,“那时候,朕其实知道,朕什么都知道。可是朕控制不了自己,朕……朕的身体已经太久没有过那样的反应了……太久、太久……那是欲望啊!朕没法再错过……”
沐沧澜蓦然睁眼,燮阳帝亦看着他。
苦笑中,原来已然多少星霜风尘过去,天,已然……这么晚了。
一轮明月,笼罩这九州山河。
燮阳帝的苍白的脸为月光罩上一层冰冷的银膜,声音也似没有热度,缓缓的流淌着:“朕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在晚上望天,望月亮,想那小小的一弯月如何就能普照天下,辉及四方?后来,朕的太子傅告诉朕:那叫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要朕有一天也像那日月一样普惠万民。朕以为朕可以做得到,只要励精图治,广纳贤才,兢兢业业的照那些圣贤书上所记载的圣君之道去做,就总有一天可以做个黎民爱戴的贤明君主。可是朕错了。当太子、作帝王最要紧的不是什么忧国忧民,最要紧的乃是保位子保命!朕从八岁被立为皇储到十六岁开始随先帝上朝听政,这中间你知道朕身边死过多少人?一个小太监,刚服侍你半天就忽然变成了悬在树下的尸首。还有数不清的宫女、亲卫……更还有朕的太子傅,朕前后死了四个太子傅啊,你相不相信?”
沐沧澜没有回答,只是静静负手望天,月光亦洒满了他满怀满襟。
“那么多年,如履薄冰、惊弓之鸟……怎么形容朕这个东宫太子都行。但朕心中毕竟还有轮明月,即使再艰难也还能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虽数十年光阴过去,提到那一刻情形,燮阳帝还是流泻出满目的愤愤不平,“先帝于木兰围场秋狩,猎后宴饮,忽然窜出一伙北蛮的刺客。大家仓皇应对,不防备时一个刺客跳了出来,举剑直刺向先帝。朕离先帝最近,直觉的用胳膊一挡,手臂上立刻被划了道口子,顿时血流如注,朕……朕见不得那猩红,立时失去了知觉。醒来才知道先帝遇刺,伤势沉重。”
原来先帝盛年时突患恶疾,辍朝多日,由当时的皇后——现今的太后垂帘听政,背后竟藏着这般隐情,沐沧澜转过眼来。
对面燮阳的黑瞳却似并无焦点,木然继续道:“但朕既不哀伤,也不高兴,只是十分的恐惧。因为先帝临昏迷前,对朕说了一句话:‘竖子胆小,如何能担一国重任?!’朕当时真愿他再也醒不过来。先帝昏迷了整整十日。那十日,朕没吃过一餐安稳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夜从恶梦中惊醒,都是梦见先帝突然废我。而那时,母后宠爱四皇弟,也一直在联络朝臣,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等十日后,先帝醒来时,朕……朕已经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先帝见了朕,终动了恻隐之心,未再提废立。而朕一回东宫,就大病一场。等病愈时,朕发现……朕……”燮阳闭了眼,声音沉到了泥土里:“朕的身体彻底垮了,朕没有了欲望,身体亦没有了……反应。那时候,朕才二十来岁。朕以为那只是太累了,可是,几年过去,怎么调养都没有丝毫改变。于是朕只好抱来了怀曦——找了好几个孩子,只有他鼻子尖尖——呵呵……咳咳,怎么就偏挑了他去?”
原以为静如止水的心在听到那个名字时,还是禁不住一悸,沐沧澜看见对面的人亦看着自己,眸中有着某些熟悉的含义。
燮阳帝的瞳仁渐渐又恢复了沉黑,望着月光下那如玉如英的身影,道:“朕以为这一辈子就这样提心吊胆的过了,谁知竟又让朕看见了一轮明月。朕感觉到朕的一生都会因他而有所改变:他是那样的清新,那样的明净,那样的光芒仿佛能照亮整个东宫。”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簪花宴上惊鸿一瞥,一树梨花压群芳,从此一生再不能放。
流光飞旋,让人恍然分不清过去现实,唯那一轮明月古今仍同。
燮阳帝沉溺于回忆:“那一夜,朕用‘春日醉’得到了他。朕终于摘下了那轮明月,但也同时失去了他的光华。那一夜,朕得到了帝位,得到了江山,却仍旧一无所有,两手空空。江山也没能治好朕的病。那一夜过后,朕依然是每天都做着各种各样的恶梦。而梦醒,也再不会有那样明亮的月色再照亮朕的心。朕不甘心,朕恨啊,朕还在盛年,如何能忍受得了从此就这样下去?朕要找回自己的雄心,重振雄风!朕不要再每夜都在梦里被先帝痛骂:‘竖子胆小!胡不敢为父报仇?!’朕要带领天军,横扫天下!”
帝王一声咆哮,血流飘杵,葬送了数十万性命。
听的人想起路过兀良堡时,那莽莽荒原上的累累坟茔和凄凄白花……
是焉非焉?
唯有那月光,能将世间一切洁净肮脏都包容下。
许久的沉默。
“陛下……”
燮阳帝抬睫,月华第一次那般清晰的照亮了彼此凝视的眼眸。他看见那人一笑,如记忆深处永开不败的梨花——
“陛下,其实您爱的并不是那轮月亮,而是——”沐沧澜的眸子那般清亮,不杂微尘,“曾经胸怀天下、无有私照的自己啊……”
一滴泪,从那晦暗太久的眸中轻轻滑落。
南风徐来,带来草木的清芬、瓜果的甜香,以及泥土的芬芳——那一切都是来自天朝的方向,来自那阔别已久的——国……家……
燮阳帝低下头去,双泪长流,良久,终于举起印章,在圣旨最后重重落下。
“沧澜……”r
他第一次听他这样称呼,只见燮阳抬头,看着他:“谢你陪朕这最后一程。”
沐沧澜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倦意和暖意同时由四肢百骸涌上心来,燮阳帝闭上眼睛,缓缓道:“虎符和孔雀胆都藏在朕的腰带里。明日一早,就送朕……回家吧。”
沐沧澜倒身下跪,晶莹的水滴融进了清明月华。
十 天高云浅(四)
景弘四年,夏,太上皇燮阳崩于南归途中。
他的死,在民间不过激起了星点细浪——有人传说他并非是病死,而是自己服了毒药,因为实在没脸回来见列祖列宗,死时七窍流血好不凄凉。人们议论了一段时间也就渐渐失去了兴趣,或许是因太过无稽离奇,又或许是觉得并没什么值得奇怪。总之,在太上皇的棺椁运抵京城之前,京里已然按敕令挂好了白幡白布,百姓也都穿上了丧服。一城缟素,倒是格外平靖宁和。
紫金将军瞿濯英亲率八千兵马奉梓宫归朝,进京后,行在队伍最前列的人在一座府第门前停步,只见府门大开,两行宫监素服立于门口。瞿濯英勒了马,朝身后马车内道:“给你半个时辰,回去换衣服。”想了想,又问:“够吗?”
里面的人没有回答。只见帘门掀开,一清癯身影下得车来,抬眼望那宽阔门庭,微微竟有些陌生——数月以来,竟是第一次回自己的太傅府。
沐沧澜走进府中,但见花木扶疏,石径整洁,一切还如往常,只是也因国丧而添了白色,平添几分疏离。径直走向内堂,宫监们也随着他走进。正要推门的手,不知怎地,就停了一停。忽然想起很久以前,有人会从里面将门打开,对自己笑:“老师!吓着你没有?”
而如今,等了片刻,还是他自己推开了门,屋内整肃如昔,不见微尘,更不要说人影。
怎么可能……他不禁勾起一抹自嘲的笑。
“太傅,按皇上吩咐,奴才们已守候多时,这就伺候太傅更衣。”有内侍立即捧上朝服,以及缠帽用的素纱。
“嗯。”他望了空落落的屋子最后一眼,闭上了眼睛,听凭他们摆布。
不过须臾,众人便见那熟悉的紫袍玉带缓步而出,帽上素纱飘拂,依然无改那天朝第一臣的端方宁定。
瞿濯英看着,心却是一揪。
沐沧澜什么都未说,径自还车。
不多时,后面的梓宫奉达,白色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离此不远的皇宫方向行去。
皇宫也披上了一律的纯白,原先是统一的明黄汪洋,如今又成了一片素白之海。
大殿之上,广场之中,百官聚集,万众同哭,跪迎梓宫归来。
一入宫门,便听见满城恸哭。
皇帝亦是一身缟素,双目红肿,泪流不止,一丝不苟的按照礼仪扶棺入殿,恭恭敬敬将父皇梓宫奉于正殿之内。金殿中,早是满目素白,青烟袅腾。
接着又是一通痛哭,后经众议,定下先帝谥号: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孝光勤俭皇帝,用尽可用之华丽词藻,庙号:文宗。
按照惯例,底下的程序便该是宣读遗诏,而当太傅沐沧澜亲自捧出那盛着大行皇帝遗命的紫檀木盒时,却被当今的皇帝阻止了,皇帝痛哭流涕,不能自持,道:“太傅稍缓,朕现在胸中大恸,心绪不宁。且等先安葬了父皇之后,再好好聆听遗训。”
此言一出,哭声一顿,很快又立刻反应过来,重汇一片悲声。只是这哭声究竟几分真假?还是在掩饰着什么:对可能变天的不安、对帝王心术的揣测,还是对自己仕途的忧心?
无人能辨清,就连沐沧澜凝视着自己学生的眼睛,都再看不透那深黑凤眸中隐藏的用心。
※※z※※y※※b※※g※※
停灵九日,皇帝日日亲于殿中守灵,内阁诸人随驾侍奉。
每一天,都有臣子进进出出,不时汇报皇陵完善的事宜、千秋城万寿山警戒的情况,以及其他许多不为人知的种种。
而据说四王府那头,亦是每天白灯高悬,灵灯长明。
两方人马时有碰面,亦无多话,只渐竟有流言四起,道皇帝迟迟不宣遗诏,定有隐情,例如并非大行皇帝亲生……
大行皇帝灵前,当今天子捏清香三柱,跪拜完毕,亲将香插入香炉,望着牌位上长长的谥号,清俊的侧脸隐现于香雾之中,半晌,方缓缓道:“独缺了个‘武’字。”
夜幕已垂,金殿内只剩了最后的守灵者。另一人静静的望着他的背影,点了点头。
“群议的时候就没有人提。”后来谥号长到不能再长的圣祖皇帝凤怀曦却仿佛看见了似的,挑起眉峰,“这个字,的确不是每个皇帝都能担得起。”——说这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不久后便会将这个珍贵的字眼送给他最珍爱的人。
那人那时自然也并不知晓——沐沧澜听了,回道:“因为此字的确分量太重,价值太大。一提到它,人往往都只想到‘穷兵黩武’,‘耀武扬威’,一字既出,往往就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却忘了这‘武’字本意是为‘止戈’。”
“树欲静而风不止。”怀曦仰首望头顶沉沉雕龙藻井,“我欲息干戈,人却不愿与玉帛。澜——”说着,他转过了身来,殿中白幡飘荡于他点漆眼底,却摇曳不了其中坚定的光泽:“是你教我如何杀伐决断,如何排兵布阵,如今,你难道竟不信我?”
那清光明朗,耀得暗沉灵堂亦有片刻明亮,让他心不禁随之一荡,一句“我信。”就这么脱口而出。
年轻天子眼中的光芒更盛了,盯着他,继续言道:“那你又信不信:我将来会开疆辟土,成一代霸主,教四夷再不敢觊觎我天朝?”
他没有反对。
怀曦便更继续:“那你又信不信:我将来会勤政爱民,作一位仁君,让天下安泰四海升平?”
他露出微笑。
素纱轻曳,如那时光之手,将幕幕往事拉回眼前:仿佛,他还是草原上那历数繁星的孩子,他依旧是大雁湖边那指点江山的青年。恍惚中,他又重新看见那双清明湛然的眼,有如一生梦想追逐的大好河山——原来,自己一直就未分清,哪一个是人,哪一个是社稷,哪头才是自己心中最深最重的牵念。
少年天子站在父皇灵前,再辉煌盛大的谥号与那朝阳般煊赫的身影相比,都显得无力而苍白。少年深深的看着他,再坚强成熟的外壳,在长久的等待中,也终于瓦解,眼中流露出满满的期待。那样温柔而动情,似能将所有的冰封瓦解。
暖流涌上,然而这潮却已来得太晚,退潮时只留下无尽的酸楚,此时,他已只能选择沉默,目光移开,凝注于灵前端放的紫檀木盒,竟忽然有些明白何为无语凝噎。
怀曦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终于再忍不住,回眸盯住了他,急切道:“你如果当真信我,那,明天就先等我解决了一切,你再拿遗诏出来。”
“可能吗?”他却摇头,“若

![[古色古香]情渡沧澜 作者:暮溪石封面](http://www.kptxt.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