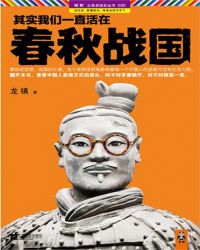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恕G『玫缡永镌谔肝褰绲摹敖愕芰怠蔽裁次榷ǎ咕倭四竟壤褡雍托×止庖唬盆氤j蛔隼印N矣行┏跃囱樱砜杉炎蛱旎厝ズ笊贤隽瞬簧僬夥矫娴难芯俊�
吃过饭,许可佳给玲姐打了一个电话,问老易现在怎么样了,要不要让她妈妈帮忙。语气自然亲密,姐啊姐的叫个不停。玲姐的反应我不知道,反正我的耳根子有些发热。我觉得自己随时在等待着许可佳突然发作,我仿佛能看见她的笑脸后面有一副扭曲的面孔。她的语气实在是太自然亲密了,让人难过。末了,许可佳让我跟玲姐聊几句,说:“你表姐问你恢复得怎么样,还是你亲自向你表姐汇报吧”。她把电话递给我时,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的呼吸一下子不那么顺畅了。
()免费TXT小说下载
玲姐说:“你没事吧,现在觉得怎么样?”
我说:“啊,没事,挺好的。”
玲姐把老易去烤鸭店的经过详细解释了一遍,我不时啊啊两声。等我发现自己不像平时打电话的语气时,我差点结巴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许可佳依然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我。我鬼使神差地关心起老易的身体来了。玲姐一听我提这个,说你还想得起来这个呀。她开始数落我不该耍性子斗酒逞能,把老易弄出了毛病,害她陪了一个通宵。
我问:“一个通宵?”
心里沉了一下。像一条船的裂缝蓦然扩大了,哗哗进水,但还是得在激流中强撑着。
玲姐说:“就是。老易直到现在还起不了床,直喊这儿痛那儿疼的,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完。他又没个亲人在北京。”
我问老易这会儿在哪儿。
玲姐说:“在老易家里。”
我说:“不行就送医院吧。”
玲姐说:“老易不肯去。”
我说:“那就不用管他了。”
玲姐说:“你说得轻巧!他这么大年纪,哪像你那么经折腾?要是死了怎么办?不死落下后遗症半痴半傻怎么办?你负得起责任吗?”
我说:“我有什么责任?”
玲姐冷笑了一声,说:“你不用跟我嘴硬。两个人斗酒,一个死了,另一个该有什么责任?老易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你有没有责任会有人告诉你的。我这会儿累得要死,懒得跟你说了。”
说完玲姐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许可佳站在旁边一直笑嘻嘻地看着我。我不知道她看出了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打电话的时候,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许可佳脸上的笑容像塑料花,真正的她就躲在塑料花后面观察我。她的目光像要穿透我一样,让我浑身不自在。她能从我脸上看出什么呢?她不可能知道我的心正在往下沉,不可能知道我的大脑里正翻滚着玲姐跟老易在一起的种种情景。
许可佳后来去了我母亲住的房间,跟我母亲说说笑笑的。有几分钟,我听见许可佳一个劲地问玲姐是我们家什么表亲。起先,母亲说他们那一辈人的表亲多得数不清,不想具体说。接着拗不过许可佳的缠问,母亲就在我和玲姐之间编排了七大姑八大姨,其中,一个姑一个姨死去了多年。我暗暗吃惊,庆幸母亲问我玲姐是哪门子表姐时,我没有编故事骗她。
一个多月后,许可佳去我的家乡小城旅游了一次,顺道打听和查证了一下我家的表亲。当许可佳坐着小船,沿着血脉的河网寻找那些通向玲姐的表亲时,遇到了一个又一个断流的地方。她两手空空回来了。这是后话。
这天目睹母亲被逼说谎的一幕,我心里真是惭愧和烦恼不已。我真想走过去对许可佳说,我和玲姐不是表亲关系,那又怎么了,知道了这个要干什么。但一想到许可佳没什么错也挺可怜的,再想到我曾答应过玲姐要在外人面前保持表弟身份,我又开不了这个口。许可佳的父亲是玲姐的上司,玲姐非常在意自己在单位里的形象。不到不得已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不应该撕破这一层薄纱。
突然,许可佳在母亲房间里大哭起来了。我走过去,看见许可佳趴在母亲怀里哭得浑身发抖。我问母亲怎么了,母亲说:“不知道,刚刚还有说有笑的。也可能是因为你不肯去她家里吃年饭的事?她告诉过我,说她父亲骂她真贱,还骂她妈妈真贱。你看你做了什么好事!”我有点相信了,从灶王节开始,许可佳就经常问我什么时候去她家里吃年饭,我都是胡乱找一些理由搪塞她。我知道她家里的年饭因为我一天天拖下来了,并影响了她家亲戚朋友安排年饭的次序。我有点内疚,拧了条热毛巾递给许可佳。许可佳擦干了脸,把她家里发生的事说了一遍。昨天晚上,许可佳的母亲问许可佳的父亲,能不能请我父母和我一起吃年饭。许可佳的父亲起先看报纸不说话,后来突然跳起来,一边撕报纸一边大骂。 听到这里,我心里格登响了一下,觉得这件事不像是真的,即使是真的,许可佳也不是为这件事大哭。不过不管怎样,事情都应该是因我而起。可我也没什么办法。我又给许可佳拧了一次热毛巾,除了拧热毛巾,好像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
母亲把我拉到一边,问:“要不你还是去吃餐饭吧?不就是一餐饭嘛,你又不是没去吃过。”我直摇头,对母亲说:“现在我更不能去了。”母亲说:“要不你不去,我跟你爸爸去?”我说:“你要是觉得合适你们就去。”母亲沉吟了一下,说:“我要是觉得合适,早就和你爸爸作东请许家吃饭了。这事你没个态度,我们不好出面。”听母亲这么一说,我多少有些放心了,我真担心她会莫名其妙地冲到许家去,或者又去什么馆子里摆上一桌。也许是我在前门烤鸭店那么闹了一场,母亲心有余悸,不然她才不会管我什么态度不态度的。
这天下午母亲安慰了许可佳好一阵子,具体叽咕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只听到许可佳后来笑了。送许可佳出门的时候,母亲理了理许可佳的衣领,突然提到了她送许可佳的那只耳环。母亲问:“你怎么总是不戴那只耳环呀?是不是那只耳环太老气了不好看?”
许可佳看了看我,不停地笑。我也嘿嘿地笑。
母亲说:“你们两个笑什么?那只耳环样式是老旧了点,可上面的祖母绿,是货真价实的祖母绿呢。镶在上面快一百年了吧,一点都不发暗。”
许可佳说:“啊,原来这么珍贵!难怪小天弄丢了不敢告诉您。”
母亲也“啊”了一声,望着我。
我只好把在许可佳面前编过的一个故事,再编一遍。
母亲皱了皱眉头,说:“这孩子,总是这样恍惚。丢了算了,改天给你买一副新的,新的样式是要好看一些。”
许可佳也不推辞,冲母亲笑了笑。母亲要我送许可佳去打车,许可佳拦住了,说:“外面有风,他身子还虚着呢。”她一跳一跳的很快就下了楼。
()免费电子书下载
母亲关上门,马上揪住我的耳朵,把我揪到她的房间里去,要我说实话是不是真的把耳环弄丢了。我怕她会伤心,告诉她没有丢。她要我拿出来。我要她答应不送给许可佳,才拿出来给她看。母亲说:“我还怎么好送给她?快快拿出来!”我把耳环找出来递给她,她才舒了口气,说:“你要真弄丢了,我真要把你的耳朵揪一块下来。嗯,收回来也好,今后要送给谁还是我亲自送去,免得你胡乱送了哪个表姐,可惜了祖上传下来的东西。”母亲的这句话让我有些不高兴,我嘟哝着说:“人家还不一定稀罕呢。”母亲说:“人家稀不稀罕是一回事,我稀不稀罕是一回事。”接下来就聊起了她跟许可佳编的假表亲这件事,母亲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是作孽,这么一大把年纪,还跟人家小姑娘说瞎话。”
我像听见了冷不丁响起来的鞭炮一样,耳朵里有一根神经蓦地抖动了一下。母亲接着罗罗嗦嗦地说了下去,大意是:她虽然不赞成我跟玲姐的关系,但她也知道这种关系不是一时半会断得了的。她希望尽快结束,同时不希望让许可佳知道。她觉得这种事闹起来谁都不好看,也影响我将来的选择。我心里清楚这些可能都办不到,不过也不想跟她拧着说。母亲能暂时容忍我跟玲姐的关系,我觉得对于她来说,已经不容易了。我不应该要求她马上支持我的选择,她的观念毕竟受她所经历的时代的限制。等将来生米煮成熟饭了,估计她也就认了。这几天随便她说什么,反正她在北京的日子长不了。
没料到,十几分钟后,我的这些想法就面临了考验。母亲告诉我,她想跟我长期住在一起。最好她这次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处理一些事情后,就来北京。她说她有退休金和积蓄,生活费用不要我操心。我结婚前,她可以照顾我的生活,我结婚有孩子后,她可以照顾我的孩子。我抓了半天脑袋,说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母亲强调了一遍她的理由:她主要是不愿意去敬老院跟一大帮老人住在一起。她担心总是跟老人呆在一起,会加速自己的衰老。
就在这一瞬间,我瞥见了在母亲的生命中飞逝的时间之箭。那是一条理解母亲的清晰的轨迹。她仿佛大半辈子都在与时间作战。她拚命抵抗时间,抵抗时间把她光滑的脸变成废墟,把她鲜活的身体变成累赘。末了,她又不得不像她这个年龄的绝大多数女人一样,放弃了身体上的抵抗,不再奢望用化妆品和保健品来保卫身体上的年轻。她走上了另一条抵抗之路:通过保持思想年轻,使自己回到年轻人的队伍中来,使自己的大脑和心灵不致与青春绝缘。她希望能跟我住在一起,也就是希望每天近距离地从一个年轻人的言谈举止里吸取鲜嫩的汁液,浸泡在朝气里。如果能允许她帮着带孩子更好,她可以跟在孙子后面回到童年,乐呵呵的像孙子一样迈着蹒跚的步履。
抓着脑袋这么想一想后,觉得有一束光照进了脑袋里,仿佛人生的迷宫又向我敞开了一个秘密的窗口。我联想到了玲姐,仿佛从母亲心灵中的一道轨迹里,找到了一条理解玲姐的线索。立刻,心里充满了跟母亲认真谈一谈玲姐的渴望。我希望母亲能更深地理解我和玲姐的关系。我试探着聊了几句围棋大师小林光一跟年长13岁的木谷礼子婚后美满幸福的故事,母亲马上打断了我,让我不要胡思乱想的。她说这事要是发生在中国,就算那个什么光一不怕人背后戳脊梁骨,他妈妈一定怕得要死。我问:“这管别人什么事呢?”母亲说:“不跟你这混小子乱说了,也不知道你是真混,还是假装混来逗娘亲开心。”
我说:“当然是逗老妈开心啦。”我心里多少有些明白了,母亲想保持思想年轻,但有些地方还摆脱不掉更早时代的阴影,那些阴影已结成了硬茧,一时半会难生新肉。她能在性观念上与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同步已经不容易了,一涉及婚姻,就要退缩,这也没什么难理解的。她没有一套可以用一致性来形容的观念,脑子里聚集着几个时代流行的思想碎片,那些碎片拼凑成了一个混乱的复合体。我再次联想到了玲姐,玲姐的一个侧面肯定也是这个样子的。
我决定还是慢慢说服母亲,或者,造成事实来让她接受。既然她不希望被时代抛下,想理解年轻人的愿望是那样强烈,我相信她最后还是会理解我并与我站在一起的。不管怎么说,我和母亲之间有一条脐带无法割断,她应该是希望我获得幸福的。即使她铁了心要一直反对下去,我也只好得罪了。说句不该说的话,她从小没怎么照顾过我,我现在的选择,她不应该干涉过多。
我觉得现在真正的问题应该不是在母亲这里,而是在玲姐那里。有什么东西在我跟玲姐之间越堆越多了,再不清理清理,我们的感情很可能就要被埋葬。我怀疑这几天不是老易在装病骗她,就是她在找借口骗我。把前门烤鸭店里发生的事在脑子里慢慢过了一遍,渐渐联想到这样的一幕:在大海上,我和她划的一条船裂开了口子,她看见一块木板从附近漂过,犹豫再三还是跳了下去,抱着木板越漂越远。而我,还在埋头抢修那条破船。
我闷闷地走下了楼。外面很冷。我站在门洞口竖起了防寒服的衣领,朝雪地上几只起起落落的麻雀望了一会儿,觉得这些麻雀像我脑袋里一些不肯安静的念头。我决定在小区里走一走。事到如今,我真是该好好想一想了。我已经里外不是人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路上碰到一个雪人,歪着鼻子,拿两颗石子眼珠瞪着我。我莫名其妙地踹了它一脚,在它肚子上留下了一个窟窿。在小区里遛达了一圈,找了些理由安慰自己,对自己说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再次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