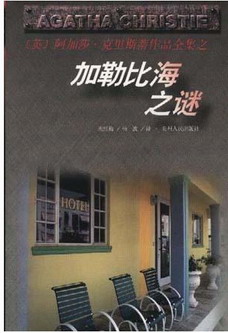加勒比海岛谋杀案-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就知道这些吗,戴森先生?”
“就是这些。抱歉,我只能效这么一点力。怎么?这么重大吗?为什么呢?”
魏斯敦耸了耸肩膀,“依现在的情况来说,任何事情都可能很重要。”
“我搞不懂这跟我的药丸有什么关系。我还以为你们要问我这女子遇害时,我的一
切行动呢。我都一一仔细地写下来了呢。”魏斯敦颇感兴趣地看着他说。
“喔?真的吗?真感谢你这么费心,戴森先生。”
“我想,这样大家都省些麻烦,”葛瑞格说着,往桌子上递了一张纸给他们。
魏斯敦仔细研看,戴文垂把椅子拉近,顺着他的肩头一起看。
“很清晰,”魏斯敦看了半晌之后说:“在差十分九点的时候,你与夫人都在自己
的木屋里换衣服,准备去晚餐。然后,你们到露台上与卡斯皮亚洛女士喝了几杯酒。九
点一刻的时候,希林登上校夫妇来跟你们一起去吃晚饭。依你所记得的,你是在十一点
半左右就寝的。”
“当然了,”葛瑞格说:“我不知道那女子到底是什么时辰被杀的——?”
他的话里多少带着些质问的味道。不过,魏斯敦警长却似乎并没注意到。
“是肯道太太发现的,是吧?她一定给吓惨了。”
“是的,劳伯森医生已经给她打了一针镇定剂了。”
“这是很晚发生的事吧,多半的人都上床睡觉了吧?”
“是呵。”
“她死了很久了吗了我是说肯道太太发现她的时候?”
“我们还不知道她死亡的确切时间呢。”魏斯敦委婉地说。
“可怜的小莫莉。她这下子真是受到惊吓了。现在想想,我昨天晚上好像一直都没
注意到她。还以为她头痛或有什么不舒服,在房里躺着呢。”
“那么你是什么时刻看到肯道太太的呢?”
“很早,在我换衣服之前。她在餐厅里布置呢,在排桌上的餐刀。”
“喔。”
“那时,她还有说有笑的,”葛瑞格说:“跟我打哈哈。她真棒。我们大家都喜欢
她。提姆真是命好。”
“好的,谢谢你,戴森先生。除了这女子维多莉亚将药丸交给你时对你说的话之外,
你记不起什么别的了吗?”
“没有了……就是我说的这些。她问我是不是找这些药丸,说是在白尔格瑞夫老头
子屋里找到的。”
“她晓不晓得是谁放在那儿的?”
“不晓得吧——我实在也记不得了。”
“谢谢你,戴森先生。”
葛瑞格推开了屋里。
“他倒挺周到的,”魏斯敦说着,手指甲还点着桌上那张纸:“那么急着要我们知
道他昨天晚上都在什么地方。”
“有点过份热衷了,你看是不是?”戴文垂问。
“这很难说。你晓得,有人天生就对自己的安全或是惹上麻烦,特别紧张的。这倒
未必预示他们有什么犯罪感,可是话说回来,也可能正是如此。”
“你觉得犯罪的机会如何?乐队演奏正起劲,大家舞兴也浓,出来进去的,没有人
能提出不在现场的确实证据。大家从这个桌子送到那个桌子的,女士们进化妆间,男人
出去踱步透气。戴森也可能乘机溜出去的,任何人都可以溜出去的。
可是他的确很心急要告诉我们他并没有溜出去。”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桌上那张纸。
“嗯,肯道太太是在餐桌上摆刀子的,”他说:“我在想,他会不会故意把这事扯出来
的。”
“你以为可能吗?”
对方仔细推敲了一阵。“我想有可能。”
在两人坐的屋外,掀起了一阵吵嚷。一阵刺耳的尖声坚持要进屋来。
“我有事要报告,我有事要报告。带我进去见先生,你带我去见警察。”
一名穿制服的警察推开了屋门。
“有一名饭店里的厨子,”他说:“急着要见你们。他说有事要报告您们。”一名
满脸惊惶的黑皮肤男人,戴着一顶厨师的白帽子,自后面推开警察,闯进屋来。他是个
副厨,古巴人,不是圣安诺瑞当地的人。
“我要告诉你们,我要说,”他说:“她跑到我的厨房里来,是真的,手里还拿着
把刀。一把刀,告诉你,她手里真拿着一把刀,她跑进我厨房,又打门口出去了,到花
园里去了。我看见她的。”
“沉住气,”戴文垂说:“呃,沉住点儿气。你是说谁啊?”
“我告诉你我说的是谁。我说的是老板的太太,肯道太太。
说的是她。她手里拿了把刀,跑到黑漆漆的外头去了。那是晚饭以前——她始终没
有回来。”
十五、继续探究
“我们可以跟你谈几句话吗,肯道先生?”
“当然。”提姆自他的办公桌上抬起头来。他把桌上的一些文件推开,并让了椅子
给他们坐。他是满脸的颓丧。“办得怎么样了?有什么进展吗?这个所在已经是未日将
近了。客人都要离开,打听班机的事。生意刚刚有了起色。唉,老天,你不知道我与莫
莉在这个旅店花了多少心血。我们把一生积蓄都投在里头了。”
“的确是不小的打击,我了解,”魏斯敦警长说:“我们很能体会。”
“只盼望一切尽快地有个水落石出,”提姆说:“这个倒霉的女人维多莉亚——唉!
我是不该这么讲她的。维多莉亚这女子,其实人挺好的。不过,总得有个很明显的理由
嘛——
她一定是有什么隐秘,或是搭上了别的男人。也许,她丈夫——”
“吉姆·艾利斯并不是她丈夫,但他们两人好像相处得很好。”
“只要尽快有个了断就好了,”提姆又重复了一句。“抱歉。
你们是要跟我谈谈。请随便问吧。”
“好的。是有关昨天晚间的事。根据验尸的结果,维多莉亚是晚间十点三十分至午
夜之间遇害的。依这里的情况来看,不在现场的证据是很不容易抓住的。客人们跑来跑
去,跳舞了,离开露台又走回来的。的确很困难。”
“我了解。不过,你的确认定维多莉亚是这里的客人所杀的吗?”
“这种可能性我们也不能不查明的,肯道先生。我要特别问你的,是你的一个厨子
所说的话。”
“呵?哪一个?他说了什么?”
“据我了解,是个古巴人。”
“我们这儿有两个古巴人,还有一个波多黎各人。”
“这个叫恩瑞可的人说,你太太从餐厅穿过厨房走到花园里去,手里还带着一把
刀。”
提姆瞪了他一眼。
“莫莉,带了一把刀?这有什么不可以?我是说——呃——
你不是认为——你这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客人到餐厅来之前的这段时间。我想,那该是八点半左右的时候。你本人,
那个时候,正跟领班佛南度谈话吧。”
“是的,”提姆回想了一下。“是的,我还记得。”
“那时候,你太太从露台上进来了?”
“是呀,她是进来了,”提姆说:“她总要到露台上去查看餐桌的。有时候,服务
生常摆错了东西,忘了刀、叉之类的。
一定是这样的。她一定是在重摆餐具。一定是多出一把刀子或是汤匙,她就带在手
里了。”
“她从露台进入餐厅之后,跟你说话了吗?”
“有的,我们谈了几句话。”
“她说了什么?你记得吗?”
“我想我问了她在外头跟谁说话来着。我听见她在外头说话的声音。”
“她说她在跟谁说话呢?”
“葛瑞格·戴森。”
“喔,是的。他也是这么说的。”
提姆又说:“我晓得,他在打她的主意。他有这种毛病。
我很不痛快,就说:‘真混帐,’,莫莉笑了开来,还说她自己会给他点颜色看的。
在这方面,莫莉是很精明的。你也晓得,她的差事不容易作。客人得罪不起,像莫莉这
么漂亮的女子只有看淡一点,一笑置之。葛瑞格·戴森一看见漂亮女人就禁不住要毛手
毛脚的。”
“他们两人有没有口角过?”
“没有,我想没有。我不是说了吗,她通常只是一笑置之。”
“你不能确定她手里究竟拿了刀没有?”
“我记不起来了——不过我敢说她一定没有。事实上,她根本没有拿。”
“可是你刚才却说……”
“我那是说,如果她人在餐厅或是厨房里,是很可能顺手拿起一把餐刀的,我现在
记起来了,她从餐厅里进来的时候,手里根本没有拿什么东西。这一点不会错的。”
“好的。”魏斯敦说。
“提姆有些不安地看着他。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吗?那个混帐笨蛋恩瑞可——姓曼纽吧——管他的——到底是
怎么说的?”
“他说你太太走进厨房,一脸怒气,手里拿着一把刀。”
“他在胡说八道。”
“在晚餐时或稍后,你可曾再与你太太谈话?”
“没有,我想没有。那时候我忙得很。”
“晚餐的时候,你太太在餐厅里吗?”
“我——呃——在的,我们总得四下照顾一下客人,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
“你一句话也没跟她说吗?”
“没有,我想没有……我们通常都很忙,不会注意各人在忙什么,当然也就没功夫
谈话了。”
“那么,一直到三个小时之后,她发现死者尸体,走上台阶之前,你是不记得跟她
谈过话的了?”
“她受了很大的惊嘛。她心里难过极了。”
“我知道。的确是很难受的经历。她怎么会跑到去海滩的小路上去了呢?”
“忙着把客人的饮食都上桌之后,她经常出去走走,躲躲客人,透透气。”
“据说,她回来的时候,你正与希林登太太说话呢?”
“不错。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客人都去睡觉了。”
“你跟希林登太太谈什么呢?”
“也没什么特殊的事。为什么?她对你说了什么?”
“到目前她还没说什么。我们还没去问她呢。”
“我们只是随便谈谈。莫莉了,经营这家饭店之类,东扯西扯的。”
“后来——你太太就走上了露台的台阶,告诉你出了事了?”
“是的。”
“她手上有血迹!我告诉你,你心里到底有什么企图?你是别有用意,是吧?”
“请不要激动,”戴文垂说:“我知道,提姆,这对你是很不容易承担的打击,可
是,我们不能不把事情问清楚。据我了解,最近你太太身体好像不太好?”
“胡说——她很好。当然了,白尔格瑞夫少校的死很令她难过。她是个很敏感的女
子。”
“等她复元一点时候,我们得立刻问她一些问题的。”魏斯敦说。
“这,现在不行。医生给她注射了镇定剂,不许人惊扰她。
我不能再让她难过,再给吓着,你们给我听清楚了!”
“我们不会去吓她的,”魏斯敦说。
“我们总得把事实搞清楚。现在我们不会去打搅她,不过,只要医生说可以了,我
们就得去见她。”他的语气虽很委婉,却是没有商议的余地的。
提姆看了他一眼,嘴巴张开,却没有说话。
艾芙琳·希林登泰然、镇定一如往常,坐在指给她的椅于上。对问到的问题,她都
经过一番慎思,才慢慢地回答。她用深黑、充满智慧的眼睛细心地看着魏斯敦。
“是的,”她说:“他太太从台阶上来告诉我们有人被杀的时候,我正跟肯道先生
谈话。”
“你先生不在场吗?”
“没有,他已经睡觉了。”
“你有什么特别理由要跟肯道先生谈话吗?”
艾芙琳扬起了画得很好的眉毛,眼神显然是谴责性的。
她冷冷地说道:“你这问题问得真怪。没有——我们的谈话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你与他谈起他太太的健康情况了吗?”
艾芙琳又考虑了片刻。
“我真记不得了。”最后她还是回答了。
“真的吗?”
“你是说真的记不得吗?话怎么可以这么说呢——人在不同的时候,会谈很多不同
的事情。”
“据我所知,肯道太太最近身体不太好。”
“她看起来还挺好嘛——也许显得有点疲惫。当然,经营这样一家饭店是很费神的,
她又没什么经验。自然偶尔会有点慌乱。”
“慌乱。”魏斯敦顺口重复了一句。“你是用这个字眼形容她吗?”
“也许这个字眼有些老派了,但也并不比一些时髦的字眼差。稍微上了点火,就称
之为‘滤过性病毒’,为日常生活烦点心也被认为是‘神经衰弱性的焦虑’——”
她的浅笑使得魏斯敦感到有些尬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