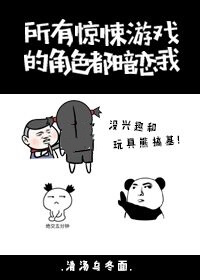流浪金三角-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雨季一过,政府军旱季围剿便开始了,战斗日趋频繁。半年过后,于小兵已经当上班长,成为一个有战斗经验的老兵。他的屁股上曾经穿过一颗子弹,脸上落下一道难看的刀疤,那是一个敌人用刺刀给他留下的终生纪念,幸好是轻伤,否则难免成为烈士。野佧班长在两个月前被一颗炮弹炸断腿,当时敌人正在进攻,他疼得在地上拧成一团,脸上五官全错了位,只有那双垂死的眼睛射出哀哀的光来。班长其实并没有错,他打死林建国,那不是他的罪过,是战争使然。于小兵想通了,他抬头望望天,天空晴朗而深邃,像口天真烂漫的陷阱。他不去看伤员,只将冲锋枪口向下压了压,扣动扳机……
从前的红卫兵于小兵就这样被自己的子弹消灭了,他变成一个真正的士兵,对子弹和死亡无所畏惧,心像石头一样冷酷无情。这期间游击队总是被敌人追击,一道越境的北京知青牺牲好几个:罗援朝是夜间行军失踪的,他失足掉下一座悬崖,只有风把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声惨叫慢吞吞地刮向远方。而另一个担任侦察任务的江国庆则是被敌人迎面捅死的。他喝多生水拉肚子,刚刚从一棵树后站起身来,来不及拉上裤子,一柄雪亮的刺刀迎面捅在肚子上。他死后姿势很难看,糊了一裤子稀屎。
一个太阳光金灿灿的日子里,战友聚在一起喝闷酒,都是北京知青,气氛压抑,情绪悲观。于小兵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他盯着大家说:“切·格瓦拉是怎么死的?”
李红军喝着糯米酒回答:“好像是被俘后牺牲的。”
于小兵又说:“他为什么不开枪自杀?”
喝酒的人都愣住了,切·格瓦拉是红卫兵狂热崇拜的精神偶像,他们都是读过《格瓦拉日记》才投身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但是没有人能回答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于小兵哈哈大笑,笑得流出眼泪,连连说来来,为活着干杯。于是那天四男一女都喝得酩酊大醉,又偷偷吸了鸦片,吐了一地秽物。
被对立派通缉的打砸抢分子刘黑子刚到边疆插队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越过边境参加反政府游击队。
初中生刘黑子并没有那么多高尚的革命理想,他不喜欢读书,不痴迷革命理论,更不知格瓦拉为何物,即使知道也决不会顶礼膜拜。他是那种下层平民子弟,出身低贱,父亲拉三轮车,码头扛大包,子女缺少教育,靠本能生存。因为重庆武斗打死人,为了逃避运动和对立派通缉,他与同伙才选择了非法越境的道路。如果刘黑子拥有格瓦拉同志的地位和权力,他为什么不好好享受而要自讨苦吃呢?
刘黑子说:“回去是不行了,我们都是打死过人的,日他娘!……打仗老子不怕,老子在重庆是出名的武斗大王,谁见了不怕?那回在朝天门,老子一口气打了一万发子弹,枪筒打红几根!打活人靶子赌香烟,谁敢干?所以我说,弟兄们好好干,将来坐了天下,大家还不弄个省长市长干干!反正闹革命,打死人不偿命!”
但是重庆的武斗大王第一次上战场就吓得尿了裤子。
那是一次遭遇战,真正的战争,而不是重庆乌烟瘴气的群众武斗。游击队正要开进寨子,正好遭遇政府军出寨子,枪声立刻哒哒地响起来,一颗大号达姆弹把碗口粗的树干拦腰击断,树枝砸在刘黑子头上,立刻鼓起一个大血包。就在他跌倒在地上的时候,一个人好像被风刮倒一样重重压在他身上,那人仿佛刚从粘腻的海水里捞上来,浑身湿漉漉的,散发着一种新鲜海草温暖而浓烈的咸腥味。他感到海水还在顺着那个身体往下淌,流到他的脸上和嘴里,像小虫子在爬,弄得他痒痒的。他砸砸舌头,感觉海水是咸的,不,好像是甜的,像小时候外婆熬的糊米水又浓又稠。
一发迫击炮弹在附近炸开来,几乎把他的耳朵震聋,爆炸气浪把他身上的那人掀开来。他使劲睁开被胶水粘住的迷糊眼睛,这才看清那人原来是他的同学陈倭瓜。陈倭瓜眼睛睁得大大的,样子很怕人,肚子已经变成一个空洞。刘黑子赶快在脸上抹一把,抓到一手破碎的肠子和人胃,胃里还有早饭和没有消化的食物。武斗大王一恶心,就趴在地上哇哇地呕吐起来。
枪战激烈进行,各种武器的射击简直惊天动地,咚咚咚,咣咣咣,咔咔咔咔,刀光剑影,死亡之神漫天舞蹈。每个人都在杀人和被人杀死,他们用生命进行赌博,虽然最后的结局尚未产生,但是不断有痛苦的哀嚎和惨叫响起来,像屠宰场,反正那些人一定不是赢家。中弹的人像牲口一样噗通栽倒,四脚朝天,有的痉挛扭曲,有的一动不动,好像睡着一样。许多红彤彤的液体就从他们身体里流出来,让人觉得他们的身体本身就是一只易碎的玻璃瓶子。
()
武斗是什么?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狂欢节,是成年人模拟的杀人游戏。战争才是真正的死亡大餐。好比演员在台上表演收割舞蹈,悠扬而多姿,但是他们永远学不会收割,而脸色黝黑的农妇在水田里干活,只一下,那些水稻就直挺挺地倒在泥地上。军人都是杀人专家,他们的职业就是收割死亡。他们甚至不用弯腰,手指轻轻那么一动,生命就像水稻一样纷纷跌倒在肮脏的泥地上。
此刻来自山城重庆的武斗大王刘黑子被一种深刻的恐惧和死亡气氛所包围,他把头埋在泥土里,身体像树叶簌簌发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觉得好像有根鞭子在脖子上嗖地抽了一下,就那么轻轻一抽,脖子上的皮肉就好像不结实的报纸一样裂开来,鲜血四溅,他一下子看见自己的脖子断了。“哦……我的脑袋要掉下来啦!”这么一想,他的尿就不争气顺着裤子汩汩地淌下来了。
一颗手榴弹在不远处爆炸,掀起泥土溅了他一头一脸。他动了动,下意识甩掉头上的泥土,这才发现脑袋依然结实地长在肩头上,他的脖子也没有因此折成两段。这时他听见一个走调的声音在心里急切地叫道:“你没有死,你活着!……你得活下去!”
一瞬间鲜活的生命和生存愿望重新回到身体里,血液依然汩汩地在体内流淌,他不顾一切地翻身滚进一条水沟。这一滚果然救了他的命,因为不久他就看见一排机枪子弹打在他躺过的地方。子弹优美地在空气中打着旋,跳跃着,歌唱着,像一群快乐的小鸟,幸好他及时躲开了。子弹撞击在石头上,石头立刻像朽木一样裂开来,溅起一群五彩缤纷的火星。他虚弱地躲在岩石下面,大汗淋漓,像个初生的婴儿。
幸好政府军不占优势,打了一会儿就主动撤退,游击队打扫战场,在岩石下面找到负伤的重庆知青刘黑子。其实刘黑子也没有负什么重伤,只是擦破了一点皮,抹抹烧酒就好了。只是他的情绪恢复得慢一些,过了几周才渐渐恢复正常。
第二十六章 走向深渊
不难想见,三十年前焦昆到金三角寻父的企图是注定要落空的。
焦昆是昆明知青,在滇西下乡,那时候下乡知青很容易耀武扬威,偷鸡摸狗拔蒜苗,把对命运的绝望不满发泄在当地农民身上。焦昆不这样,他本分得像头绵羊,老乡都夸奖说没见过这么本分的男知青。只有焦昆自己心里清楚,他当然比不得别人,别人有张狂的资本,他没有,因为他父亲是右派,还在劳改农场服刑。
有一天,一个人悄悄带信来,告诉他父亲去了金三角。这个消息很突然,父亲到金三角干什么?金三角那样大,他在哪里呢?焦昆傻眼了,就像面对茫茫大海,一时间不知所措。当然父亲的行动有他的理由,焦昆猜不出来,冥思苦想几天以后,他还是做出一个足以改变他一生的惊人决定:偷越国境去寻父。
关山重重,山大林密,金三角地广人稀,加上语言不通,人地不熟,连线索也没有一个,他到哪里去找父亲呢?流浪一个多月,他很快在腊戌附近被缅甸警察抓住,先痛打一顿,然后关进拘留所。
拘留所是在一座地下室里,没有窗户,刚从明亮的地方进来,两眼一抹黑,就像掉进黑窟窿里,什么也看不见。焦昆闻到一股刺鼻的恶臭气味扑面而来,像掉进了大粪池,熏得他连忙捂住鼻子想:“妈呀,这是什么牢房,怎么这么臭?”
等眼睛适应黑暗,他才看清牢房很像闷罐车厢,地上挤着许多犯人。那些犯人都不出声,坐在草席上看他,眼睛像野兽一样在黑暗中闪动绿荧荧的光。焦昆倒吸一口冷气,幸好这时靠近屎尿桶地方站起一个人来,大声用汉语问他:“你是新来的知青吗?……这里有空位置,不过要忍耐些。”
于是他就同牢房里的知青认识了。招呼他的这人是昆明知青,叫秦大力,另外两个,一个是上海知青余新华,另一个是北京知青郜连胜。他还得知,隔壁女牢里还关着两名女知青,一个是余新华尚未结婚的妻子周招娣,另一个也是昆明知青,叫姜小玲。
放风的时候,他见到隔壁的女知青,原来周招娣是个孕妇,挺着大肚子,因为阳光见得少,脸色苍白。姜小玲也没有什么表情,对他们点点头,就顾自蹲在水槽跟前洗头发。大家都觉得很苦闷,很绝望,周招娣忧心忡忡地问余新华:“听说移民局要把偷渡的知青遣返回去,是吗?”
余新华安慰她说:“侬要多保重身体,管他遣不遣返。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
北京知青郜连胜头发直竖,怒发冲冠的样子。他是读过一本叫做《格瓦拉日记》的油印小册子,然后决心献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料革命没有找到,却被关进牢房,他坚信革命信念决不因为坐牢久了,就像雨季的潮湿天气一样发了霉。他看一眼周招娣的大肚子,鄙夷地说:“嘁!你们这样乱搞男女关系,哪有一丝革命青年的气味?”
余新华脸涨红了,脖子充血,问题是他是上海知青,上海男知青个个长得跟豆芽菜一样,是不兴跟人动手打架的。倒是一旁的秦大力看不过去,站出来愤愤地说:“老郜你不能这样说话,都是知青,各人有各人的难处,你要是思想崇高,到山上打仗去,干么跟别人过不去?”
郜连胜看他一眼,因为秦大力人高马大,动起手来会吃亏,就冷笑着走到一边去。焦昆觉得不解,说:“都什么时候了,身在异国他乡,还这么不团结?”
上海知青就乘机说了郜连胜许多坏话,什么自大狂、极左思潮、自以为是、唯我独尊等等,听得焦、秦二人无话可说。放风结束,回到牢房里,几个人都气鼓鼓的不想说话。
开饭时候,牢卒给每人发一只芭蕉叶饭团,只有一二两大小。焦昆放在鼻子底下闻闻,觉得气味不对头,打开来一看果然是馊的,吃不下去。他看见那个郜连胜一点也不挑剔,大口吃得很香,心里觉得很佩服。余新华恳求牢卒说:“请把我的饭团给我妻子,她怀孕了,行行好!”
秦大力很同情他,说:“你不吃饭怎么行?”就把自己饭团分一半给他。上海知青很感激,接过来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吃完就抹开眼泪,说:“早知道受这么多罪,干么还要往外跑?”
郜连胜像个坚定的革命者那样说:“只能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我们必须越狱!”秦大力赞同道:“对!得想法出去!”
拘留所好比一座垃圾中转站,旧垃圾还没有运走,新垃圾又来了。金三角形形色色的人都在这里出入,小偷,毒贩,杀人越货的强盗土匪,也有不少背景复杂的政治犯,比如反政府武装分子,国民党情报人员,等等。总之你很难辨别他们的身份,弄清朋友还是敌人。
这天夜里,隔壁女牢突然传出凄厉的喊叫,夹杂着敲打铁门的哐啷声。余新华脸一下子白了,抓住铁门发疯地喊叫:“来人啦!哦,招娣,招娣,你怎么啦?是不是……要生产啦?!”
一个值班牢卒睡眼惺忪地走进来,大声呵斥道:“闹什么啊!再闹,明天给你戴脚镣!看你们老实不老实!”
余新华央求他:“我妻子要生孩子了,行行好,把她送进医院,求求你了。”
牢卒瞪起眼睛骂道:“想得倒美!你是什么东西,还想进医院?……生就等她生在牢里,明天叫人来收尸。”
知青都气炸了,扑到门边破口大骂:你一个反动派走卒算什么东西?老子堂堂中国知青,受你这样侮辱?……你还是不是人,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你只配做条狗!帝国主义的乏走狗!
正闹得不可开交,有个人从地上站起来,用标准的汉语劝说他们:“好了好了,你们别跟他吵,救人要紧,让我来想想办法。”
大家一愣,这是个新来的犯人,有四十多岁年纪,穿掸族服装,其貌不扬的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