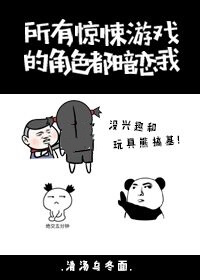流浪金三角-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她迷惑不解地抬起头来,看着我因气愤而涨红的脸,那双纯净如水的眼睛里写满问号,好像是在小心地询问,我做错什么事情吗?
我大声质问她,愤怒使我的声音走了调。我说:“你……怎么能这样?”
她低头到处找找,又仰起脸紧张地问我:“哪样?我,怎么啦?”
当她弄清楚我生气的原因后,立刻轻松地笑起来,连连安慰我说:“不有关系不有关系,小汉人!我们世世代代这样喂娃子,(母亲)吸了大烟,奶水就好,娃子吃了不闹病。不信你看……”她抬起一只丰满的Ru房,用手轻轻一挤,雪白的|乳汁就像珍珠泉一样喷出来,臊得我满脸通红。
“……娃子要是闹睡,闹肚子,你给他喷几口(烟),他就好了,睡得乖乖的。不光娃子,我们大人要是闹病,头疼肚子疼,打摆子,吸吸烟,再不就吞一丁点生烟,保准你壮得跟头黑熊一样。”
“生病可以吃药,为什么要吸鸦片呢?你不知道有很大危害吗?”我对她的理论并不信服,觉得是她在为自己的恶习辩解。
“我们不有药,鸦片就是药。你刚来,打摆子,发烧头热,就是给你喷了烟,吞了生鸦片才好的。”我大惊,愣了一阵,只好躲到一边去。那个婴儿果然在母亲悉心照料下安睡过去。
在我曾经短暂地走过金三角的那段日子,我看见美丽的罂粟花不仅像旗帜一样飘扬在掸邦高原的红土地上,而且它的根系还深植于那些山地民族的灵魂里。他们从未走出大山,原始封闭,大自然给予他们的唯一恩赐就是贫穷和罂粟。他们在努力同贫穷搏斗的同时收获罪恶,罂粟是他们通往天堂或者地狱的唯一途径。他们决不是天生的罪犯,然而正是这些救助和呵护过我的善良而勤劳的山民,他们源源不断种植出来的大烟被提炼成更加可怕的海洛英,走私到中国大陆,到亚洲、欧洲、美洲和世界各地,毒害全球人类和他们的后代。魔鬼不是自己生长出来,而是被包括我的恩人罗勒大哥一家这样善良的人们共同制造并释放出来的。
联合国禁毒署资料,二十世纪下半叶,在亚洲南部以种植罂粟为生的各国人数超过一千万人,地域主要分布在萨尔江流域直至湄公河流域的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的三角形地带,区域面积之广大,相当于缅甸国土的三分之一,或者七个台湾岛加在一起的总和。
这个区域就被形象地称为“魔鬼金三角”。
第二十章 末路英雄
统计资料显示,国民党入缅前的1949年,金三角鸦片产量仅为三十七吨,这个数字与当时东南亚各国鸦片产量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仅以越南、老挝和泰国为例,这些国家鸦片产量均超过一百吨,可见当时金三角还算得上一片净土。
六十年代前,也就是国民党残军反攻大陆的“勐萨时代”和柳元麟时代,金三角鸦片生产也无明显变化,1959年世界卫生组织估计,金三角鸦片产量约为六十吨,这个数字仍然不足以对人类生活构成威胁。
这期间相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一件大事,这件事看似与金三角无关,然而历史表明,它对金三角乃至整个世界禁毒运动都将产生举足轻重和意义深远的影响。北京政府仅用三四年时间,就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历史性地完成禁毒壮举,中国大陆不再有罂粟遍地烟祸横行的景象。中国政府为全世界做出一个榜样。中国禁毒成功意味着世界最大的鸦片产地和市场消失,但是这并不等于毒贩坐以待毙,市场供需杠杆就是靠利润刺激生产,毒品暴利给不法商人带来巨大财富。也就是说,市场可以培养,可以开辟,只要有人吸毒,毒品就会被源源不断制造出来。
我们看到,进入六十年代,尤其是国民党帝国崩溃之后,作为反攻大陆的军事桥头堡不复存在,政治意识被淡化,金三角鸦片种植业反而开始兴旺,以迅猛势头快速增长,产量也像滚雪球一样成倍上升。六十年代中期突破一百吨,1970年突破一千吨,十年间产量翻了十番。到八十年代更是不可遏制,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二千吨,令全球震惊。后来这一纪录屡屡刷新,九十年代金三角鸦片终于突破二千五百吨大关,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王国。
与这一组数字相对应的是,世界吸毒人数直线攀升,九十年代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全球吸毒人口约为三亿,也就是说平均每二十人之中有一人吸毒,其中百分之六十六为青少年。199年,全球毒品走私总收入约占全球商业贸易收入总额的百分之八,达到四千亿美元!
对我来说,上述数字提供一条可供参考的变化的历史坐标线。我的疑问在于,为什么恰恰六十年代是一条分界线?五十年代国民党兴旺时期,金三角毒品处于休眠状态,政治对于毒品生产有抑制作用吗?或者说,五十年代播种,六十年代开花,七八十年代结果,这是历史发展的周期规律?1961年,国民党残军的没落直接导致金三角毒品王国的兴旺,这是偶然性使然,还是因果关系?我将目光投向云遮雾罩的亚洲南部金三角,在那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上,无数巨大的问号像漂浮的冰山,它们将自己的真面目隐藏在水下,隐藏在历史暗河的深处,只露出八分之一的山峰若隐若现地向我迎面驶来。
我的另一位泰国朋友刘舟是个诗人,说“泰国朋友”不十分准确,主要是不够亲切,因为很多年前他同我一样也是云南知青,也在边疆插队,后来去了金三角,当过缅共,打过仗,吃过很多苦。再后来他辗转到了塘窝,娶了当地一位汉族姑娘为妻。姑娘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文焕将军的妹夫,原国民党第三军参谋长古少卿将军。
刘舟是个执着的汉语诗人,性格十分豪放,泰语至今说不好,汉语诗却写得激|情澎湃。他寄给我许多诗作,其中部分在国内刊物发表。他这样吟唱道:历史的长河呜咽流逝 暗淡的岁月不再重返 普天下炎黄华胄 携起我们森林般的巨手 重铸黄魂九鼎。
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热爱诗歌?为什么痴情不改,一往情深?”
我说:“理想主义?爱情至上?或者生活优越,低吟浅唱?”
他哈哈大笑说:“什么这样主义那样主义。告诉你,你受过刑吗?或者中枪伤而没有麻醉药,所以你就得拼命地吼叫,把那些可怕的疼痛从喉咙里吼出去。”
这个比喻令我毛骨悚然。我说这是诗吗?是恐怖主义。
他说你在缅北流浪那阵,我正在勐版打仗,为生存而战。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社会如果到了仅仅为生存而战的时候,你就到了毫无人格、信心、自尊和理想可言的地步。你变成野兽,你的敌人也是野兽,弱肉强食,茹毛饮血,你的神经就压迫变形,这时候我想到写诗。
我反驳说:“你岳父,还有段希文李文焕他们打了一辈子仗,一辈子不得安宁,他们写诗吗?”
他叹口气说:“其实他们都写诗,只不过各人方式不同。你看那些将军身后墓碑上,哪个没有留下无限感叹,那不是诗又是什么?”
我立刻表示服气,承认他的话很有道理。对戎马一生的军人来说,他们不是用手中的枪写诗么?我说你岳父他们在金三角打仗究竟为什么?为信仰,理想,还是权力、金钱?
诗人陷入沉思,最后悲观地摇摇头说:“我认为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活着’。”
无独有偶,我有幸采访和认识的许多老军人:雷雨田、杨绍甲、李崇文、丰顺禧、梁中英、黄科、马鹿塘和勐萨郊外的老人,他们都无一例外表情庄重地使用这个名词“活着”。事实上活着是胜利,谁活在最后,就能看到或者接近希望,虽然他不一定活得最好。
雷雨田回忆那个艰难岁月说:“后来无路可走,好像降临一个死亡的世界,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活下来。”
()
我说你们怎么选择美斯乐?是偶然,还是必然?
老人想想回答说,都算吧。
我以同样问题询问杨绍甲将军,我说你们为什么选择塘窝而不是别的地方作根据地?他苦笑说,因为走不动了。
另一位梁中英将军则指着自己腿上的伤疤,干脆地说:“都是命,死了是命,活着也是命。遇见什么人,跟谁走,那都是命!”
公元1961年雨季说来就来。
仿佛旱季还在逞凶,凶恶的阳光炙烤得地面积起厚厚的粉尘,没有风,那些细小尘埃随着热气流上升,明净的空气仿佛融化的玻璃发出阵阵颤动。人们躲在屋檐下,水牛把庞大的身躯浸泡在河沟里,狗们趴在树下伸舌头。到了下午,空气变得滞重起来,太阳好像抽筋一样突然散了神,变得有气无力,坚硬的光线像风筝那样飘飞起来,空气中明明白白地增加许多水份,变得浓稠粘滞,于是人和牲口都一齐张大嘴巴,像扔在沙滩上的鱼一样徒劳地张合,好像他们都用腮而不是肺呼吸。
这时候雨季就像一头阴险的鳄鱼一样扑上来。
积蓄了整整一个旱季的积雨云团好像冲破闸门的洪水,汹涌地扑进中南半岛上空,长长的闪电像鞭子凶猛抽击大地,猛烈的炸雷由远及近,发出骇人听闻的巨大爆炸声,于是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硫磺味。台风横冲直撞,将海平面挤压变形,就像万吨水压机挤压一张薄铁皮,将它们变成几十米高的波峰浪谷,然后驱赶它们浩浩荡荡地冲上陆地来。城市和村庄被冲毁,树木、行人和房屋被卷走,台风还像一个野心勃勃的封建暴君,到处攻城略地,把蓄满水分的积雨云团源源不断地赶往大陆深处,将山林覆盖,河沟注满,淹没低地,冲毁山坡,引发洪水和泥石流,将山川大地变成一片汪洋泽国。
这一年全世界都笼罩在“厄尔尼诺”现象的可怕阴影之中。中国后来宣布发生百年不遇的灾害,饥荒在全国蔓延,时间持续三年,死亡人数未见公布。史称“三年自然灾害”。
段希文骑在马上,沿着泥泞山道艰难前行。
头顶大雨如注,山谷仿佛变成一座昏暗的牢房,低矮的云层挤压树梢,疲惫的队伍像蜗牛一样在崎岖的山道上缓慢移动,人人脸上都挂着茫然和疑问的表情。段希文忧郁地望望天空,心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第五军从猫儿河战场紧急撤退,之后一度进行战略大转移,先是根据台湾命令渡过湄公河,试图像当年占领金三角那样在老挝北部重建根据地。谁知这回是美国人站出来反对,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新的不安定因素加速老挝内乱,白宫直接向台湾施加压力,台湾不得已,只好命令柳元麟撤军。第一、二、四军服从命令,经由泰国空运撤台,第三、五两军再次联合抗命,宣布就地独立。
独立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台湾不承认,取消番号,你就名不正言不顺,这支连国籍也没有的汉人队伍只好变成土匪。
老挝政府宣布非法入境的汉人军队为不受欢迎的人,政府军出动飞机和地面部队拦截,第三、五军在老挝军队打击下不得不落荒而逃。早有准备的缅甸军队当然不肯放过这个报一箭之仇和痛打落水狗的大好机会,他们像猎狗一样扑上来,一路围追堵截乘胜追击。时光流转,此残军非彼残军也,第五军痛失根据地,流离失所,又经历内部分裂,情报不灵,到处被动挨打,变成丧家之犬。好比从前威风凛凛的兽中之王,一旦受伤落魄,它的敌人包括那些最胆小的豺狗都会猛扑上来撕碎它。为了不被敌人消灭,他们只好不停地行军转移,冒着大雨在金三角崇山峻岭中四处流窜。这是一个悲惨的时刻,雨季提前来临,交通中断,到处洪水暴发,官兵士气低落,伤员病号剧增,开小差溜号甚至集体逃亡事件天天都有发生,仿佛整个世界都成了这支不幸队伍的敌人。
段希文默默看着队伍从他面前经过。这是一些他熟悉的灰暗面孔,他们都是云南人,家乡子弟兵,经过岁月演变,这些人早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队。一个妇女从他面前经过,她是军人家属,怀里婴儿大声啼哭,母亲却没有奶汁,还有两个跟在后面走路的孩子累极了,坐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肯走。母亲打了孩子又打自己,结果大人孩子哭成一团。将军看得心酸,险些掉下眼泪,他把坐骑让给孩子,自己随队伍步行。
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以来,这支前国民党军队已经悄悄发生变化:年轻人长出胡子,中年人进入老年,单身汉变成拖儿带女的丈夫和父亲。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这支行军打仗的队伍里有将近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反攻大陆的政治目的已经消亡,台湾也不再是他们的靠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