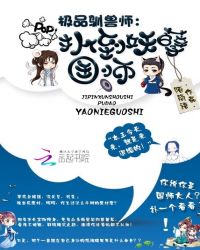国师之道-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们已先行离去,贫僧代为谢过。”
“大师怎么说客气话,我是诚心诚意请大师多住几日。”楚离心下黯然。眼前的昙无成也是垂垂老矣,只怕今次一别再无相见日。
“缘起缘灭,本是天理,小友无须为此伤怀,”昙无成眸中染了三分怜惜,望着楚离道,“小友小小年纪,已有如此造化,实属不易。贫僧今日既与小友有一面之缘,有两句话想送给小友。”
“大师请说。”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天地之道无穷尽,人有不能至,当虚怀若谷以求真智。”昙无成念了声佛号,又道,“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一切因果皆由自造,不可怨天尤人,小友日后不必为之自责。”
第一句让楚离脸色大红。她可不正是因为赢了这次口水战而沾沾自喜得意洋洋呢嘛!楚离想,要是昙无成大师和他两位同门上台发问,不过两三句话就能让她败下阵来。她能赢,不过是因为挑衅她的人不够厉害。或者更确切地说,真正大智慧者看得透其中利害便不争这浮名。这也是为何昙无成师兄弟三人只于台下静观并未当场责难的原因,他们这些大智慧者惜才爱才,知利害权衡,所以才特地私下来找楚离。
第二句却让楚离似懂非懂。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因果自造、不怨天尤人,这个楚离明白,可是为什么让她不必自责呢?
楚离心有不解,正要发问,昙无成却道,“小友不必多问,天机不可泄露。”
“……”这句话简直是搪塞利器,楚离只好缄口。她暗自嘀咕,为什么总有这样好似知道什么却又什么都不肯说的人呢?虽然是高僧,可这点着实让人不好接受。装神弄鬼的作风,倘若不是昙无成确有大德,楚离一定把他当神棍。
昙无成观其神色,不由莞尔。楚离看见这笑容,大有弥勒佛大肚容天下的气度,便只好笑叹,“我只是不喜欢这种说了不如不说的方式。”
昙无成哈哈一笑,“小友当知,人心不古,欲壑难填,即便我们能够预知未来,却不能把握人心。唯一能做的,只有尽力趋利避害。而小友本该是方外之人,却被人心牵涉其中,贫僧不忍,故有此忠告。”又道,“万般法相,各有其理,可知而不可言。小友只要问心无愧,便足矣。”
“多谢大师提点,晚辈定当顶天立地,绝不负人。”楚离作揖相谢,昙无成扶住她,“贫僧也该告辞了。”
楚离苦留不住,只得送他离去。
其时晨光普照,万物乍然生辉。楚离目送昙无成消失在视线里,在这熹微中久久伫立,心中似有千结万丝,却理不出头绪。
远远地看见昙无成回头,朝她合掌施礼,楚离也双手合十,恭送他离开。
隔得太远,她听不见昙无成那声仰天长叹。
“我佛门当有此浩劫,惟愿小友能帮扶一二,少些杀孽。”
第17章 【钗头凤】17()
刚万分不舍地送走昙无成,国师府里又来了人。
不过这次来的人,可就没有昙无成那样让楚离欢喜了。因为来的是个宣旨太监,召楚离入宫觐见。还送了官服来。
楚离一看,这官服也真是奇特,竟是一身藏青的锦绣道袍。楚离嘴角抽动,她又不是道长,穿什么道袍啊。
楚离不愿意穿。她早饭还没吃呢,就让她换官服上朝,心里是一千一万个不乐意。更何况,原来也没见寇谦之穿什么官服啊。宣旨太监等得久了,不由得催了两句,楚离只当听不见,慢慢磨蹭就是不理。她对皇宫可没什么好感。
等到东边日头大亮,楚离才正正衣冠,慢慢踱步晃了出来。宣旨太监一看,心里老大不开心。这个小国师竟然还没换衣服!可他也不敢再耽搁了,要是再让楚离回去换衣服,指不定得换到什么时候呢。只怕到时候早朝都下了,那时皇帝怪罪下来,他可担待不起。索性由着楚离去,反正不穿官服,有罪的是楚离又不是他。
朝堂之上,拓跋焘一眼看见仍旧粗布麻衣不改的楚离,脸就阴沉下来。楚离离得远,又不能正眼看皇帝,自然就看不见他神色。文武百官却是偷偷瞄着皇帝脸色呢,满朝文武本来就对楚离着装不满,如今看见皇帝神色,心中无不暗自嘲讽。这无知贱民,怎可堪当国师大任!更何况还是个女人。就只等着皇帝发怒,让这个小姑娘吃些苦头离了这里。
哪料拓跋焘阴沉之色只是一闪而过,竟对楚离笑道,“国师免礼,怎么这样就上朝来了?”
楚离道,“启禀皇上,民女……微臣看那官服,竟似道教着装。可微臣既非道教中人,怎可穿它门中服饰?所以没穿。”
群臣哗然。
拓跋焘问,“爱卿不是道教中人?”
“自然不是。”
“那也当不是佛门中人。”
“也不是。”
拓跋焘顿了顿,“可是出家人?”
“算不上。”
一番问下来,群臣议论纷纷。
高平公李顺李尚书道,“皇上,以女子为国师,已经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更何况这小女子又非出家人,何德何能堪为国师?”深受皇帝宠爱的尚书一开口,朝中大臣立刻分成三派,不少人跟着李顺进谏,“请皇上三思!”
拓跋焘没说话,一旁东郡公崔浩崔司徒上前一步道,“李尚书此言差矣。楚离年纪虽小,然则月前清凉峰辩法,文武百官所共见,敢问诸位有谁能与她一辩?女子之身又何妨?李尚书博学多识,岂不知,殷商之时女将军妇好上阵杀敌,不输人后。东汉有女史班昭,世人尊为‘大家’,汉和帝多次召入宫中为皇后和贵人之师,邓太后临朝后,她还曾参与政事。女子只要有才德,哪里输了我们这些儿郎?”崔浩又转而问楚离,“何况国师虽非出家之人,但必是方外之人。下官所言,是也不是?”
看起来这个崔浩像是在帮自己……楚离想了想,答道,“是。”
崔浩满意地笑了,对皇帝说,“皇上,国师一职,应为天下之师,解天下之惑,却并非只有出家人才可担此重任。楚离是寇天师延请的方外高人,又是天师认定的国师,出任国师乃是顺理成章,再合适不过了。”
咦……楚离听着奇怪,竟然说她是寇谦之认定的国师?难不成这是拓跋迪为了给自己洗脱罪名糊弄了崔浩?楚离抿唇不语,心想一定是这样。不然,怎么能洗脱自己的嫌疑呢?多亏了拓跋迪。只是不知道寇谦之到底怎么样了。
崔浩说罢,也有一小波人跟着道,“皇上,崔司徒言之有理。既然是寇天师认定的人,自然不是等闲之辈。”
还有一些人始终不说话。连楚离都看出来了,这文武百官不是以李顺为首,就是以崔浩为首,剩下那些大概是中立派。
李顺道,“没想到崔司徒不仅人长得像女人,连心地也都向着女人呢。”
崔浩脸色立变,“李尚书什么意思?”
“好了!”皇帝拓跋焘及时开口,“两位爱卿不必再争,你们本是姻亲,该和睦亲爱才是。”
李顺和崔浩二人停止争辩,脸色都不大好看,只得答道,“谨遵皇上教诲。”
拓跋焘又道,“至于楚离出任国师,朕圣旨已下,不容更改。”顿了顿,接着说,“楚离之能,诸位爱卿冬祭之时,已亲眼所见。这无须再议。楚离,”拓跋焘转而问她,“你既然非佛非道,那么师从哪方?”
楚离想了想,“如果非要说的话,我该是出自道家。但对我来说,只是倾向于道家。实际上,诸子百家皆有可取处,我主张海纳百川。”
一时朝堂俱寂静。
直到崔浩深深看她一眼,意有所指地道,“国师胸襟,非我等能及。只怕有些俗人自以为是,还以为国师不堪此任。”
李顺如何听不懂他话外音,怒哼一声。
拓跋焘哈哈大笑,“好,国师有如此胸襟,是我大魏之福分哪!”又说,“朕看辩法之时,国师似是对佛门有诸多不满呀?”
“唔,”楚离虽然直觉这话问得有点蹊跷,但她初涉朝堂,又不经世事,不知此话深意,只如实道,“并非如此。”
“嗯?”拓跋焘没料到她否认,眼神有些凌厉起来。
楚离不为所动,只自顾说,“皇上,我反教不反义。”
“什么意思?”
“就是我反对教派,但不反对佛经。”楚离直言不讳,“道教也是如此。我反对道教,但不反对道教经典。”
“这却是为何?”
“皇上,无论佛道,它们各自的经义都非常精妙,乃不可多得的大智慧,理应继承发扬光大。”楚离沉声道,“但是,聚众成教却是大大不该。就如佛教,当今天下,百姓十之七八都入了佛门,如此一来,天下人无论懂与不懂、能与不能,都聚在一处,不事生产,只求佛问道,这天下焉能不毁?”顿了顿又说,“再者,佛教享有种种特权,大肆圈地占田,已俨然成为蕞尔小国,僧徒骄奢淫逸,误导百姓,哪有半点求真求智的样子?挂羊头卖狗肉,还白白侵占天下良产,岂不可恨?”
她直抒胸臆,刚正不阿,正中拓跋焘下怀。拓跋焘隐去唇边笑意,神色严肃道,“国师所言甚是。只是,不知该如何处置呢?国师可有高见?”
“高见谈不上,”楚离全无半点心机,旁人问什么她就答什么,根本没注意到朝堂上大臣们已经噤若寒蝉,视她如眼中钉肉中刺,只自顾答道,“皇上,这天下佛教猖獗,却佛不是佛,人不是人,人神不分,佛魔不分,绝不能再放任。微臣以为,应当严格控制寺庙和僧侣数量,不能任由其大肆发展。不然,再这样下去,只怕天下尽是佛门,再无百姓。民生尽毁矣!”
良久,拓跋焘一声长叹,竟流下泪来,“国师所言甚是!朕糊涂,竟不知其中利害,险些毁了我大魏百年基业,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楚离一下看傻了眼。怎么的,这还把皇帝说哭了?
“众爱卿,国师所言,你们也听到了,可有异议?”拓跋焘脸上泪痕未干,哽咽着问文武百官。
这种情形下,谁还敢说个“不”字。
崔浩接道,“皇上,国师所说,句句关乎家国社稷,理当尽数奉行!”
后面随即不少人跟着崔浩进言,“望皇上纳谏!”
拓跋焘含着泪眼望了一眼李顺,李顺一哆嗦,连忙跪下,“国师所言,句句在理,臣请皇上纳谏!”
李顺都跪下了,立刻文武百官跪成一片,“请皇上纳谏!”
“……”楚离一头雾水。怎么这会儿没人打击她了?她有些茫然地环顾了跪着的百官,又看向拓跋焘,竟见皇帝一脸满意的神色,“既然这是众卿家众望所归,又是国师亲谏,朕焉有不从之理?好了,都起来吧,即日起,就按照国师的谏言,控制寺庙和僧侣数量。”说着顿了顿,“详细的,等退朝后朕裁定拟旨。”
楚离又道,“皇上,如果这样的话,还有一件事。”
“国师请说。”拓跋焘似乎恨不得她多说点。
楚离心里觉得奇怪,一时也搞不清缘由,只好说自己想说的,“百姓入佛门,多因税务繁重,不堪重负。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佛寺人数众多的问题,还请皇上减轻赋税,与民休养生息。”
拓跋焘顿了顿,“国师一心为天下苍生计,朕岂能辜负国师一片心意?这样吧,”拓跋焘道,“今日国师所说,朕都着人拟旨实行。另外,寇天师在时,朕奉他为天师,特许他不称臣,不过天师自谦,素来以微臣自称。朕观楚国师似是不喜这等称谓,那么也免了吧。”
满朝文武都听着楚离一会儿“微臣”一会儿“我”的换,极为不悦,只觉得她实在是无知贱民不通宫廷礼仪。却没想到皇帝竟然对她如此厚待,居然可以像前任国师一样免称臣,顿时群臣寂然,看向楚离的眼神立刻不一样了。
第18章 【钗头凤】18()
退朝后楚离还是云里雾里的。
这头回上朝上的,跟看戏似的。楚离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可她又想不通其中利害关节。还没刚出大殿呢,身后呼啦围上一圈人,七嘴八舌的说着什么。楚离一下懵了。她刚听见这人说了点,那边又有那人说话,这么多人一起说,杂乱无章的让楚离觉得脑子不够用。不过她看看这些说话之人的神色举止,好歹是明白了,估计都是在说些奉承话。楚离木着一张脸,不知该如何应对。她虽然不惧与上千人谈佛论道,但对于这种明显不知真情假意的人情应酬,显得乏力而又无措。
于是只能木着一张脸,万年的面瘫脸此刻发挥了极致的作用——安神。
百官见此情景,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