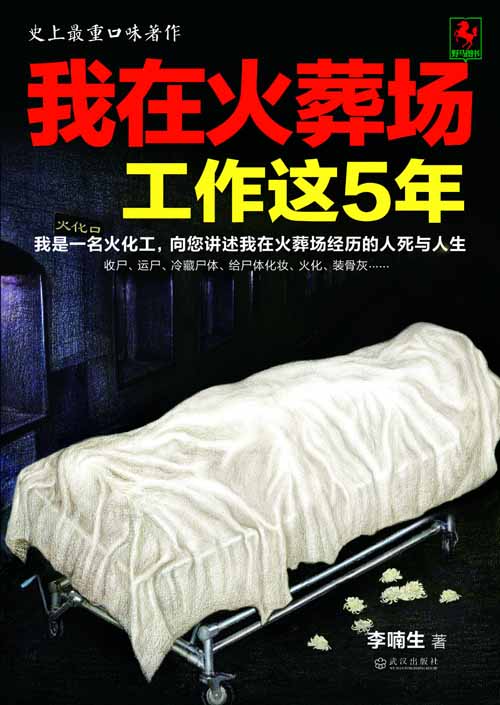火葬-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殉葬”的是一百九十四个敌兵!
苦战了五天,河岸上的一营人,只剩下两排了。
敌人本想用很小的兵力拿下文城,我们的一营人用敢死的精神惩罚了这个狂傲的错误。敌人增援;我们的援军,可是没有来到。敌人有炮,我们只有轻武器与足用的弹药。敌炮施威,我们的人散开,各自为战。敌人的炮火失去了应有的效力,而我们的枪弹象一种有知觉的东西,到处去找敌人的头颅与胸口。敌人改变了进攻的计划。把士兵们分成好几路,分头渡河。我们分散开了的士兵,没有集中与同时歼灭各股强渡的敌兵的可能与力量。所以,一部分敌兵已过了河。
唐连长一见敌兵过了河,就知道我们已无望及时的得到援军。他把埋伏在城郊附近的人全拿上去截击渡过河来的敌兵。在城郊与河岸之间,他支持了三天,敌人到了东关。唐连长已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几乎可以立着便睡去,可是他的脸上还不断的笑着。笑着,他指挥;笑着,他射击;笑着,他前进或后退。前进,他在最前,后退,他在最后。看见他的笑脸,弟兄就好象看见一股温泉似的,心中立刻感到温暖,而把一切危险置之度外。我军与敌兵的装备几乎相差了半个世纪。我军与敌兵的数量相差不止好几倍。多么艰苦的任务啊!可是唐连长的笑脸教弟兄们忘了一切,而只顾向敌人射击。
一手一支枪,唐连长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还匀出手来从腰间抽出一根大葱,咬一大口。咬一口葱,眼中流出点泪来,他感到一点舒服,身上轻松了好多。
退到东关,他教弟兄们到西关去守车站,他自己进城去看看县长。大家都已疲倦得抬不起脚来。他把没咬完的三根大葱扔给了他们:“咬口葱,跑步!”他的大葱的效力不亚于仙丹,立刻把大家的精神提起,一气跑到西关。
唐连长在东大街遇见县长。县长的眼睛至少和连长的一样红,而脸上的神色比连长的更疲倦。县长是个四十多岁的矮胖子,很忠诚,很慈善,只是不大懂现代的军事。“怎样?连长!”县长紧紧的握着连长的手。
“敌人已到东关!”唐连长用笑容冲淡了语气的紧张。“是吗?”县长把汗手抽了出去,楞了一下,转身就走。“往哪里去?县长!”唐连长向前赶了一步。
县长脸上的神气是忠厚人偶尔想露一露聪明,不敢自傲,而又不能不自傲的那一种。“他们已经预备好了滚木礌石!”“谁?”唐连长没法抑制住自己的惊异。
“壮丁们!他们还预备了石灰罐子,等着把敌人的眼睛都迷瞎!”说罢,县长又要走。
唐连长把县长一把拉住:“县长!你该走!带着壮丁们走!你的石灰罐子一点用处也没有!”
“走?”县长仿佛永远没有想到过这个字,不住的眨眼。“走!快走!敌人不会马上进城,”连长极负责的说:“他们必定先把城外的防御都扫清了,才敢进城。快走,还来得及!”
“放弃了城池?”
“壮丁们没有武器,没受过训练,不能作战!即使有武器,也不该死守城里,敌人会用大炮轰击!”
县长立在那里,眼睛看着自己的手,好象向来没有看见过似的。唐连长猜不透这个忠厚的人在思索什么,他只好接着说:
“援军一时绝不会来到,敌人的兵力又比我们大的多,我们没法子守住城!走!快走!别白白牺牲了我们的没受过训练的壮丁!”
显然的,县长并没想起什么好主意来,他只问了声:“你呢?”
“我去守车站!我们守不住城,可是在敌人进城以前,我们能教他们多死几个,就算尽了职!走!县长!在路上,你若是遇见我们的师长或旅长,给我说一声,唐立华已死在了文城!”唐连长双手拉着县长,呆立了一会儿。连长低着点头,县长仰着点头,四只眼对看着,眼神说出来:“我们将是永远可以共生共死共患难的朋友,假若这次死不了的话!”“再会吧!”唐连长似乎还有许多许多话要说,可是只这么低声的向县长告别。放开手,象老虎看见一个什么肥美的小动物似的,飞跑而去。
县长赶上去两步,想说什么,他还有没有找到适当的话,唐连长已经不见了。
车站外的洋槐树林中,坐着二十二个人。他们都抱着枪,垂着头,昏昏的睡去。唐连长不忍惊醒他们,可是又不能不马上发命令;他楞了一会儿。但是,他们在昏昏忽忽之中,仿佛感到了唐连长的来到。没有什么声响与麻烦,他们都睁开了眼,立起来。向左右稍微一看,他们立刻排得相当的齐整。“坐下”唐连长低声的说。等大家又都坐下,他细细的看了一看:连副不见了,排长只剩了两位,勤务兵和火案敢情也都拿上了枪!连勤务兵和火案都算在内,才一共二十二个人!他舐了舐上嘴唇,回头向林外望了望,仿佛希望那些与他共患难的朋友还会从林外走来,虽然他明知道那些熟习的面貌与语声是永远,永远,见不到,听不着了!转过头来,他重视着地上,好象不敢再看面前的人,因为看到一位排长,就不由的想起另一位排长;看到勤务兵,就想起连副来。连副的小胡子与一闪一闪的白牙,张排长的斜眼,李万秋同志的六指,和……都在他的心中活着,都好似他自己身上的东西。可是,他们都上哪里去了呢?不能再想!再想,一想,他就会马上大哭起来。不是为怕死而哭,而是为给共患难的朋友献出心中的热泪。说真的,他们由死亡而得到光荣是映射在他自己,与现在还坐在他面前的每一个人身上。他,与坐在他面前的二十二个,会在阵亡了的朋友的光荣中找到他们自己的光荣。他应当大笑,不该落泪,可是,他笑不出来!他的眼中并没有泪,可是他用手去揉了揉。他应当赶快向大家说几句话,否则他也许真的大哭起来。话还没想好,他已叫出“同志们!”
“同志们!”他重了一句,而仍找不到话讲,楞了一会儿,慢慢的蹲下去。这一蹲,他身上的筋肉似乎弛懈了一些,他想起话来。一挺身,他又立起来。惯于在他脸上来往的笑容,又来到他的嘴角与鼻凹间。
“同志们!连火案算上,咱们只剩了二十多个人!我们已和师部失了联络,援军恐怕一时不会来到。车站上,纱厂里,还有许多粮食,东西。我们不能给敌人留着。马上就去焚毁!我没法子请示上方,但是我觉得——凭着我的良心——应当这么作!王排长,你带八个弟兄破坏车站!孙排长,你同八个弟兄破坏纱厂!我和其余的人死守这里;这里便是连部!也许,敌人马上就来到,我们抵抗!凭着我一个军人的良心,我的命令只有一个字,死!”
说完这段话,他的因困倦而发红的眼,发出些光,象两片流动的明霞。他的笑意由嘴角鼻凹扩达到眉梢。亲切的,慈善而又严肃的,他看着象亲手足似的二十二个战士。
二十二个战士没有任何动作与表示,只是脸上显出一种轻快与得意的神气。假若唐连长的脸是太阳,他们的脸就好似接受到阳光的花。
“王排长,孙排长!马上出发!”唐连长和两位排长握了手。
不出唐连长所料,敌人不敢进城,而先在四面的关郊细心的搜索。在南关北关,他们没有遇到枪弹与手榴弹,只搜出不少手无寸铁的壮丁;随便的选择了一下,有的留下作苦力,有的死在刺刀下。
将近黄昏的时候,文城城内静寂得象一座古坟。小儿抱着母亲的膝,老人藏在屋中最黑暗的地方。年轻的妇女把脸涂黑,穿上最破的衣衫,象看到猫的老鼠,向门外,厕所,和最不舒服的地方乱躲乱藏。没人顾得作饭,泡茶,或点灯,而只想象着由门板刺进来的刺刀的可怕!他们知道敌兵已到了城外,逃走是来不及了。他们知道我们的守军,那给他们打了好几个胜仗的守军,已经都躺在了城外的黄土上。他们知道,县长已把学生和壮丁带走,城里已没有一个可以拿木棍或花枪和敌兵拚命的人!怎么办?怎么办?谁也没有一点主意!他们已经没有心思去想明天,因为死亡就在眼前;他们知道自己是拴在屠场的猪羊,刀已经离他们的脖子不远!刀,或者还是最好的东西;怕只怕,敌人还有比刀更厉害的刑具,最爱体面的姑娘本能的感到她们的刑罚必定不是刀,而是绝对不能忍受的污辱。她们有的上了吊,有的把剪刀揣在怀里。最亲爱的父母,在这时候,不能给她们半点安慰与主张,而只呆呆的看着她们采取最聪明或最愚笨的办法。聪明与愚笨,在这时节,已失去界限;因为快要进城来的敌人是人兽未分的动物!悲泣,自杀,黑暗,恐怖,教文城城里静寂得象一座古坟。实在没有主意了,他们反倒盼望敌人快些进城,杀剐存留,给个干脆!
正在这个时候,西门外起了火。城内没有一个灯亮,城外起了好几个火头;城是黑的,天是亮的;人们开始由黑暗的角落里出来,在门外呆呆的望着火光。火光永远有一种悲壮的吸引人的力量,不管是在什么时候。火光给大家一点刺戟,大家都想狂喊几声,把心中的黑暗吐出来,而使自己与火一样的光亮。可是,大家并没敢喊叫。看看那把半个天烧红的火光,他们反倒觉得分外寒冷,不住的打噤。这悲壮而有吸引人的力量的红光也给人以渺茫之感:没人能抓到那光,或挨近那火;火与光中宜示着毁灭死亡!
“烧啊!烧啊!”忽然一位老人狂喊起来:“烧了房,烧了城,不给日本鬼子留下呀!烧啊!烧——”
这个呼声几乎没得到任何响应。它没使大家兴奋,也没使大家恐惧。当最大的危险来到眼前,人们反倒在表面上露出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样子。随着这呼声,大家低声的彼此说了点什么;此外,别无动作。
那老人——城中最正直刚强的教过私塾的先生——还在喊,而且把一玻璃瓶洋油倒在土炕的草褥子上,预备放火。
这时候,城外的火光忽然暗了一些,漆黑的烟柱,象受了什么不可忍的刺戟与压迫,疯狂的往上冒,似乎要把星天变成黑幕。烟钻得极高,下面的火舌变成无光的血红,从黑烟里吐出来,又吞进去。烟在高处散开,火光又明亮起来,把天都照亮。这时候,城内老人的草褥已经燃起,老人仰卧在火光里。不久,黑烟与火舌从门窗内吐出,比城外的小,而热气直扑到人们的脸上。大家开始喊叫,开始奔跑,争着来救火。这时候,城外有了枪声。
“唐连长还打呢!还打呢!”大家的心又欣悦的跳动起来,几乎和前几天打胜仗的时候一样。
城外,有铁路路工的帮忙,士兵们把所有应该破坏的东西都付之一炬。火起来,他们散开,各自为战。敌兵到了,首先尝到槐林中射出的子弹。
敌人一方面包围槐林,一方面到所有能藏人的地方去搜索。不管是树林,还是独木,不管是一道浅沟,还是一堆垃圾;不管是一段矮墙,还是铁道旁边的小木阁子,都使他们迟疑,害怕,只在一阵两阵三阵猛烈的射击之后,他们才敢前进。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而只感到这里的树、沟、土堆、墙、和一切东西,都有眼睛,都有子弹,都会要他们的命。火光把整个的车站,照得如同白昼,但是火光越明,他们越怕;他们只能象蛇似的爬伏在地,看到一个黑影或黑点,便把头贴在地上,火忽然明了,又忽然暗了;火忽然移向东边,西边暗起来;又忽然移向西边,东边暗起来;在这一明一暗,忽东忽西之中,他们惶惑、恐惧,只管放枪壮自己的胆子,而不管子弹向哪里打,和打什么。
从一株树后跑到另一株树后,唐连长和他的六个弟兄变动着地位,向四面八方射击。唐连长的汗把袜子都淹湿。天气还相当的冷,他的身上可是只脱剩下了一件汗衫。他的心中,现在完全是空的,假若还有什么感觉的话,他只是想喝水;他的口中冒着火。在敌人的枪声稍静一点的当儿,他倚着树吐了口气;更想喝水。从树旁来了一只手,轻轻的放在他的腿上。他以为是那个也拿着枪加入作战的勤务兵呢。不是,地上卧着的人,不是兵,而是个铁路工人。“给你!唐连长!”工人声音很小,而很清晰的说:“三个馒头,一瓶水!”
唐连长顺手把馒头接过来,马上扔在地上,再伸手,他摸到那玻璃瓶的脖子,很凉,很滑;他的心里也立刻感到清凉滑润。水有点煤油味,可是他一气把它喝光。“哈!”他吐了口气。这时候,他才觉得工人的可感与冒险。没顾得道谢,他教工人快走。工人递给他一支香烟。
唐连长摇了摇头。“快走!谢谢你!”
敌人的枪弹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