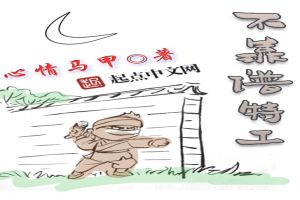乌泥湖年谱-第8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老师和他哥哥吴安林都发了言,他们表示一定要同吴松杰划清界线。会上,宿舍里的几个红卫兵看到他的反动诗,十分气愤,用剪刀把吴松杰的头发都剪了。现在,李老师要把吴松杰永远赶出家门,还要离婚。吴松杰不肯,李老师就在家里大吵大闹。吴安森的外婆也帮着他妈妈闹,已经闹了好久了。本来吴安森和吴安林没怎么闹的,可是后来,不知怎么回事,他们也闹起来。吴安林还打了他爸爸几个嘴巴子,说他爸爸是败类。后来吴松杰就一直蹲在窗户下面,两只手抱着头,一声也不吭。
三毛和嘟嘟直跺脚,这样大的一场热闹又没看到。连刘四龙和刘五虎都抱怨道:早知道就不去武大了,一个像章也没有要到,还错过了看批斗会。
对于吴家,三毛第一讨厌的是吴安森的妈妈李老师,这李老师总是阴声阳气地挑他的毛病,弄得他心烦。其次是吴安森的外婆,老太婆成天唠叨他们,又是说他们把楼梯弄脏了呀,又是说中午吵得她没睡好觉呀,动不动就来告状,没一天对他们满意过。第三讨厌吴安森,吴安森特别不讲道理,喜欢跟人打架动粗,特别是伤了刘四龙的眼睛,不可原谅。吴安森搬来这里这么多年,怎么都跟三毛和楼下的刘四龙玩不到一起去。三毛惟一不讨厌的人就是吴安森的爸爸,三毛觉得他看上去心眼挺好。有一回三毛连奔带跑往楼下冲,结果冲猛了,刚跑了一半,就摔了下去。
吴安森的爸爸正好下班回来,他扶起三毛,还帮三毛撩开裤腿,看看有没有伤口,然后又把三毛背了回来。因为这个,三毛每次见到吴安森的爸爸都要礼貌地叫一声:“吴叔叔好。”但是,吴家这个惟一让三毛有好感的人,却写了反动诗。这使得三毛格外生气,仿佛有一种受骗的感觉。刹那间他连吴安森的爸爸也讨厌起来,三毛觉得他们家没一个好人。那么,坏人跟坏人吵,也就不是什么坏事情了,这等于让他们自己跟自己斗,斗倒一个少一个。
三毛和嘟嘟迫不及待地穿过围观的人群,回到自己家中,他们兴奋地要将他们一天的经历讲述给爸爸妈妈听。但是雯颖和丁子恒却对他们这一天的故事毫无兴趣,他们一直关注着隔壁的吵闹,悄悄地谈论着蹲在窗下的吴松杰。从他们的谈论中,三毛知道,吴松杰已经一天没有吃饭。可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三毛自己不也一天没吃饭吗?难道那个写反动诗的坏人没吃饭比三毛没吃饭更重要些吗?
三毛想着使有些生气,他突然扯开嗓子高声地叫了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已经一天没有吃——饭——啦——”
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叫喊,把丁子恒和雯颖吓了一跳,也令楼下围观的人大吃一惊,大家似是怔了片刻,然后醒悟,立刻发出快意的笑声。笑声过后,吴家的吵闹也陡然停止,就像收音机突然间关掉了一样。
这样的效果,出乎三毛意料之外,原本他只想恶作剧一下,不料却结束了一场坏人之战。他对此觉得颇为遗憾。
十四
输送寒意的北风仿佛毛虫,慢慢地,不慌不忙地向前爬行。它先改变掉树的装饰,再改变掉人们的外表,最后,它终于顺着人们的骨头爬进了人们的心里。不知不觉间,萧萧瑟瑟的秋天不知去向,里里外外驻满冬日的苍凉。
轰轰烈烈的运动丝毫没有因为天气的寒冷而降下它的温度。院里各处室已经成立了许多兵团,有消灭帝修反兵团,有红旗飘兵团,有兴无灭资兵团,有心向党兵团,有卫东彪战斗司令部,诸如此类。整个总院内,一共有多少兵团组织,丁子恒始终没有弄清,他只觉得这场面的混乱好像封建割据或是五代十国再或是军阀混战时的样子。
总工室的吴思湘和金显成都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了大楼的地下室。
那里阴暗而潮湿,因为没有暖气,里面的寒冷也让人难以忍受。他们每天在那里写交待材料写揭发材料写反省材料。一想到那些黑屋里的人,丁子恒便身不由己地心惊肉跳。
各兵团又开始批判省委工作小组的反动路线。工作小组组长王副省长的历次讲话被一条条列出来,逐字批判。施工室为写批判省委工作小组的反动路线的文章作了专门的分工,丁子恒也要写一个部分。可是为什么批判或是批判前和批判后的观点有什么实质差别,丁子恒并没有弄清楚。没有为他解惑的苏非聪,面对这样的形势他很是茫然,他觉得自己对这些事情总难抓住头绪。有些政治词语他觉得彼此差别很小,可是政治敏感度高的人一分析,便能分析出极大的差别来,这差别常常能把他吓一跳。因此,他平常说话也不太敢引用政治术语,生怕自己一句话用得不对,倒成为反面语言。这段批判文章,难为了他许久,最终拿出来时,他自己都知道一定过不了关。结果正是如此,批判小组的一个成员说:“算啦算啦,丁工就只有这个水平,也别再难为他了。”为这一句话,丁子恒对这个成员说了至少十声“谢谢。”
这天,终于开了一个词语明朗的会议,丁子恒终于有了自己敢说并且会说的内容。这天的会议是讨论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这指示令丁子恒长舒一口气,他想,进行这样的讨论,会不会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呢?于是他主动地发了言,讲了几句套话以后,很快就转到促生产上。他说了一些宝珠寺和乌江渡的问题,最后强调说,工作如果不抓紧,预期时间一定完不成任务,这样就没法向四川省交待。
他的发言一结束,便有人笑:丁工一讲政治,就找不到词,一讲生产,话就多了起来。再贴他一千张大字报,他也还是这样。这话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丁子恒一时有些惶恐,可环视了一下笑他的人,发现这些笑声并无特别的恶意,方将一块石头从喉头放到心底。
乌江渡的总布置平面图是丁子恒的主要工作,丁子恒把自己埋进了乌江渡的资料堆里。虽然他紧张的心情并未松弛,但他在做这些事情时,总还能暂时忘却其它,总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份淡档的愉悦。他先贴好1:5000的乌江渡地形图,又找来1:2000的乌江渡地形图,将之晒成四份。他反复研究乌江渡的布置,觉得这里地形复杂,高差大,地位窄,布置起来实在很困难。就算充分利用废渣造滩,仍然难以拉开场地。因为这些难度,工作量陡然加大。关于附属企业占地面积,关于钢管安装场地的位置,关于仓库区的平整工作量,关于右岸桥头平整高度,关于车站附近的填方,关于汽车基地前方仓库,关于运输的费用,关于公路货流,关于运输强度,关于土石平衡,如此如此,大量的工作必然耗用大量的时间。而所有的工作,必须在无数的生产会议开过,大家意见达到统一的情况下,方能一一开始。然而,整个的生产秩序已经被打乱,人们已无心坐在桌前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各种会议接踵而至,没有会议的时候,大家又必须进行许多问题的学习和讨论,然后还要去看日新月异的大字报。各兵团人马除了一个接一个地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和四处揪斗人以外,还安排有兵团自己的系列活动。如此一来,生产会议总难召开。丁子恒心中焦急,却也无可奈何。
无奈中,他只得去找每一个相关的干部,找室主任,找书记,找革命委员会委员,找工会组长,找施工室每一个兵团的负责人。他跟所有人都说,乌江渡的工程时间很紧,工作量非常大,这个工程并不是设计总院单方面的问题,还牵涉到四川省。毛主席说要“抓革命,促生产”,毛主席还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必须每天抽出最少半天时间来完成生产任务。每一个听他说这些的人都不耐烦,生产任务对他们来说显然没有意义,眼下革命才是最要紧的。再说比起生产的辛苦,革命也要有趣得多。丁子恒面对一个个不置可否的回答,显得有些尴尬。最后还是尚未彻底打倒的室主任说话了。室主任说:“丁工你就做你的去吧,有人批评你,再说。”
丁子恒听得此话,如蒙大赦,此后他便每天上午坐在桌前计算或绘图。开始他还有些忐忑不安,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竟然什么事也没有。他这才意识到,对于他这样的小人物,倘若他自己无意闹革命,革命也未见得非要找到他们上来。他为自己无意间发现一片天地而欣喜若狂。
这天下午,学习《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学习中,分别属于两个兵团的人争执起来,争执尚在高潮之中,突然外面人声喧哗。有人高声说:“林正锋昨天晚上被人绑架走了,现在下落不明。”
这个惊人的消息令满屋争吵戛然而止。丁子恒正心不在焉地听他们吵来吵去,闻得这声喊叫,惊愕半天,然后是木然。许久,一种莫名的凄凉由心底升起。想到人生在世,命运竟如此变幻莫测,忽而沧海,忽而桑田。就算人有铁腕,也无法把持得住。林院长已是通天人物,却也无法保住自己。他革命革了一辈子,可是人们一旦要革他的命,立刻就可以把他革得去向不知。就算以后有了下落,不也如同砧上之肉,任人割宰吗?一个人活在世上,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这样的革命就是最好的吗?革命的目的,是要保住江山不变颜色,可是一个江山,什么样的颜色才是最好的颜色呢?红色江山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好人?一个人连自己是不是好人都不知道,他又怎能明白自己是否忠于无产阶级专政呢?无产阶级专政是否需要那么多的兵团,各行其是,而把生产停顿下来呢?工厂停工了,大坝工程下马了,农民不种田了,是不是江山就红透了?那是一种什么红?是人血染的红色吗?丁子恒思绪散漫,想到此时,他被自己所想的吓了一跳。他的心怦怦地跳着,有一种作贼心虚的感觉。好在这一切思绪,都被封闭在脑海中,无人知晓。
丁子恒告诫自己,以后连这种胡思乱想都最好都不要再有,万一不慎,流露于言行,那连地下室都没得坐,定然要掉脑袋。
仿佛自这天起,丁子恒工作的速度就慢了下来。虽然他每天上午仍然雷打不动地坐在桌前计算,但他觉得自己做这些事情已经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内心很空,很虚,很茫然,很混乱,乌江渡的工作是他生命中惟一的寄托。他做这些事,就仿佛一个溺水之人紧紧地抓着一根小小的木头漂流在茫茫的大海上,这根细木或能令他在波浪中起起伏伏,渡水抵岸。又仿佛一个深夜的迷路者看见了一线曙光,这一线曙光一头牵着太阳,另一头拉扯着他的生命,让他不致被暗夜吞没。
寒冷的冬天就在有人兴高采烈有人垂头丧气有人迷乱茫然有人惶惶不安中大踏步深入。天色也越发阴冷,冷得让人觉得是不是两个严寒叠在了一起。
这天上午是援越抗美游行活动。游行进行了三个小时,长江流域规划总院出动了许多人。他们举着旗帜从机关出来,一直走到中山公园。行在路上,各兵团之间,一边为各自的观点争吵不休,一边骂美帝国主义。丁子恒几乎分不清那骂声到底是针对美帝还是针对观点不同者。其它单位的游行队伍也从一条条小路汇合到解放大道上,每逢两支游行队伍相遇时,大家便一起高呼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情绪十分热烈。这时还常常会有人领着头唱起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歌声往由几个人开始,然后不断有人加入,渐渐地变成巨大的声音,那声音使人产生的幻觉,仿佛凭此呼啸之歌便足以将美帝国主义埋葬。
在群情激昂的气氛中,游行结束,回到总院。一进大门,队伍开始散乱,人们各自找捷径回自己的办公室,亦有人留在大字报栏前观看新贴出的大字报。更多的人则是直接往食堂而去,因为距午餐的时间已没多久。
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发出了惊呼:“哎呀!烟囱上有人!”这呼叫有如惊雷贴着头皮炸开,人们几乎同时朝烟囱上望去。
众多的声音叫着:“是谁呀?是谁呀?”
有人认出了烟囱上的人,大声喊着:“是吴松杰!”
人们纷纷跑到烟囱下面,瞬间,烟囱下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人。尚未被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