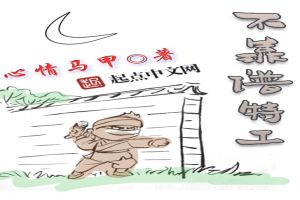乌泥湖年谱-第7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刘格非的言论很快传开。人们再见到刘格非时,眼睛里便有了另一种内容。刘格非吓得要死,在家里夜夜骂他老婆:吃饱了饭多放几个屁也好,多什么嘴呢?刘格非本是一个斯文人,到这时候,也顾不得斯文了。秦云岚自知犯下大错,不敢再多言,只是每天尽量把饭菜烧好,好让刘格非顺心顺气。
但想要刘格非顺气已然不太可能。只几天工夫,院里关于刘格非的大字报便上了墙。对于刘格非来说,最严重的问题并非他老婆嘴里传出的那几句话,而是去年年底他为毛主席诗词拟的灯谜。一张大字报说,这是利用毛主席诗词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这一张大字报便足以使刘格非魂飞魄散。
几乎从这天起,刘格非便成日低着头。走路低头,开会低头,工作低头,谈话亦低头,仿佛颈椎已断,全然支撑不起他那个头颅。刘格非长期伏案工作,原本就有颈椎病,一个礼拜低头下来,颈椎病犯了,压迫神经引起头疼,疼得连牙根都受牵连,一张脸疼得变了形,却不敢去医院。秦云岚急得跪在观音菩萨前哭求保佑。
刘格非忍着头疼,抓起老婆的观音便砸,砸完低吼道:“你还想给我惹事!”
全院都在批判“黑灯谜”。讨论中对“黑灯谜”的分析也越来越透彻,越来越深刻。透彻深刻到刘格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些灯谜乃自己所作。毛主席的诗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句,是多么伟大而豪迈,多么雄壮而深沉。而刘格非给的谜面却是“不是对人说话”,这分明污辱和漫骂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诗曰:“喜看稻菽千重浪”,分明是歌颂中国农村丰收景象,刘格非却说是“西风里参观平原秋庄稼”,刘格非把自己对西方花花世界的向往栽到毛主席身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词曰“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刘格非却用用“后背心挨了一拳”做谜面,从这些字眼上就能看出刘格非反对和嘲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阴暗心理。
刘格非纵然是低着头,天天写检查,一天比一天深刻,把自己骂得一天比一天厉害,却没有人想要饶过他。分析黑灯谜的文章还是接二连三地贴上墙,除此以外,他过去写的一些文章也被翻出来。他的文章许多都是介绍苏东坡诗文的。他盛赞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一句。说是苏东坡这首词,虽是大气磅礴,呼啸之声豪迈而起,但若无此句所给予的格调和情怀上的升华,整首词也就流于一般。正是这声“人间如梦”的苍凉长叹,将此词提拔而上,深刻而下,成为永世流传之词。大字报说,刘格非的对苍凉趣味的欣赏和把玩,正来自他自己的内心情感。他对他过去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资产阶级生活留恋万分,对新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深怀不满,故长期抱有苍凉之心。刘格非还对元代小令写过诸多赏析文字,其中两篇被诸多大字报揭露。一是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之一:“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蜘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另一首是关汉卿的《四块玉·闲适》之一:“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什么?”前一首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刘格非欣赏此诗,目的是要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对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带给人民的幸福生活,刘格非视而不见。却借赏析古诗之名,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政府领导,人民所有的只是痛苦,简直是恶毒之极。而后一首,则是刘格非借关汉卿之口而表达自己的消极和愤世之情。刘格非他愤的是什么世?他因何而消极?他为什么而不平?
刘格非每天晚上都重新写检讨,因为每天出现的大字报会提出些什么新的问题,他无从预料。他的检讨越来越糟贱自己,糟贱到他不知道还有什么词可以一用的地步。然而最糟糕的是,他的检讨中的句子也开始被人用引号勾出,进行分析和批判了。刘格非再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才好。
一天在全院会议上做检讨时,他哭了起来。这天很热,会上的气氛有些紧张,俱乐部的电扇偏还有几台停转,屋子里闷热难当。刘格非的泪水和汗水混得一脸,它们蒙了眼睛,令他看不清纸上的文字,于是他一边哭一边用手不停抹着脸,弄得脸上白一块黑一块,脏兮兮的。
台下有人喊:“装什么可怜样子!”
“你难道觉得自己委屈了吗?”
“你哭成这样子,是想控诉新社会吗?”
“你作哀兵之状,是想博得人们同情吗?告诉你,没有人会同情一个反革命分子!”
刘格非在一片叫喊声中,身体一软,便倒了下去。会场上似乎因他的软倒而愣了一下,但只几秒钟,喊叫声再次涌起,会场上嘈杂得听不出人们在喊叫些什么。
在这混乱的叫声中,有人上台把刘格非架了出去。
当年下午,院里便贴出了刘格非的《认罪书》。
我的认罪书东风浩荡红旗扬,亿万人民心向党。毛泽东思想万万岁,前进路上有方向。
革命的同志们,我乃资料室刘格非也。今日犯下滔天之罪行,在此仅借白纸黑字,向诸位革命同志低头认罪。
正如人所共见,非乃一仪容委琐,粗服乱发者,望之便知不是好人。非长期以来,对新兴之中国心怀鬼胎,对伟大之共产党恶眼相向。非为发泄心头仇恨,曾尽心尽力进行颠覆破坏。或以黑灯谜污辱领袖,或借古诗词攻击政府,或假检讨书妖言惑众。非用心之恶毒之阴险之下流之龌龊,人所不齿,畜亦示憎。非一向扮以两面嘴脸,佛口蛇心,人前虽满面笑容,暗地却深藏祸心。非虽如常人之有心有肝,但非之心肝则含污纳垢,粪坑是也;非虽仿雅人之弄文弄字,然非之文字如驴鸣犬吠,聒耳而已。幸革命同志,火眼金睛,口诛笔伐,断然识破非之赤口白舌,两面三刀之阶级敌人嘴脸,使非乘伪行诈、倒行逆施之伎俩,莫能长久。古人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遭。又云:多行不义必自毙。非乃自作孽者也,非必自取灭亡也。今之非已形同狗稀,徒具人形,不打倒非,不批臭非,不将非之毒钉拔将而去,不足以泄众恨,亦不足以平民愤也。非在此求告诸位革命同志:非自即刻起,将延颈举踵,急盼批判之烈火将非熊熊燃烧。非愿被此火焚烧而死,以此而谢罪诸位革命同志也。
丁子恒从工地回到家的当天,便看到了刘格非的这份“认罪书”。他的心咚咚咚地跳得异常猛烈,一种痛彻之感从心口漫向全身。丁子恒不由自主地以手捂胸,仿佛是害怕剧烈跳动中的心脏会破胸而出。所有回家的快感,都被刘格非的认罪书冲没了。丁子恒突然想到四个字:血口喷己。
次日,谢森宝主任再次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传达省里意见。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运动。运动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自始至终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要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去学。
二、精读《宣传工作会议讲话》,放手发动群众,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分清知识分子中的左中右派。对中间派要团结批评或斗争,运动不要针对这些人。主要矛头要对准党内反党分子和一小撮反社会主义分子,即右派。
他们一遇机会就兴风作浪。
三、成立代表大会,是组织左派力量、团结多数群众的一个好形式。
四、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五、加强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要靠党的领导。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必将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
七、全省文化大革命运动,要争取有点有面,点面结合,普遍发展。运动要落实在大学毛着,改造世界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
关于写大字报一事,谢森宝特别作了强调:
文化大革命与四清是密切相联系的,是整党内的当权派,鼓励大家用大字报的方式。不过,中央负责同志的大字报不要贴,要转给办公室,不要乱贴在大门口。
重大政治问题和男女关系问题的大字报,不要贴,要交办公室。设计革命办公室,现改为文化大革命办公室。斗争锋芒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其他人要团结改造,不要都戴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
思想意识和反革命行为要区别开来,一贯与一时要区别开来。一律不杀不抓。运动时间暂定三个月。上午办公,下午搞文化大革命。
听报告时,张者也坐在丁子恒后排,他也刚从乌江渡回来参加运动。报告开始前,两人闲说了几句关于宝珠寺和乌江渡的情况,张者也突然凑到丁子恒耳边,压低了嗓子,说:“你知不知道,刘格非疯了?”
丁子恒浑身一惊,他几乎要失声喊叫。但谢森宝业已坐上了报告台,丁子恒的惊呼声终于还是咽了下去。张者也见丁子恒如此惊愕,便赶紧接着说:“昨天我见到他,他不断地用非常诚恳的语气说‘今之非已形同狗稀,徒具人形,不打倒非,不批臭非,不将非之毒钉拔将而去,不足以泄众恨,亦不足以平民愤也。’说完就哭,哭得眼泪鼻涕一大把,然后用手背抹来抹去,简直不知道让人说什么才好。”
丁子恒亦不知说什么才好,他心里乱成一片。幸而报告开始,谢森宝开始讲话,张者也匆匆又补充了一句:“院里把他送到六角亭精神病院了。”说完他坐直身体。
丁子恒觉得自已被张者也传达的信息击中了。九年前苏非聪被打成右派时的感觉,又恍若来到身边。命运仿佛埋伏在身边的困兽,一不留神便会扑过来大咬一口,令你遍体鳞伤,永伤元气。刘格非疯了。那个曾经在柳山湖农场与他畅谈苏东坡诗文的刘格非,那个曾经与他笑猜灯谜的刘格非,那个身材瘦小而神态洒脱的刘格非,从此再也不会出现。一个人就这么简单地淡出了你的生活,而你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淡出别人的生活。悲哀又一次笼罩了丁子恒的心。
“天公尚有妨农过,蚕怕雨寒苗怕火。阴,也是错,晴,也是错。”这是谁写的呢?丁子恒想不起来。但他能想起在柳山湖、刘格非同他谈论此曲时的表情。
刘格非的现状,给丁子恒带来莫大的不安。他在柳山湖农场与刘格非成天谈诗论文的事,许多人都知道。而刘格非的灯谜,他亦曾大加赞扬。这些与刘格非的交往,令丁子恒时时处于不安之中,他不敢想象,倘若有人把他和刘格非联系起来,呼啦啦地给他来一批大字报,他的结果又会怎样。
丁子恒的不安,有如感冒,传染了全家。二毛住校了,家里的两个孩子三毛和嘟嘟,都已学会察言观色,每天吃饭时,看看丁子恒的脸色,便一声也不敢吭。因为心思太重,丁子恒夜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觉。雯颖对此既担忧,又紧张。她不由自主地把自己也绷得紧紧的,随时随地看丁子恒脸色行事,生怕自己照顾不周,给丁子恒增加烦乱。
生活如此沉重,雯颖觉得自己未免承受不了。这天晚上,雯颖说:“子恒,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我看,你不如要求回到工地上去好了。反正那边的事情也多,而在家里,你什么事也干不成。”
仿佛“啪”的一下拉开了电灯,丁子恒心里蓦然间明亮起来。他想起金显成的“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之说。古人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工地正繁忙,我又何不回那边去呢?1957年反反复创的出差救过我一回,难道今年不能再救我吗?这么想定,心里立即轻松起来,这夜他竟睡得很好。
次日丁子恒便到总工室找到老总吴思湘,说他想立刻回到宝珠寺工地。吴思湘说:“你不是刚回来吗?”
丁子恒担心自己的动机被吴思湘看破,于是话间就有些忸怩。丁子恒说:“前两天,姬宗伟从工地给我来过一封信,说那边开始下雨,看起来今年的暴雨期可能比较长,白龙江多半会涨大水。所以,我想早点回去,把有些事情抢在洪水到来之前做完。工作一完我就回来参加运动。”
吴思湘笑了笑,意味深长道:“跟1957年相比,你已经聪明了许多。”
丁子恒没想到吴思湘会这样说话,怔了一怔,旋即明白,立即答说:“十年时间,通过政治学习,无论怎样,思想上都会有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