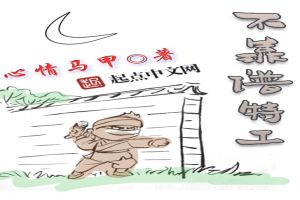乌泥湖年谱-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婆找到队部,向队长和政委哭诉,政委批评了王志福,令王志福做检讨。王志福不服气,说:就连毛主席家里都闹矛盾,我有什么闹不得的?他这完全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其次一条是,王志福一心想往上爬,每次搞完一项革新,都要跟人吹嘘说:人要升得快,就必须得有真本事,光晓得开会讲几句空道理,读几本派不上用场的书,有什么用?
他这宣扬的是什么观点?开会时什么道理是空道理?什么书是派不上用场的书?
总院对这封信非常重视,据说已找王志福谈过话了。总工室的人从王志福垂头丧气的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传说的真实性。
这天召开的室务会议是由总工程师吴思湘主持的。吴思湘的脸在秋阳映照下显得洁净而明朗。吴思湘说下月初,他将同林院长一起去北京参加部里的会议。会上,将讨论长江流域规划的要点报告。他的脸上不时露出一些笑容。接着又将业务工作做了些新部署:土壤化学室合并过来由总工室兼管;明年准备聘请灌溉专家,上半年人要到位;总工室两个副总工程师,一个负责唐白河,一个负责长江流域规划,等等。说完所有这一切,吴思湘把声音提高了,他说:“在反右斗争中,谢谢大家给我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段时间,我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都在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有人说这是些派不上用场的书,我觉得这个说法完全错误。我学了之后,大受启发,深深感到真理的伟大。我很希望在学的过程中,能同在座各位进行交流。”
吴思湘说完便含笑离去。丁子恒无意中看了一眼王志福,他的脸色灰暗,头垂得很低,一只脚在地上无聊地画过来画过去,样子分外可怜。
苏非聪捅捅丁子恒,说:“那小子蔫多了。”
丁子恒说:“他也算尝着了滋味。”
苏非聪叹一口气,说:“虽然这家伙先前批判起别人来,没说一句公平话。可现在,真把他打成右派,也实在太不公平。”
丁子恒想了想,说:“你说得也是。连他都成了右派,我就越发搞不清定右派是个什么标准了。”
丁子恒和苏非聪正说话,那边柴启燕对着王志福叫喊起来:“我说王志福,你光是坐在这里动也不动,挡着我正常走路了。”
王志福跳起来,说:“你有什么好神气的?不就是没轮上你当右派吗?喊喊叫叫干什么?”
柴启燕说:“你是什么意思?你挡了我的路,我还不能说,扯什么右派不右派的?你是反右积极分子,还能让你当右派不成?”
王志福“呜”的一声哭了,且哭且说:“你没见吴总的脸色,这不明摆着右派轮上我了?”
丁子恒有些不解,说:“这是什么话?吴总脸色好,与你有什么关系?”
王志福仍然哭道:“根据我们室的人数,右派指标是三个,除了邱传志和张云庭外。第三个本来应该是吴思湘的。现在……现在……吴思湘没事了,那……那个指标,还不到我头上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没想到会有今天!”
王志福的话令室里人都大为惊讶。柴启燕说:“会是这样?”
王志福说:“怎么不会?那你说,一共三个指标,我们室里除了我,还会有谁?”
苏非聪有些愤然,说:“哪有这样打右派的?又不是搞工程拉计算尺,拉个比例出来,尺这边是右派,尺那边是左派。数不够还得硬派上几个,这岂不是笑话?”
王志福止住哭泣,怔怔地望着苏非聪,半天没有说话。
更惊人的消息传了出来:王志福把苏非聪说的关于拉计算尺的话,写了份揭发材料交上去。这是直接攻击反右斗争,比其它任何言论都更为反动。总工室的第三个右派便迅速敲定:苏非聪。
丁子恒闻知此消息瞠目结舌。他只会张着大嘴,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大脑在瞬间完全空白。苏非聪跌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两眼发直,傻瓜一样,两只手在桌面上来来回回空抓着,什么也没有抓住。
丁子恒清醒过来,见苏非聪如此这般,吓了一跳,忙说:“苏工,镇定点,镇定点,说不定是误传。”
苏非聪完全失去了平常的潇洒和睿智。他的表情一会儿焦急,一会儿愤慨。同所有右派的紧张、凄惶以及胆怯不同,苏非聪表现出他的激烈和暴躁。他不时用强硬的口气说:“我不是右派。我坚决不能承认我是右派。这是人为的陷害。”
董凡和孙昱等人便驳他,说人家王志福揭发的话,的确是你亲口说的呀!
苏非聪便吼叫道:“我说我不是就是不是!”因为他的态度,在批判他的会议上,人们发言用词亦越来越严厉,苏非聪同揭发批判他的人不断地发生争执。
这天下班,吴思湘叫丁子恒去他的办公室。丁子恒进门后,吴思湘走到门口朝走廊方向张望一下,见无人,便赶紧把门关紧,且将门销插上。
丁子恒颇觉怪异,说:“什么事?”
吴思湘拉他到窗边,低声道:“苏非聪住你隔壁,是吧?”
丁子恒心跳了一下,说:“是呀。不过,这些日子我们并没有什么来往。”
吴思湘说:“我知道你是个谨慎的人。不过,你一定找个机会跟苏非聪说一下,不要用这种方式。要屈服,要认命,要为妻儿老小着想。否则,最后被送到劳改农场去就好吗?或者,枪毙掉……”
丁子恒吓得腿一软,顿时生出魂飞魄散的感觉。好半天方颤声道:“难道……
难道……会这样?“
吴思湘说:“我不知道会不会。但是我比你们年长,我知道政治斗争的残酷。
右派就是敌人,对敌斗争就是你死我活。我对你说这些话,也是凭着我个人对你的了解和对苏非聪的了解,请你一定规劝他。“丁子恒使劲地点点头。
这天回家的路上,丁子恒神思散乱,几次差点叫车撞上。行至蒲家桑园路边小店,他买了一盒香烟。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无助;感觉到作为一个人,他是多么孱弱;感觉到命运就像潜伏于四周的野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朝你扑来,将你变成垃圾。他的心更加迷茫,以至需要借助一支香烟来帮助自己镇定。
这些日子,苏非聪下了班便把自己关在屋里。苏家成天死寂一片,连孩子们都知道家里遭有变故,平日大吵小闹的尖叫声也一律消失。丁子恒总是只能见到愁苦着面孔,从厨房到家里忙进忙出的魏婉娴。
夜里,孩子们皆睡去,丁子恒慢慢地踱到苏家门口。魏婉娴端了一盆水从屋里出来。
丁子恒轻声道:“苏太太,能不能叫苏工出来一下,我有要紧事跟他讲。”魏婉娴露一副受惊吓的样子。丁子恒苦笑了一下,说:“我必须跟他讲。”
魏婉娴放下脸盆,折回房间。几秒钟后,苏非聪走了出来。丁子恒拉了他进到厨房。
苏非聪无精打采的,说:“什么事?丁工,你最好还是避点嫌为好。”
丁子恒说:“这我知道。只是吴总要我无论如何跟你说一下。”
苏非聪有些惊异:“吴思湘?”
于是,丁子恒把吴思湘对他所说的一切原封不动地告诉了苏非聪。苏非聪脸色大变,呼吸急促得可让丁子恒看见他胸脯的起伏。头上电灯散发着昏黄的光,煤炉已用煤泥封闭,只有一个小孔透露出一点红光,煤气味道缭绕在这个小小的空间。
突然,苏非聪剧烈地咳嗽起来。他仿佛被呛着了,咳得涕泪横流。魏婉娴立即冲出房间,她尖声叫着:“阿苏,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右派就右派,别气坏了身子。”
面对备受磨难的苏非聪,丁子恒心里百味俱生。他呆望着魏婉娴为苏非聪捶背,又呆望着魏婉娴将苏非聪手臂搭于己肩,扶着苏非聪缓缓走向屋里。丁子恒的眼泪禁不住快要流出。
被搀扶着往外走的苏非聪突然止步,他回过头,深深地看了丁子恒一眼,苍白如纸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他低声说:“谢你了,丁工。”
次日早上,丁子恒看到苏非聪时,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批判会上,苏非聪一反往日的强硬,变得唯唯诺诺起来。无论人们怎么批判,无论人们采用了什么样过分的言词,他都一律接收,一律认罪。
丁子恒的心更加痛苦。他突然觉得,亲眼看到一个人灵魂的崩溃,比亲眼看到一座大坝的崩溃,更让他胆战心惊。
批判苏非聪的时候,丁子恒发过一次言。他重复了一番别人都说过的话,显得平乏而空洞。依然有人批判他的“温情主义”,但这一回丁子恒不再重蹈旧辙。他沉默着,听着人们在批判苏非聪的同时,也批判着他。他想,虽然我承担不起“右派”这顶帽子,可是我同样也承担不起自己良心的折磨。
领导亦同丁子恒作了谈话,批评他的右倾同情思想。便有议论传来,说因为总工室只有三个指标,丁子恒才当了个“漏网右派”。这议论令丁子恒出了一身冷汗。
十四
这一年,乌泥湖有六家出了右派。他们是:
甲字楼上左舍吉迪成家;丁字楼上左舍苏非聪家;己字楼下左舍林嘉禾家;庚字楼下右舍李琛明家;辛字楼上右舍沈佳士家;壬字楼上左舍王唯康家。
十五
1957年的最后一天,也将被冷飕飕的寒风吹刮而去。这日下午,丁子恒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蹒跚在前的苏非聪。他的身影在阵阵扑面而来的风中,如飘如摇,而他的每一个步伐却又显得那么沉重。丁子恒远远地走在后面,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年初他们一起顶着风雪看房子的情景一次次浮在眼前,甚至仍能听到“咦?
一座寺庙;哦!两个和尚“的说笑。
如此,丁子恒心里涌出哀伤。他想,1957年瞬间将成往事。往事随风而去,永不复返。而人们却永远只会对着面前的日子说:新的一年来临了。
1958年(一)
百紫千红花正乱,已失春风一半。
——北宋·李元膺《洞仙歌》
一
一个下雪的早晨,苏非聪全家仓惶地离开了乌泥湖。这是离春节并不太远的日子。
总院的意思原本是让苏非聪下放到三斗坪工地,这其实是一个最轻的处理。同室的张云庭已送去了劳改农场,邱传志下放到外业队伙房。但苏非聪仍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生活中没有了自尊和骄傲,对他来说,犹如没有了水和空气。他用了自己最后一点勇气,向院里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然后,决定带着他的全家五口人和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返回老家。
苏非聪一家人走的时候,丁子恒已去上班。丁子恒不知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局面,也不知送他和不送他会有怎样的结果。他只能麻木着自己,采取一种听凭自然的方式。他想如果他在家,他就送一送,如果正好他必须上班,他就只能去上班。
但是当魏婉娴告诉雯颖他们定好了上午十点钟的船票时,丁子恒还是松了一口气。
雯颖头天冒着风雪去头道街给静雅静宜静沁一人买了一件衣服,还买了几种点心让他们在船上吃。雯颖把这些东西交给魏婉娴时,魏婉娴哭了起来,雯颖亦泪水涟涟。她想起几个月前两人还倚着房门讲着关于石评梅的诗,而转眼间却要互道别离。世事的变幻,竟全然不给她们半点预示。雯颖本是不信菩萨的,这一忽儿,她突然想,那天魏婉娴斥责了菩萨几句,难道报应便应在今日?想罢她有些毛骨悚然。
魏婉娴哭完后,回到房间,拿出一本封面已泛黄的书,递给雯颖,说:“这是石评梅的诗集,我以前好喜欢的。送给你作个纪念。我们走时,你一定不要送我们,连送到走廊上都不必。这辈子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可是我心里会记得你们一家的。”
雯颖接过书,哽咽道:“我也会记得你们。”
三轮车抵达丁字楼门洞口时,雪下得很大。地面已经变白,北风卷着雪花呜呜地叫着。雯颖听见苏家人丁零哐啷抬物下楼的声音,脚步十分杂乱。她没有出去,一手抱着嘟嘟,一手搂着三毛,三个人站在窗口,隔着玻璃看着三辆三轮车载着他们一家人悄然而去。
三毛说:“苏妈妈他们还会回来吗?”
雯颖说:“不知道。”
三毛说,“是不是我跟静沁吵架,苏妈妈生气了?”
雯颖说:“不是的,不关三毛的事。”
三毛说:“那为什么要走呢?其实我还是很喜欢静雅姐姐和静宜姐姐的。就是静沁有点讨厌,可是她有时候对我也很好呀。我不想他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