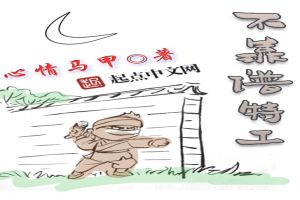乌泥湖年谱-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方方
楔子:关于乌泥湖的说明
一 乌泥湖的地理环境
在我的印象中,乌泥湖位于汉口的西北方向。
我为了证实自己的印象,便找出一本商务印书馆所出关于湖北的《地理词典》查看。这本书是我公公送给我的,他是该书的主编。但令我惊异的是,书上认为,乌泥湖在汉口的东北方向。我对此颇为不解,因为从地图上看,乌泥湖无论如何也是在西北部的。而且我小时候写作文时,一直说“我的家位于汉口西北大门的旁边”。
我想问挝我公公,只是这时的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他不会记得究竟是汉口东北部还是西北部有一个名叫乌泥湖的地方。于是我想,我的直觉毕竟不如编书的学者可靠,所以,便依了书中所说,让乌泥湖在汉口的东北方向。
乌泥湖应该算是汉口著名的后湖的一个部分。后湖并不是一个湖,而是一群湖泊的名字。其实往更远一点的年代说,汉口当年都是沼泽和水泊。乌泥湖想必就是这些水泊中的一个。
一个被我们称为郗婆婆的老人总是说,她的爷乙以前告诉她,这湖下面的泥乌黑乌黑的,像煤一样,所以就叫乌泥湖。但湖里的水却是极清亮的,里面的青鱼尤其肥硕。每年冬天,都有好多渔人前来捞青鱼,说是乌泥湖青鱼腌制以后,肉色嫩白,极是好吃。后来汉口慢慢成为了繁华都市,人也越来越多。人们与水争地,湖泊便渐渐地干了。乌泥湖在人水相争中落败下来,成为一片长满着青草的陆地。从此,乌泥湖便不再是湖,而只是一个地名。
郗婆婆家的房子几乎就是盖在以前乌泥湖的湖心。她家的后门有一个小小的水塘,塘里漂满着浮萍,四周则长满水草,有一两棵柳树垂在那里。不知那是不是乌泥湖最后的水面。
后湖在乌泥湖北面。乌泥湖退水为陆后,后湖依然荡着它的水波与人对抗。后湖的莲藕是汉口人最喜欢的一道菜。把它和猪骨头煮在一起,汤色清白,浓香扑鼻,莲藕入口即化。后湖便因了这些莲藕而形成一个个像样的村落。
我上中学的时候,曾经多次由学校组织去后湖公社挖鱼塘。顶着朔朔的北风,我们脱去棉衣,挽起裤腿,站在一片烂泥地的旷野中,等着男生们用锹挖出稀泥装满我们的簸箕,然后我们便挑着这稀泥一摇一晃地走到远远的一个废弃的坑边,将稀泥倒在里面。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守着这么大水面的后湖还要让我们学生来挖鱼塘呢?后来才知道,曾经如珍珠一样撒在后湖四周的湖泊都如同乌泥湖一样,被人逼退,变成了菜园。湖泊的锐减,使得好食湖鱼的武汉人的餐桌上,已难闻鱼香。
政府便决定挖掘人工鱼塘,以解决武汉人吃鱼的问题。事情总是这样奇怪、人好不容易把鱼赶走了,然后又花费更大的工夫再把它们请回来。
在后湖和乌泥湖之间,夹着新江岸火车站。据说芦汉铁路汉口段最早就是从这里动的工。铁路线纵横交错地爬出很大一块面积。夜晚的时候,我们能听得到那里的调度员用懒懒的声音在高音喇叭中调度车辆。火车的鸣叫声亦拖着长长的尾音,穿越过那里惟一的一条能通公共汽车的二七路,从乌泥湖的上空柔和地划过。
乌泥湖的西边是一个部队营房。营房的面积十分之大。隔着墙,我们总能看到那些绿衣的军人们来来往往。他们肤色红润,体魄健壮,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崇拜的偶像。上小学的时候,营地曾经派来些解放军做我们的辅导员,这使得我们常常有机会走进那座营地。现在这个营地成为了二炮的一个学院。
有一次我们在学校种植的水果有了收成,于是由少先队大队组织了几个中队长,从每一种水果中挑选出一个最好的来,装在果盘里,然后打着队旗送到解放军的营地。我是其中代表之一。那是我第一次参观解放军的宿舍。记得当我看到了他们叠得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的被子时,感到非常吃惊。回家后,我整整练了一个月,学会了如何把被子叠得漂亮。直到今天,只要我想,我的被子总能叠得美观如同艺术品。
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倚在营房的墙头上,看里面的人们操练。有一回,我的一个同学雪茹说,我们会不会亲眼看见那里面出现一个王杰?那是我们坐在营房的墙头上,唱着《王杰和雷锋一个样》这支歌时挑起来的话题。我们曾经围绕这个话题讨论过很久。然而,我们始终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场面。雪茹便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她非常有水平的话。她说:看来王杰太少了。
乌泥湖的南边以郗婆婆的房屋为界,便是郊区农村。在郗婆婆的小屋旁,除了那个小小的池塘外,同池塘相连的是一条长长的河沟,河沟上有一座小小的独木桥。
桥面上破了几个洞,没有栏杆,走过它时,常常令我感到害怕。水塘、河沟、稀疏的树木以及独木桥都同郗婆婆的屋子和谐地溶在一起,一眼望去,满是田园风光。
跨过小桥便进入农村,这就是蒲家桑园。从我家的窗口可以望得见这个村庄的屋顶和它不时升起的炊烟。我有许多的同学住在这个村子里,但我除了去过他们的村口,也就是刚刚跨过那座小木桥,就再也没有往纵深去过。
村子里有许多的狗和满地的鸡屎。在村里跑来跑去的小孩子也都一个个脏兮兮的,鼻孔下面多半都吊着些鼻涕。我得承认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我,因为家境较为优裕,往往会身不由己地摆出些小姐派头。我从来都没有到班上那些农村孩子家串过门,所以,至今我的脑子里没有一点蒲家桑园村里的印象。所知的星星点点只是:这一带曾经都是一个蒲姓地主家的土地。环绕他家地界的全是桑树。因此,当地人都管那里叫蒲家桑园。解放后,姓蒲的一家都逃走了,地也分给了穷人。蒲家桑园在我记事的时候,便被称做了蒲家桑园大队。
村里的人大多姓蒲。蒲家地主的侄儿还住在村里,他替他的堂兄戴上了大地主的帽子。而他实际上曾经是武汉大学的一个进步学生,毕业后一直在汉口教书。有一天他不知深浅地回家看望母亲,恰恰遇到村里的干部批斗地主,找不到他哥哥,便顺手抓住了他。说好批斗完还让他回汉口教书,但不知何故阴差阳错地竟没有让他走人,于是他便成了蒲家的地主分子。他每天拉长着脸跟着村里人下地干活,一天天地被沉重的农活和沉重的心思压驼了背。他的小儿子同我的小哥哥是同班同学。
大家提起他什么事,都不说他的名字蒲海清,而是说“驼背的儿子”。
蒲家桑园的农民都是菜农。他们的菜地呈半包围的形态环绕着我们居住的乌泥湖。我们如果要上街,就必须沿着他们的菜地行走很长的一段路。但蒲海清也就是驼背的儿子说,村子北边的菜地即包围着我们乌泥湖宿舍的那片地,只是他们村土地中很少的一点点,而村子南边有很大很大一片。在油菜开花的季节,刮风时站在田边,可以看到一层一层金黄色的浪从远处滚滚而来,那一刻你就忍不住想往后退,恐怕浪头会扑上脸来。他的这个形容给了我很为深刻的印象。每次我看到大片的油菜花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蒲海清站在我家走廊上,一边挖着鼻孔里的鼻屎一边同小哥哥说过的这番话。
与蒲家桑园紧靠的地方亦属于部队。这支部队并未见多少人马,从它的大门经过,可以远远望见里面有着一排排低矮的房屋。似乎从来也没有听说谁进到里面过,亦没有人去猜测它为什么存在。直到1967年的一天,突然涌出一些人到里面抢枪,于是人们才恍然,原来这个守得严严实实的地方是个军火库。那一天,我上初中的小哥哥正好路过那里,他跟着人跑进去捡了一把枪回来。他曾经把这支枪藏在我家厕所里很长的时间,但终于被我发现了。他为这支枪写过许多次交待材料。
乌泥湖的东边成分有些杂乱。除了我们的乌泥湖宿舍外,还有一大片敞开着的野地。地里开放着无数的野花,还长着许多马齿苋。有这个印象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我跟着我的二哥一起去找过这种野菜。现在回想起来,它并不好吃,但它的小叶子肥厚肥厚,有一种特别的好看。野地的边缘立着一座碉堡,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留下来的。碉堡旁有一个勘测队留下的矩形的水泥标识。那是我们常常玩耍的地方。
在野地上没有盖仓库的时候,站在勘测标识的水泥墩上,可以远远地望见更东边的地方立着另外一座碉堡。这座碉堡和一条稍宽一点的石子路连接在一起。我记得它最初的路名似乎就叫蒲家桑园路,后来被改为工农兵路,这个路名一直沿用至今。许多年后,我乘车经过工农兵路,发现这条我曾经了如指掌的路已经变得十分陌生,我甚至指认不出一个我所熟悉的地方。
与工农兵路旁边的碉堡面面相对的是一个大粪坑。我们出门往往走到大粪坑处便向右手拐弯,从这里一直可以走到黄埔路,然后便进入到繁华的城市中心。
乌泥湖大概就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往东更远一点,有着著名的二七纪念碑。从那里再向南一点,便是长江流域规划设计总院的机关所在。因为它的存在,才赋予乌泥湖这个平平淡档的地方丰富而厚重的经历,也才使得乌泥湖的命运嵌入了整个时代的命运之中。
二 乌泥湖的人间历史
乌泥湖化湖为田后,四周一直是零零星星的沼泽和野地,人烟稀少。清朝时,湖边修起了一座庙,庙里供着一个无精打采的菩萨。小时候我听说供的是关公,可也有人说不是关公,是观音娘娘。这两个人物形象相去甚远,究竟是谁,不得而知。
庙里原本有一个和尚,说是从黄梅东山五祖寺上下来的。和尚每天都敲敲钟磐,清早出来打扫一下院落。他平平静静的面孔和淡档泊泊的生活,引起附近一些人的兴趣,人们对他有了一些关注,于是香火就旺了起来。可是和尚还没有来得及等小庙香火旺出一点名气,就在一天突然失踪了。郗婆婆说,她爷爷讲那个庙的事情时,对那和尚只说过一句话:那是个真和尚呀。没有了和尚的小庙香火萦绕了一些日子,便又随风散去。那庙后来被人叫做“乌空庙”。不知道早先有和尚时,是不是也叫的这个名字。乌有和空无,意思重复,加重这种意思也不知有什么样的意味,只是对于一座清冷的寺庙来说,这么叫着也还恰如其分。
在有了乌空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乌泥湖有过什么样的更多的故事,我不太清楚。只知道这里属于汉口的东北大门,是一个兵家常争之地。这里曾经打过很多的仗,近代历史上颇为悲壮的阳夏保卫战便在乌泥湖摆开过战场。书上说,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军,一直打到了江北的乌泥湖,占领了乌空庙,将清军赶到了几乎出了汉口地盘的滠口地带,然后就守在了乌泥湖这个地方。冯国璋率领着北洋军打过来时,乌泥湖便成了炮火连天腥风血雨之地。成千的人望着这个名为“乌空”的破庙怅然而死,鲜血很轻易地染红了乌空庙周围的河沟。也许死去的人们在最后合上眼睛那一刹,会突然明白横在他眼前的“乌空”的含意。
乌泥湖四处曾经遍布着碉堡。直到1962年我上小学后,依然有三座碉堡散立在附近。除了我所提到过的两座外,另有一座立在我就学的小学校园里。小时候,虽然天天都见到碉堡,可因为到底是生活在平静和安宁之中,与欢笑和幸福相伴着,便从来就觉得战争距离我们很远很远。现在想起来,其实在那时,战争也就刚刚过去不几年。
1955年春天的一个日子,突然有几个不速之客来到了乌泥湖。他们默默地走在这一大片水泊和荒草交错铺展的野地里,不时地望望因土地空旷辽阔而显得低矮的天空。天空中有几片浮云,浮云缱绻着,令空荡档的天空生出一些妩媚。残破的乌空庙在这片天地中显得孤独而渺小。
一个小个子的中年人说:“就在这里吧。”
随行的一个青年人说:“这里简直像个风景区。”
小个子的中年人没有接他的话,只是放眼环视着在风中倒伏的荒草和荒草丛生的水塘边几株绿色葱宠的树。他忽然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随行的另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说:“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小个子中年人笑了:“这是我最喜欢的诗。他给人以时光流逝、空间辽阔和灵魂孤独的三种感受,就像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事。三峡是前无古人的,是后无来者的,是在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