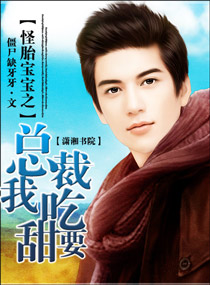怪胎-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蓝好蓝,使她无法面对。她变得像个易受伤的小女孩,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开始缭绕于心头。她翻了个身,强迫大脑变成一片空白。可是这只是一种奢望:愈试着使脑筋迷糊,它就变得愈清醒。她一直让自己保持同样的姿势,慢慢地,她觉得四肢沉重、意识模糊。在完全沉睡之前,她的下腹轻微地震动了一下——轻微处就像蝴蝶振翅一般,不过那是温馨而舒畅的感觉。
布强生在外面隔着玻璃观察她。姗曼莎和其他实验者不太一样。大部分医学院的学生都拥有冒犯性的口才,而她的口吻却是机智逗趣的。外观上,她是个相当迷人的女孩,可是在她泰然的态度之后似乎隐藏着一点点不安。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他抽出她的申请卡。姗曼莎。柯士汀,23岁,未婚,生物学博士班的研究生。她的自传写得很坦诚且不拘形式。他真正想了解的是她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脑波记录器上的钱条非常对称,起伏的节奏也很平稳。布强生喝完杯中最后一口咖啡,正打算再加一些的时候,突然注意到脑波起了略许的变化——在每一个波浪的末端都出现了一个小黑影。他不太敢确定自己是否真正看到了那些小黑影。于是他眯起眼睛仔细地打量了一会儿。这回,他什么也没看到。他猜想刚才只是电压不稳,因为波纹正常得很呢。
布强生看着姗曼莎。她一动也不动地躺着,眼皮也很平静地合着,完全没有转动的迹象。他看着姗曼莎,又看看脑波记录器。难道刚刚是幻觉?他用手背揉揉眼睛。
布强生又倒了一杯咖啡,现在荧幕上每一个波浪都很清晰稳定了。渐渐地,他的实验对象进入了“眼球迅速转动期”。
就在荧幕上的波纹换成做梦期的型式时,布强生发现黑点又出现了一会儿。这回他真的纳闷了,会不会是线路受到干扰或是受到描图机内静电的影响?不过这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事。
电话响了。那是电脑中心打过来的。
“博士,你那儿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怎样?”
“我们这儿发生了奇怪的现象。所有的电脑都错乱了。我好像向你解释过。每次你的实验对象一开始做梦时,‘老梅’就会发生错乱,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反正所有和‘老梅’相连的电脑里的程式全都跟着乱成一团,磁带机也停止转动。可是‘老梅’和你那儿的线路却继续畅通。当‘老梅’错乱的时候,我简直不知该如何形容它。我只能说它在自言自语,答非所问。”
“很抱歉让你那儿一片混乱,不过我又能怎样呢?”
“还有,我想顺便请教你一件事。‘老梅’经常打出几个莫名其妙的字……让我念给你听。‘飘浮、开始对话’……”派勒说,“这些字对你有特殊的意义吗?”
“没有,怎样?”
“我也不知道。就在我打电话给你五分钟之前,‘老梅’自动在报表上印出了这些字。”
五分钟……有样东西突然唤起了他的不安。他瞥了姗曼莎一眼,她正在打鼾。他又瞥了荧幕一眼,脑波已回复正常的睡眠形态……然而,五分钟前,一个奇怪的黑点曾经出现在这张荧幕上。
布强生挂上电话后一直隔着玻璃注意他的实验对象。小黑点,电脑中心打来的电话……这两件事有关系吗?他决定和姗曼莎谈一谈。
第七章
“要不要加糖或牛奶?”他边问边把手伸向柜台上的小方盒。
“不用,谢谢。”姗曼莎说着,轻轻地摸摸他的手背。
布强生看看她的手。通常,他不太喜欢这种肌肤的接触,可是现在他觉得有些……不同。
姗曼莎喝了第一杯,紧接着又叫了一杯。
“你喝那玩意儿和巴西人一样凶。”
“这是我唯一的嗜好。”姗曼莎说,“我崇拜咖啡,我好像给咖啡因迷住了。你想这样对我不会有不良影响吧?”
“不良影响?你是指……”
她赶紧把眼撇开。
“我是说对身体。你没读过这方面的报导?”
“当然,咖啡因的确对身体不太好。”
“可是,你认为它会破坏我的染色体吗?”
()
“这一点我就不清楚了。你问这个干嘛?”
“只是好奇。”
又来了,他想,她老是使他觉得困惑。他是为了前一天实验室里的事才约她出来喝咖啡的。他对自己突然说出邀请她的话感到很吃惊,就连卢里太太也对这件事扬起眉头,嘴角列出神秘的微笑,一般说来,布强士是绝不和他的实验对象有任何私交的。可是姗曼莎给他的感觉大不相同,她是个成熟的女孩,她有种不可解释的魔力……
真想不透,他想,我就是不知不觉地对她愈来愈有兴趣。为了他的事业,他规定自己不能和任何一位女孩发生感情,此外,他的创伤还未全愈。他发现研究工作是使他心境平和最好的药剂。现在,他的工作已经完全占据他的心灵。
然而,他毕竟不是和尚。偶尔他也会和女人约会。女人到底可以满足他的肉体需求。裘伯利医学中心有上千个单身女人,他可以和她们某一位保持着肉体关系,而一旦涉有感情成份时,他就会与她分开。可是现在……
他的眼神凝视着虚无的一点。她的眉头也疑惑地扬了起来。
“你在想干么吗,布博士?”
“抱歉,你说什么?”
“我说,还要多久才正式服用安眠药?”
“我们要先记录你正常的脑波描图,可能再过三、四次就开始了。”
她又皱眉头了——难道她有什么心事吗?
“对,我想到下礼拜三或四,你就得开始吃药了,怎样,你急着一试吗?”
“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她又把手放在他的手背上。“下礼拜你都会在实验室吧?”
“这个周末我要出城参加一个会议,可能要好几天才回来。不过不要担心,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卢里太太。”
他看看表。“看来我耽误了你不少时间。柯士汀小姐,谢谢你今天的合作。”
“叫我姗,好吗?”她喝完咖啡,从椅子上站起来。“祝你有个愉快的会议周末。”
下礼拜二布强生开完会回来的时候,直接赶到实验室而没有先回家。他要在姗曼莎醒来之前赶到,前两天开会的时候,他总是想到她。他的情绪似乎又开始为谁牵缠了。
他的时间算得恰恰好。当卢里太太站起来迎接他的时候,姗曼莎的实验正步入尾声。
“进行得怎样?”他问卢里太太。
“非常顺利。我必须承认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位小姐,她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不,不……”
他们一起看往玻璃的另一面。姗曼莎已进入最后一次的眼球转动期。布强生把眼光转回脑波记录器荧幕上。起初,一切都很正常,可是在更换睡眠型态之际,波纹之间又出现小黑点。
“罗丝,”他指着荧幕上的波纹进入完全清醒的状态,同时,实验室中的姗曼莎睁开了眼睛。卢里太太赶紧走过去帮助她起床。
姗曼莎在洗手间换衣服,卢里太太在整理床铺;布强生则坐着思索刚才那一幕。
那些该死的小黑点到底是什么鬼玩意儿?这位学者试着想告诉自己一个答案,可是一无所获。
他不太敢肯定自己的情感,不过自从上次一起喝咖啡之后,他肯定自己开始对姗曼莎产生兴趣。他已经不知不觉打破了陈规。
姗曼莎打着呵欠从洗手间出来。
“你好,布博士,会议开得怎么样?”
“还不错,姗。对了,以后不要这样称呼我。就叫我强生好了。”
“好吧。你好,强生!”他们对看了片刻,姗曼莎才叹了口气,开始翻弄桌上的文件。
“你在找什么吗?”
“我记得卢里太太今早在桌上留了一块巧克力的。”
他笑着说,“罗丝很贪吃。姗,我打赌那块巧克力早已在她肚子里了。这样好了,你能不能撑空肚子再忍一、两个钟头?”
“我很怀疑能不能撑得住。”
“如果我答应请你吃一顿大餐呢?”
“你是要请我吃晚餐,布博士?”
“强生,又忘了?不错,是吃晚餐,不过不是馆子。我们到我住的地方,我下厨房。”
“七点。”
“我一向很准时。”说无,她还向他挤挤眼睛才离去。
第八章
砧板边上堆了一团剁碎的绿叶菜。苦艾酒瓶旁散满了空蛋壳。
“你在哪儿学的这一套?”她问。
“你是说学做蛋黄酱?”
“不。我指的是用一只手打蛋。”
“这是我生存的本领,”布强生说,“做个光棍不是那么容易。在纽约的曼哈顿区上馆子虽然享了口福却苦了腰包。我喜欢吃讲究的食物,所以必须从最基本的学起。”
“可是蛋黄酱可不只是基本的东西啊,”
“是啊,这道菜得准备好几个钟头呢。”
桌上有酒、面包、牛排、沙拉、蛋黄酱——这算得上是丰盛的一顿。只是,她并不十分了解他邀她来这儿的用意。
“你会不会奇怪今晚我为什么邀你来吃晚饭?”
“会。不过我不打算问你,我愿意保持着这份神秘。”
“其实也没什么好神秘的。很简单,我只是发觉你的脑波图有点不大正常。”
她的眼睛幽默地瞪得大大的。“老天,我会死吗?”他笑了。“你可以活到一百岁。不过你的脑波类型是我从未见过的。我并不认为这代表任何病症。用口头很难说出它有何异常之处,这样好了,我画给你看。”
布强生在纸巾的背面画出了睡眠中脑波的各种型态,然后在旁边画出了他所记得的姗曼莎的脑波图。
“这就是你的脑波图,”布强生说,“这些则是各种不同状态的睡眠脑波图,”他指指小黑点的位置,“你看出有何不同吗?”
“我想,我看不出什么名堂,除了……我的波纹后面好像还拖了一个小小的尾巴。”
“好极了,你观察力很强。”
“这条尾巴代表什么?”
他耸耸肩。“但愿我知道。此外,这体贴小尾巴都出现在你沉睡的时候,或许,你在沉睡时也在做梦。不过这是不太可能的事。”他接着说,“过去,我们在神经病患者的身上发现过这种例子;常患头痛的人也会如此。可是,你的申请卡上写明了一切正常的啊。”
“我一直健康得像头牛。”说完,她还吃了一大口面包来证明。
()
他笑着靠回椅背上。“知道我对你的哪一点感到惊讶吗?”
“猜得出来,不过你还是说说看。”
“通常我告诉病人他的脑波不正常,他一定会吓得半死,而你却满不在乎的样子。”
他在洗碗,她在旁边帮他把碟子擦干。夜色已降临,气温也随着降了几度。布强生关上阳台的拉门,请姗曼莎到客厅坐着。墙角有个石块砌的壁炉,他捡了两根柴到炉架上。
“最后三块柴。”他说。
“我喜欢火。我们家每个房间都有壁炉。我常躺在炉火边看午夜的电视节目,即使在八月也不嫌热。”
“你住哪?”
“长岛。上面有个你绝对没听过的地方叫罗瑞哈路。”
“也许,我还经常开车经过你家呢。”
她笑笑。“我也许还向你的车挥地手呢,不过,我认不出你开的是哪辆。我很高兴能离开家。”“跟人闹意见?”
“我很烦他们。”她把脚收到沙发上。
“一个典型富有而不快乐的女孩。”
“可以这么说。我爸爸从来没有在家过。他成天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妈妈和蔼,可是她太拘谨有礼。她是世界上最正派的人,永远只会微笑或是说:”当然,亲爱的。‘“
他大声笑了起来。“我猜不管你说什么她都会答应。”
“不要弄错我的意思了,她是个好母亲。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对不起她,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好了:我有个十八岁的弟弟,家里只有我们两个孩子。我爸爸给他买了一辆黄|色的法国小跑车做生日礼物。那小子真是给宠坏了,那辆车没开上一个星期就进了废铁厂,因为他酒后驾车出了车祸。自是出了奇迹。他连一点伤都没受。上次我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才知道爸爸又给他买了一辆完全一样的,只是这回是蓝色的。”
“所以你决定离开这个家。”
“并没有立刻离开。我住校期间,他们规定我每个假日都要回家一趟,好像我注定是个永远离不开家的孩子。我觉得我像是修道院里的修女。”
“你什么时候切断这条线的?”
“进大学不久。我爱上了生物学,所以决定主修这门学问。我寄了一打以上的申请信,想转到生物学校有名的学校。大二那年。我转到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