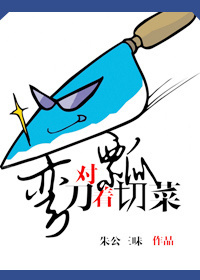吉诺弯刀-第38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六,韦格说,东西方宗教中有关地狱的说法,也许并非是偶然的。要知道,那时候东西方的人类之间,远隔高山海洋,是彼此无法联络沟通,互相影响的。为何都提出地狱的说法?
他认为地狱的说法,最早都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文明。在苏美尔人的文化当中,当时认为人死后将会去往一片“不能回归的国度”。那片冥土就是所有地狱的雏形。
第七,韦格主张在幼儿园开设冥想这类的课程。
他说,我们在教会后代向外探求世界的同时,也应该教会他们如何走进自己的内心。
韦格说,事实上,在很多信仰宗教并信赖冥想功效的国家,人们在家庭和宗教生活当中就是这样教育儿童的。而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幼儿园也已经有教师在这么做。他甚至介绍我参加过一堂儿童冥想课。一位女老师带着四个幼童,在幼儿园的地垫上学习如何闭目安心,屏蔽世界的干扰,观察内在的身心。
(二)
韦格也特别喜欢中国古典音乐。
他最喜欢一首中国的民歌,他说不知道作者是谁,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传唱的,名字也说不准究竟是什么,只知道开头的第一句是这样的:“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他说,后来,有个很有名的中国导演,找了一些很有名的中国演员,拍了一部画面、服装、音乐都很美艳的电影(注:王家卫《花样年华》),旧上海竖领女装旗袍式的,那种陈旧的美艳,里面用了这首歌的意境,还有这首歌的曲调,以及,这首歌的歌词提炼成的标题。
韦格对我说:“这歌里面,有一句话曾经很打动我的,倒和茉莉花没有什么关系。就这句:我望着窗外的街角,看着辛酸走来,幸福走掉。”
他触动了我的心弦。事实上,多年来,这首歌里面,我也很喜欢这一句就只喜欢这一句。
(三)
韦格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便是世界各地的邪教。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冒着生命危险,贴近而深入观察着一个知名的邪教组织。
他观察研究这个群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事情的最后结果是,警方和该群体之间发生了双方皆动用了高级别暴力的冲突,一些人被营救出来,一些人被关押起来,一些人被击毙,一些人死掉了。还有一些人,失踪了,一些人,被驱散了。
在韦格的电脑里,看到一小段他貌似偷拍的邪教传教视频。
一个很年轻,长得也很端正的男子,西装革履地面对镜头,讲述着他的教义。
他的眼神很少直视镜头,总是在镜头前飘来飘去,一会儿看向这里,一会儿看向那里,
他重复自己不久前刚刚说过的话,他换用不同的句子说同一个意思,他常常对别人使用反问的句子,他的双手常常紧握在一起,手指在扭动。
从韦格用手机拍回来的照片里面,可以看到小镇的夜空泛着火光燃烧的红色。许多杂沓的黑色身影穿梭在镜头前。一些手臂伸向天空。
(四)
韦格总结说,
此类不幸的邪教事件,有一些共同的迹象:
对自我利益(现实利益,永恒利益)的执著;
对身体或者灵魂常存不坏的执著;
对不同意见者的排斥;
不惜伤毁他人或者强迫他人来增益自我;
对他人普遍认同和赞扬的急迫需求;
扩张的**;拥有的**;人多势众的**;
对力感的渴求(极度缺乏力感,常常演变为对权威的狂热拥戴、对暴力的主动寻求);
对某种未知(比如末日,或者神罚)的强烈恐惧;
很强的团队依赖性及很强的团队攻击力;
有明确的敌人,和明确的对敌人的仇恨;
绝望感与逃避感;
越来越狭窄而艰难的道路;
非常有限的视野和考虑范围(通常伴随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种族中心主义或者团体中心主义);
被迫害的巨大委屈感,对不公平的激烈抗争;
在普遍的牺牲当中,教主不会代一切信徒而牺牲自己的一切,更不会为一切攻击本教的人的幸福快乐而牺牲自己的一切,自然,也就不会为一切生命的福祉,而牺牲自己的一切。
常常,相反的,有种隐蔽而炽盛的**:欲令一切生命为了证明“我的(或者我们的)正确”而去牺牲一切。
凡此种种,均是邪教的特征。
(五)
和韦格谈话。在说到宗教战争史的时候,我们曾经谈论过信仰忠诚的问题。
韦格说,要知道一个信徒是否真正相信他的神,很简单固定他的手脚,然后点燃他的衣服也就可以了。看他的表现,就立时可知他是否真正信仰他的神和他的神所说的东西。
往往不是平时那个最肯为神玩命的人就是最坚定的信徒。
总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不是为神玩命,是为冒用神的名义的“我”玩命。信仰神倒变成一个“自我神圣化”的过程了。
韦格说,宗教纷争的原因大概都在这里了。哪里在保卫神呢,在保卫自己吧。
很多“圣战”的性质其实都是这样的吧:用神圣的名义,为自我而战。
“圣战”的存在本身就是神的悲哀,说明他的信徒内心并不相信他的全知全能。
韦格说,往往那个临危表现最和平最安静的人,才最具有真正的信仰。
(五)
韦格的夫人是烘焙高手。她特别擅长做一种芬兰黑麦烤的松饼,烤得很脆,很香,但味道很淡,颜色也不好看,里面没有添加什么人工辅助剂,也没有糖,只有一点盐,质朴无华的作品,配牛奶喝,牛奶的味道渗透每一层蓬松的孔洞。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喝牛奶吃松饼的时候,韦格对我说:真正的伟大,在人类生活中,是很少会被尊重的。
他说:“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吧。大的东西能否放进小的东西里面?”
他说:“如果我是小学生,如果我回答:能,那么,我的作业本上一定会给老师打一个叉。因为不符合常识。”
他说:“但真正的常识却未必是课本所认可的那样。比如我们的肺部。所有肺泡中可以用来呼吸的细胞面积加起来,展开可达30平方公里,是我们身体展开面积的数十倍。一昼夜之间,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相配合,总共可以净化血液1万5000斤以上,远远超过我们的重量。可以计算一下,如果一个人活70岁,他的血液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将为他做多少工作。那是一个天文级别的数字。但如此神通,我们从来不叫它是神通。我们也不尊重它。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在这样运行着。我们,也不爱它,从不因此而感到幸福与满足。事情就是这样的。”
他说:“大众是肤浅的。他们只相信眼睛所能看见的东西,但是,他们虽然圆睁双眼,但却对很多事实,一直视而不见。”
(六)
我很喜欢和韦格见面,也很喜欢和他谈话。
其实我并不太喜欢喝加了奶的红茶,但与韦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喜欢。
良好的谈话就具有这样的力量。它可以改变生活的味道。
第八百零六章 傅牧师
(一)
在韦格先生的介绍下,我认识了德国科隆的一位新教华裔牧师:傅国华牧师。
傅国华老师在出任牧师之前,曾经是学中国古代文学出身的,对中国禅宗及与之相关的艺术,颇有研究,文学修养也很有境界。
我们相识后,真是一见如故,有许多的共同话题。
傅国华老师很喜欢咏诵诗歌。他经常在布道时念诗。他念诗的时候,眼神熠熠有光,声情并茂,抑扬顿挫间,有着特别的感染力。他的布道演讲,特别吸引当地的华人。
据说,他来德国前,曾在上海一所高校执教文学课,经常在课堂上满怀深情地朗诵戴望舒的《雨巷》,倾倒了广大文艺女青年。
他对丁香花格外情有独钟。
傅牧师出国已经很久了,他现在已经是别国的国籍。他一直是坚定的新教信徒,这一点是继承了他的家族传统。他一直都说:“我是有信仰的人。”他一直自豪于这一点。尽管这一点没给他的青年时代带来任何好运。尽管这一点最后导致了他的出离。
我曾专程去听过傅牧师的布道。他在布道时提到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对他的一生和艺术作品,发表了长篇的评述。
当他在讲坛上说到卡夫卡临终要求亲友销毁他的作品时,他看到坐在第一排的我,眼泪忍不住流出来了。
就是这次流泪,让傅牧师对于我,也有了格外的注意。
傅牧师后来说:“虽然当时教堂里坐了70多位华人信徒,他们都听得入神地看着我。但只有你,是明白这个行为里面的悲怆的。”他说:“你之所以明白里面的悲怆,是因为你有着同样的感受。”我对傅牧师说:“卡夫卡这个人为什么需要写作呢?因为他需要倾诉。他为什么需要倾诉呢?因为他心中装满痛苦。他的灵魂需要一个出口。他并不指望获得理解,一切对他来说都并不值得在乎。他只是要不停地写下去,就像掉在水里的人需要不停地手脚划动才能靠近岸边。写作于他就是生命的形态。是日记、是治疗、是祈祷、是泻洪。他只需要延续,并不需要观众。”傅牧师对我的这段话,印象极为深刻,大加赞赏。
之后,他送给我一本书。他说:“作为中国人,你可能不太愿意新奉新教。但是,也许,你可以在别处找到平息内心抑郁的东西。”他送给我一本厚厚的词典一般的书《中国禅宗与东方艺术》,然后又指引我去拜读铃木大拙写禅宗与艺术的各种书籍。
傅牧师,应该是我修学禅宗的启蒙老师。
永明延寿禅师的《宗镜录》(文字极其优美的佛学概论)和《万善同归集》,也都是傅牧师推荐给我的。
(二)
到杂志社工作后,有个机会去参加慕尼黑的啤酒节。
在匆匆日程当中,我给傅牧师打了电话,正好他也在慕尼黑公干。
我们挤出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在一个装满极其笨重的老旧家具的小饭店里,他请我品尝了著名的德国咸猪肘。
第二天,我们又见了一次面。这次我请他到一家中国新移民刚开张的川菜馆吃中国饭菜。这家川菜馆开张的时间不长,但在华人中却已经非常有名,因其川菜风味还非常正宗,没有被德国口味同化的缘故。
傅牧师娶了一个罗马尼亚的太太。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地道的中国饭菜了。
他被花椒辣得满头大汗,但他开心地说:“痛快,痛快!”久别重逢的时刻总是很让人感触。我们在饭桌上谈起各种事情。
我对他担任神职这件事情,多少有点好奇。我问他平时牧师都做些什么工作。
他一一给我解释如何为教区信徒的心灵服务。
他说这些的时候,脸上光采焕发。这让我明白为自己心中的信仰而工作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谈到了临终关怀的事情。傅牧师给我讲了很多他经历的死亡。很多痛苦的、不舍的死亡,很多不得已的撒手,很多未完成的心愿,很多不平静的心情,很多徒劳无用的挣扎。
再后来,我们接着找了另一个地方喝咖啡。
在喝咖啡的时候,我问傅牧师:“那么,您目睹了这么多的死亡之后,觉得什么样的死亡才是最受神恩的死亡呢?”
傅牧师说:“是那些平静的死亡。”
傅牧师说:“人在死亡降临的时候,是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的。有些平时表现温文尔雅的人会恐惧得歇斯底里,而一些平时性情暴躁的人则可能安详镇定。”
我说:“怎么样才能实现一个平静的死亡呢?”
傅牧师说:“平静的程度取决于**的炽热程度。”
他说:“我感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未竟心愿越多,没有完成的工作越多,没有实现的**越多,他临死的时候就越是不能平静。”
他说:“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活着的时候抓紧时间去完成你此生最想完成的工作。”同时也不要执着于大量的工作。”
他说:“一定要在人生各种纷纭的事务当中懂得有所取舍。不要期望齐头并进很多的工作。这样你很可能一件事情也没有办法做完。”
他说:“如果能把未完成的工作压缩到最少,则可以走得非常平静。越是平静,就越能看到神的光芒,就越是没有恐惧,就越是充满落叶归根的满足与安详。”
从咖啡馆出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