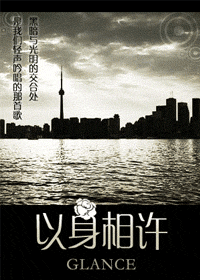以身殉攻-第8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邱锐之皱着眉头抓着他两只手腕扣到一起,制住他不断地挣动,同时朝外面喊了一声。
“阁主,什么事?”寒露的声音在外应道。“夫人这是怎么了?”
“不知道。”邱锐之面色古怪,他觉得易邪好似烧糊涂了,但到这地步也实在太离谱了些,他对寒露道:“你去把荣怀雪叫过来。”
“荣师姐?她也在吗?”易邪停止了鬼叫,突然问道。
“当然,我们是去寻镜桑花,这一路都在一起,邪儿忘了吗?”邱锐之耳朵暂时消停了一会儿,他立刻柔声劝慰易邪道。
“那涵枫也在吗?”易邪如同魔怔一般,问道。
“自然也在。”邱锐之说着就去探他额头的温度。
易邪两只手都被邱锐之按住了不能用,于是他就在邱锐之手伸过来的时候,吭哧一口就要咬上去。
邱锐之要是能被他这一口咬实在了,也就别在江湖上混了,他及时抽回手,终于有点不悦道:“邪儿干什么?”
“别碰我。”易邪气哼哼地道,还白了他一眼:“哼,都是幻觉,吓不倒我的!”
邱锐之:“”
这时候马车帘子被掀开,荣怀雪快速上了马车,然后落下帘子,她坐在对面望着被邱锐之裹成蝉蛹的易邪,问道:“易师弟怎么了?”
“他好像烧糊涂了。”
邱锐之话音刚落,就听易邪再次挣扎起来,叫道:“啊啊啊啊你们都是幻觉,我要出去啊啊啊啊”
荣怀雪也没见过这阵势,顿时也懵了,愣了半晌才道:“呃要不然,我给易师弟把把脉再说吧。”
“好。”邱锐之如此答应着,就想将易邪的手腕翻转过来,但他手上力道稍微一松,易邪立刻就开始拼命挣动起来。
邱锐之因为怕用力过大了而伤到他,竟也被他挣出一只手来,顿时一爪子就呼到了脸上,脸颊传来阵阵锐痛。
荣怀雪就这么眼睁睁地瞧着邱锐之脸侧多出了三道爪印,想笑但又觉得不适时宜,表情霎时十分奇怪。
邱锐之也一下子就沉下脸,他的耐心告罄,捏住易邪的下巴,嗓音压得十分低沉道:“邪儿,听话,好不好?”
易邪低头看了看指甲里的肉丝,已经开始怂了,被邱锐之一恐吓更是老实下来,弱弱道:“好好吧。”
邱锐之这才转过头示意荣怀雪诊脉。
荣怀雪脸上带着淡淡地笑意,在邱锐之看来分外刺眼,但也未说什么,他撸起易邪的袖子,把易邪的手腕递了过去。
易邪就像是被家长带着去打针的小孩子一样瑟瑟发抖,他生怕这些“幻境”中的人对他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来。
“怎么样?”荣怀雪探完脉后收回手,邱锐之立刻追问道。
“没有大碍,烧已经退了,顶多是有些体虚。”荣怀雪也有些不解道:“易师弟除了说胡话,没有其他症状了吗?”
“他刚才说咱们进了奔雷峡谷,遇到袭击失散一类的怪话。”邱锐之一边替易邪放下衣袖,一边蹙眉道。
“也许是易师弟夜里发热的时候梦到了些什么。”荣怀雪道:“其实易师弟年岁还小,梦里被吓到了,而分不清幻觉和真实也是常有的事。”
“我没说胡话。”易邪委委屈屈地道,他竟然被幻觉里的人质疑是产生了幻觉,不能再悲愤了:“我们接下来不是就要去奔雷峡谷吗?在那里我们中途遇到了一伙黑衣人截杀,我在马车里,你们在马车外,马车受惊了,我就和你们失散了。”
“只有寒露跟着我,他带着我跳车以后,我们为了躲雨就进了一处山里的夹缝,那下面是一座死城,进去之后寒露就不见了,四周都是一片大雾,我还在那里碰到了变成之之模样的怪鸟,它要把我抓走之后”
荣怀雪和邱锐之对视了一眼。
“咳咳。”荣怀雪轻掩嘴角,道:“易师弟想来是梦里受惊了,应该多歇息一下就会好了,邱师弟你就多安慰他一番吧,我和涵枫去买点吃食。”
“这镇上有人?”邱锐之问道。
“自然是有的,只不过很少罢了。”荣怀雪说道,这地方的荒凉远超她的想象,她开始有些担心她们带的那些补给够不够用了,而易邪眼下的情况还甚是不妙荣怀雪微微摇摇头,她低头跟邱锐之告辞后,便下了车。
易邪泄了气,他郁郁寡欢地耷拉着脑袋,如果这一切都是幻觉,那他说这些又什么用呢?
“邪儿想吃些什么吗?”邱锐之自然感觉到了他的消沉,纵使刚被易邪几番打脸,此刻依然耐着性子道:“夫君帮你买回来。”
易邪抬起头,眼神木然,这句话,也与之前的场景一模一样。
作者有话要说:那一天,易邪终于回想起来,曾经一度被邱锐之支配的恐怖,还有面对强权各种委曲求全的那种耻辱。
第111章()
易邪看了他一眼,垂下头怏怏道:“不用了;我没有胃口。”
易邪这副模样落到邱锐之眼里;便是懒得应付他了。
“邪儿在跟夫君闹什么脾气?”
邱锐之扣住他的后脑,让两人额头相抵;道:“邪儿自受了风寒,这半月来都昏昏沉沉,许久未曾跟夫君好好说过一句话;现下难得清醒,却还要跟我使性子?”
易邪心说哪有那么夸张,他在病中的那些日子只不过是一天之中睡得时辰多了些;从没像邱锐之说得那样;两人连句话都说不上。
尽管如此;易邪看了眼邱锐之脸上那三道血印子,还是底气略有不足道:“我哪有跟你使性子?”
“邪儿今天顶撞了夫君好多回。”邱锐之轻轻咬住他的耳廓,道:“记得当初邪儿刚嫁过来那会儿可是很听夫君话的;看来如今是被夫君宠坏了。”
他这话说得不轻不重,听起来也像是打情骂俏般地抱怨;甚至语调都没有任何起伏;但还是让易邪一下子汗毛倒竖。
邱锐之他不同于常人的危险之处就在于——他蛰伏在平淡表情下的险恶用心。
常常在你还无所感觉的时候;或许他就已经对你动了杀心,而你却一无所知。
但易邪却清楚地明白邱锐之每一分的情绪变化,他知道邱锐之现在很不爽,甚至知道他为什么不爽:邱锐之并不是那种默默牺牲奉献的人,他付出了就一定要得到回报;他为自己担惊受怕这么长时间,期间一直任劳任怨、衣不解带地照顾人,可不是为了让自己好起来后跟他横眉冷目的。
尽管还未搞清眼前这一切的真假,易邪还是顺势服软道:“我以为你是幻觉才那样的”
邱锐之向来对易邪的顺从受用得很,他也不再纠结方才的那点不快,表情放松下来,惫懒地在易邪颈边缱绻着,像是稍提起丁点兴趣般道:“那跟夫君好好讲讲,在你那个荒诞的梦境中,夫君是个怎样的角色,恩?”
纵使邱锐之那副如同‘唱个小曲听听’的轻薄嘴脸,让易邪手痒地想给他两下子,但却不得不说,这正合易邪的意。
这件事纵使邱锐之不提,他也是想讲的,可他张了张嘴,却发现对于邱锐之的问题,他其实没什么话可说,因为邱锐之实际在他们遇到截杀那块就已经退场了,后面都是形似他地纷纷杂杂的幻象或伪装。
“我们遇到袭击那里就失散了,你还哪来的戏份啊”易邪惆怅着道。
“不可能。”邱锐之用慵懒却肯定的语气道:“夫君绝不会弄丢了邪儿。”
“邪儿这梦听起来像是三流话本里的故事。”邱锐之轻轻嗤笑一声:“也只有在那庸俗的说书人嘴里,为了让他那无趣的情节更波折些,我才会把你丢了。”
“可我们就是分开了。”易邪毫不留情地打击了邱锐之的谜之自信,很不给面子地道:“马车受惊冲了出去,而你那会儿对付那些黑衣人都分身乏术,哪有空来追我。”
遇袭那会儿易邪正在马车中睡着,对外面发生的混乱并无感觉,他并不知道在自己所在的马车受惊跑远后,邱锐之作何反应,关于当时的情况都是听寒露后来给他复述的。
“分身乏术?”邱锐之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笑地轻蔑道:“邪儿的梦把夫君想的太不堪了,只是一伙乌合之众就能让我分身乏术的话,我怕是在当年回寒江阁的途中就不知死了多少回了。”
易邪突然心念一动,他想起在死城中看到的那些邱锐之的过往,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就证明了这一切并不是他的臆想,而是确实发生过的。
“之之!”易邪问道:“你当年回寒江阁的路上是不是曾经途经咸城?”
“咸城?”邱锐之轻蹙起眉头,脸上明摆写着‘这是个什么鬼地方’,但口中还是道:“记不清了”
“你当时难道不是跟虞骨结伴一起走的?”易邪急切道:“你们那时候在酒楼吃饭,还招惹了一个临河帮的姓曹的男子?”
“临河帮?姓曹的?”邱锐之表情有些阴鹜,他对这两个词的唯一印象就是肖寻所说——江云赋惹上的那桩命案,死的人就是临河帮的副帮主曹翼。
他记得他从未跟易邪提起过这个,而易邪从燕白那里得知的大概只有燕白的表弟被冤杀人一说,甚至连江云赋的名字都不曾提到过。尽管以江家的名头,就算易邪不怎么关心江湖事,也会知道些人物,况且以牵机派和云逍派同为四大派的和睦关系,难保易邪从小耳渲目染中得知江云赋的姓名,毕竟易邪在一开始就认出他和邱世炎了不是吗?
但至于其他的,比如关于江云赋所杀的究竟是何人,这种稍一打听就能知道的江湖传闻但以邱锐之对易邪的了解,他八成是不会主动关心的,所以难道他的邪儿,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刻意去留心了这个江云赋吗?
“我倒不记得有这种事。”邱锐之离开了易邪的颈侧,他坐直了身子,周身气质渐渐沉着下来,他眼中暗燃着看不见的火焰,语气平淡道:“但是,我却是在肖寻那里听说过——”
“江云赋。”邱锐之说起这个名字的时候,眉宇间才微露出些不易察觉的戾气,道:“传言中他杀的那人便是这个临河帮的曹翼。”
易邪引火烧身还尚不自觉,他骤然听到江云赋的名字还愣了一下,不知道何许人也,半天后才反应过来是死城中那个与邱锐之十分相像的小子,他顿时犹如醍醐灌顶:没错!江云赋!他竟然把这个人给忘了,在死城的经历绝对不是梦,毕竟梦境中出现些熟人或奇异之物并不奇怪,但是总不会出现他从未见过的人!
可是这样一来,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起来,易邪能清楚地感觉到,跟之前怪鸟的伪装和回忆中的幻影不同,眼前这个便是实实在在的邱锐之,所以他现在所处的境地到底是真是幻?
易邪思索之时,就听邱锐之问道:“所以,邪儿是如何得知曹翼这个人的?这等籍籍无名之辈,想来不值得邪儿特意去记住他的姓名吧?”
“啊?”易邪一愣,他莫名其妙道:“我哪知道这个曹什么就是赖到江云赋身上的那条人命我是因为你在酒楼跟他有过冲突,才记住的。”
邱锐之却对易邪说的有头有眼的事半分印象都无,他疑惑道:“什么酒楼?”
“”易邪无语,他搞不懂邱锐之究竟是记不住这种他口中的‘小人物’,还是他看到的回忆根本就是假的。
“教你武功的师父是不是名叫刑彻?”易邪试探着问道。
邱锐之一直沉静的表情终于出现了裂痕,他没有立即问易邪如何知道的这个人,而是冷冷道:“他这种人的名字实在配不上从邪儿口中说出。”
“至于师父”邱锐之嘲讽道:“不过是个被正道打压,而窝在南疆十数年不敢露头的败寇而已,仅教了我三年,便败于我手,称不上什么师父,踏脚石倒是听着更为合适。”
靠,当初是你叫人家师父叫得勤快啊,现在翻脸不认人了?而且什么叫败于你手,人明明就是被你杀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没有你这么化的吧?
邱锐之眼中的些许回忆之色褪去,他直视着易邪,突然从怀中取出一打银票塞到易邪手上。
易邪一脸懵逼:???
突然给我钱是几个意思?
“嘘!”邱锐之眼含戏谑地对易邪神神秘秘道:“这也算是夫君的“小秘密”之一,一旦传出去,比之邱世炎的死因公布于众的效果也差不到哪里去,所以邪儿要乖乖地守好秘密,否则你一直包庇的恶人夫君就要功亏一篑,受千夫所指了”
所以这这难道是封口费?况且我什么时候包庇你了?一开始就是你胁迫我的好不好?难道是因为我不能再嫁给你第二遍,你才要给我钱的吗?
易邪仍

![[宝莲灯]以身相许封面](http://www.kptxt.com/cover/69/6964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