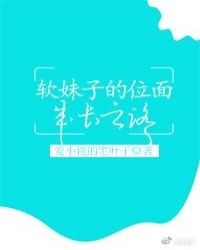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并没有感到学习压力大,但我感到:我不想做那长不大的孩子,不想一到外婆家就给我糖吃。
我,想有点自由,只要一点儿。我想用一点儿自由看书、看电视、玩电脑、画画、去公园玩……不想作业一做完,只能看半小时电视、只能读英语、只能做数学练习题。我只想能看我喜欢的动画片,不用等到每晚六点,只想在童话里遨游,只想玩够电脑游戏,只想做我喜欢的事。
我,不是机器人,一切按你们设计的“程序”做。我,想双休日没事就出去玩,不想在家里读我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英语,我只想在家里看那“囫囵吞枣”的图书。
我,要出去玩,哪怕我胆子太大闯了祸,也由我承担。
我,要大声叫喊:“让你们解放我的眼睛,解放我的嘴巴,解放我的双手,解放我的双脚,解放我的空间,解放……”
我,面对大山喊:“哎——真苦!”只听:“哎——真苦!哎——真苦!……”
与一个美国父亲的对话
与一个美国父亲的对话
我每天和女儿在一起呆5个小时,早上一个小时,晚上4个小时。
——凯文·斯考费尔德
凯文·斯考费尔德在微软公司主管三个部门,他在大学期间学习的专业是计算机和教育,与此同时,对专业之外的很多问题也抱有强烈兴趣。然而凯文给予我们的最强烈的感觉,
是他作为父亲的形象——他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他甚至纠正了我们的一个看法:过去我们想到美国男人的时候,脑子里面总会冒出一个不负家庭责任的形象,可是凯文对女儿的责任感超过了我们熟悉的任何一个中国父亲。他每天花5个小时和女儿们呆在一起,而且,他的对女儿的那种关注之情,和我们所能想象的中国父亲不大一样。
问:我听说你对美国的教育制度持很强烈的批评态度?
答:不完全是批评,美国教育制度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人类社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培养下一代。可是我们教给下一代什么呢?这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也是我们每天都应该问的问题,比如我有两个女儿,我就要问,学校要教给女孩子什么东西?
问:你对女儿的未来有自己的设计和期望吗?
答:我没有具体的目标和计划,我不能决定女儿应该做什么。我的女儿非常聪明,我只是希望她们将来的工作会更多地使用大脑。她们如果不能做很智慧的工作,就会不开心,觉得无聊。我不会强迫女儿去做什么,但我鼓励女儿在学校去学习难度更大的课程。我认为,女儿在学校学习知识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学习“怎样学习”。如果不知道怎样很快地学习新东西,她们在信息社会中将很难生存。
问:能告诉我你的女儿多大了吗?
答:12岁(从口袋里掏出皮夹,拿出6张女儿的照片)。你看,这是她们的照片……
问:双胞胎?
答:是啊,是啊(笑)。你看,这是伊丽莎白,这是亚历山大。这是她们一岁照的(笑),这是5岁照的(笑),这是最近照的(笑)。
问:你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和她们在一起?
答:差不多5个小时。早上一个小时,晚上四个小时。我每天早上给她们做早餐,和她们一起吃早饭。晚上从学校接她们回家,给她们做晚饭,和她们一起度过整个晚上,直到她们睡觉。我认为花些时间和女儿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研究都证明,家庭成员坐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能使家庭更快乐更幸福。
问:在美国西部,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家庭生活方式吗?
答:我不能确定,因为我没有看到统计数字,也许这要看不同的地区。
问:你是一个很辛苦也很幸福的父亲。
答:做一个好父亲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我非常努力。我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好父亲,但我要努力去做一个不坏的父亲。做父亲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比如说,你小时候不喜欢父母做的事情,现在你做了父亲,就会下决心不对你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有时候你发现,你小时候不喜欢父母做的事情,现在你却不得不对你的孩子做,所以你能更加理解你的父母。你父母的一些错误,你可以避免,但是你可能又会犯一些新的错误。
问: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人们都在谈论美国梦。大家都相信,一个人不怕出身低微,只要努力,就能改变自己,升到这个社会的顶上。你认为这个梦是真的吗?
答:所谓教育,就是把造就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但是到下一代,也还是有人在底层,有人在上层,和现在是同样的分布。所以,总是有些人能实现这个梦想,有很多人不能实现。在美国,人们告诉你,人人都可以实现“美国梦”,如果你没有实现,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在英国,人们会告诉你,每个人出生在不同的阶层上,如果你在低层,你就应该很高兴,为什么要到高层去呢?比如说你生活在低层,每天在工厂里工作8小时,其他时间都是你自己的。可是如果你在高层,就不是这种情况,你要经常加班,老板要求你做很多额外的事情,否则你就不能发展。所以低阶层的人也有好处,因为你不需要考虑很多事情。
问:有钱的人没有时间,有时间的人没有钱?
答:(笑)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在美国和在英国,人们说的事情不一样,但你会发现结果是一样的。阶层总是会有,人们总是在做不同的工作。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总要有一些人在上面,而另外一些人在下面。
问:那么什么人该在上面?什么人该在下面?
答:(笑)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质,教育所能做的,就是把社会的本身复制给下一代。在美国,有一句老话:权力是会消失的,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消失。即使你把最优秀的人放在上面,也会有腐败的事情发生。所以社会总是在变化,你没有办法永远赢。
做孩子喜欢的事情,不是让孩子做你喜欢的事
做孩子喜欢的事情,不是让孩子做你喜欢的事
父亲领着我走在那条街上,走过去再走回来,不停地找啊找,为的只是要满足我心中的一个愿望。
——周明
父母一生为孩子做的事情不计其数,可是能够在孩子心里留下烙印、永难磨灭的,通常
只有很少的几件。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所有那些在孩子心中具有永恒意义的瞬间,都是孩子们真正喜欢的,而不是父母自己喜欢的。
就像我们在前边叙述的,周明的父母对儿子有着无限的期待,但是周明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这种期待中长大的。父亲从来不会把自己的要求对儿子说出来,相反,他希望自己能满足儿子的要求。
虽然生活在城里,但周家境况一直艰难。父亲每月70多块钱的工资要支付全家的生活,要供养住在农村的爷爷和奶奶,还要供三个儿子读书。所以,当周明有一天说“想买一本英语教材”的时候,父亲的第一个反应是:“那本书要多少钱呢?”
“我也不知道要多少钱。”儿子小心翼翼地说。
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待父亲的“第一反应”和儿子的“小心翼翼”,是怎么也不能理解的。但是在20多年前,几乎家家都是如此。
中国孩子们学习英语的兴趣,是从1972年美国总统访华之后开始的,但在以后的几年里发展得相当缓慢。等到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广播电台里面开办了“广播英语”,大城市里终于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轮“英语热”。周明那时候刚刚进入初中,又是住在承德这座偏僻的小城,学习英语并不成风,可是这孩子对语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和热情。
父亲不是先知,不会预测儿子的未来之路,那时候他也不会像今天的父母一样,知道一口娴熟的英语是孩子必需的技能。他只不过是一个父亲,觉得儿子的愿望就在那本英语教材里,所以下定决心为儿子买来。
父亲重新计算了家庭的收支,腾出一笔钱来,然后问儿子那书是什么名字,可是儿子也说不出来。
“没关系,”父亲笑道,“我们挨家去找。”
父子两人走出家门,走到大街上。这座城市并不大,当时市民说它是“一条大街一个楼,一个警察一个猴。”两个人舍不得花钱坐车,徒步走进城,用了半个小时才走到最繁华的那条街上,从这头走到那头,每见到一家书店,走进去,周明就会听到父亲拉着售货员说:
“我的儿子想要一本书,是学英语用的。”
父子俩走过去,又走过来。父亲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三遍,周明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却每一次都失望。
接着,他们看到了第四个书店,也是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家书店,父亲拉住售货员,第四遍说:
“我的儿子想要一本书,是学英语用的。”
就在这时,周明一声欢呼。他看见那书赫然放在书架上。
父亲也是一声欢呼。
“咱们家还没有《英汉辞典》啊。”周明还不满足。
但是爸爸没钱了。
看见儿子的眼里仍然满含期待。父亲又说:“这只是本小字典,我领你去看大的。”
父亲领着儿子到了勘探队,拿出公家用的大字典,摊在儿子面前。
“你要想看,就坐在这里翻吧。”父亲说,“下个月……下个月一定给你买。”
儿子笑了。
很多年以后,周明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把我们国家的计算机英汉翻译技术推向一个新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得益于他在计算机领域的天赋,而是他在语言方面的热情。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同行们都知道他是我们国家最杰出的自然语言处理专家,但是,在1977年冬季的这条大街上,似乎只有父亲一个人知道,应当满足这孩子对语言的愿望。
“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看到《英汉字典》。”周明说。
信任的力量
信任的力量
那个晚上,妈妈给了我最好的礼物,让我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童欣
童欣9岁那年的一个晚上,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在这之前整整24小时,这个男孩子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恐惧和焦虑中,不能自拔,上课总是分神,下课不说不笑,回到家里饭也不
想吃,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他的心情转阴为晴,体会到一种真正的喜悦。
童欣现在已经32岁,还对那个瞬间念念不忘:“这件事可能妈妈已经忘掉了。可它给我的印象很深。”
那时候他在读小学三年级,是个性格温顺、学习优秀的孩子。老师把他挑出来做班干部,以为他能成为全班同学的模范,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也是个孩子,偶尔也会淘气。
这一天老师正在讲课,童欣和同桌同学为了一点小事争执起来,愈演愈烈,最后当堂打了一架。
可以想见老师对他的失望。“身为班干部,竟犯这种错误,”老师指着他怒吼,“很严重。很严重。”
“严重”这个词,突然之间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在这孩子眼前张开。最要命的是,老师命令他回家去,请母亲到学校来。
那时候80年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潮流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不过,整个社会环境还是不喜欢淘气的孩子。老师总是要学生遵守纪律,服从集体,尊重老师,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文革”的阴云已经散去,童欣不用去参加“大批判”,也不用“天天读”了,但是每年3月都要和同学们去学习雷锋做好事,这是全国统一的“文明礼貌月”。
如果你考试成绩不好,老师会说“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不争气”;如果你考了个100分,老师就会说:“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容易就骄傲了”。所以,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童欣在那时候得到的教训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教育就是把你变成一个螺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就是这样的感觉。你就做到夹着尾巴做人就最好。”
学校里面不断颁发“小红花”,提拔“小队长”,让那些听话的孩子受到鼓舞,也让其他孩子有了学习的榜样。对于那些过于淘气不服管教的孩子,老师用召见家长的办法予以惩戒,是永远不变的教育方法,几乎所有稍微淘气一些的孩子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可是老师们永远不会想到,召见家长予以严责,对孩子心理上的伤害有多么大。它在孩子的心理上留下阴影,在孩子和老师之间造成敌意,也在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