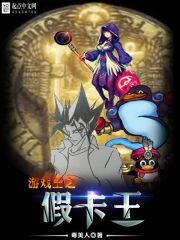法老王之咒-第8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到这里来干什么?龙象女会不会出现?”我蓦的意识到自己走错了地方,本该是躺在月光大酒店的一八零八房间里诱敌出现的。于是,我倏的起身,要走过侧面的大批观众,然后从入口退出去。
幕布上的图像消失了,一行巨大的黑字跳出来——“结束”。
我一下子释然:“电影放完了,正好随大家一起退场,不必突兀地向外走。”提前退场是对电影工作者的不尊重,这是全球电影观众都知道的常识,所以我重新坐下,等待旁边的人退场。可是,我靠在柔软的座椅上仅有几秒钟便睡了过去,并且睡得很沉,忘记了自己的一切使命。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念头突然弹起在脑海里:“那伦、苏坎怎么会失踪?他们明明就在酒店的贵宾套房里,谁能无影无形地潜入,然后把人带走?这几乎是正常情况下无法完成的,除非酒店里布满了暗道机关。如果老班在就好了,他最擅长用水银来查找暗道,在这一行里,班家自谦第二,就再没有哪一派敢称第一了。”
我倏的起身,马上发觉四周空无一人,幕布恢复了死气沉沉的灰白色。
“原来,大家都退场了?”我焦灼地向侧面跑了几步,踏上通向检票口的台阶。大约向上攀登了四五十级台阶后,我才猝然发现检票口的铁栅已经锁闭。外面的天空飘着大雪,天色也渐渐昏暗下来。
“开罗的雪可是真的不多见呢?”我低头自语,从铁栅里伸出手去,掌心里立刻落满了鹅毛般的雪片。
铁栅上挂着一块残旧的黑板,上面写着“每日一场、明日早来”这两行歪歪扭扭的英文。
我忽然明白过来,自己被困在下班后的电影院里了,而且要被困整整的一晚,但我的确有要事在身,酒店方面再有人失踪的话,米兹就得被逼得跳楼了。况且,他找不到我,会不会以为我也失踪了?
一个穿着破大衣的老头子跑过来,腰里挂着的一长串钥匙哗啦哗啦胡乱响着。他的两腮和下巴上长满了虬曲的胡子,看上去要多可笑有多可笑。
“喂,下次别在里面睡觉了,这是电影院,记住,这是电影院!”他嘟囔着开了铁栅上的锁,先放我出去,然后走进电影院,反手把门锁上。
我走下湿漉漉的台阶,猛然记起这老头子就是冷汉南。他当然也是肩负使命的,信誓旦旦地要去找回《太阳之轮》,从夏洛蒂那里换回“诅咒之石”交给洛琳。现在,洛琳都已经死在金字塔上了,他还悠闲地把自己关在电影院里睡大觉?
“教授?教授?”我用力踢打着那道锈迹斑斑的铁栅。
冷汉南已经走得很远了,就在通道尽头的幕布那里,像一个木偶剧里的道具般毫不起眼。我叫不回他,只能返身离开。台阶下面,是一个小小的自由市场,每一家小店的门口都撑着一把巨大的阳伞,挡住了纷飞的雪花。
在我左手边隔得最近的一把伞下,一个衣着朴素的老妇人正挥动着一把扇子,帮一只刚刚点燃的炉子扇火。青烟与雪花混合着,渐渐弥散在昏暗的天色里。
正文 第六部 风云际会 3阴间组织开始行动
( 本章字数:9151 更新时间:2009…7…16 22:41:51)
3阴间组织开始行动
上一章下一章返回本书返回目录
“母亲,我回来了。”我这样叫她。
她回过头,皱着眉看我,忽然长叹一声:“你去哪里了?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天都要黑了。”
“我去看电影,睡着了,然后被锁在电影院里,刚刚才有人开门放我出来。”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但在印象中,母亲不该这么老,而且脸色、语气也会比现在好得多。
“真的?真的?”她冷笑着连问了两遍,仿佛当我是在撒谎一样。
“真的,当然是真的。”我接过她手里的扇子。
“你——要倒霉了!”阳伞正对的小店里,一个男人大步跨出来,举起右手,狠狠地指着我的鼻尖,又一次大声重复,“你,要倒大霉了,知道不知道?”他的样子,如同早就洞悉天机、熟知未来一般,一副悲天悯人但又幸灾乐祸的模样,让我一阵阵后背发凉。
“我真的只是去看了一场电影,而且冷汉南教授可以作证,不信,你去问他!”我指向台阶上那道紧锁的栅栏。
男人的手指更用力地戳在我的额头上:“冷汉南死了,你、要、倒、大、霉、了!”
我的思想清晰了一些,也醒悟到冷汉南的确已经死在沙漠里,无人能够证明自己被困的过程了。
“他已经死了,又怎么可能在电影院里出现?”陡然间,我连打了三个寒颤,浑身上下冒出一层惊惧的冷汗。
“回家吧,回家再说。”母亲黯然地丢下扇子,走向一道破旧的篱笆。
我跟在后面,那男人也跟过来,兀自恶狠狠地追问:“你到底去了哪里?你到底去了哪里?陈鹰,我老实告诉你,你要倒大霉了——”
铮的一声,我的小刀已然脱鞘而出,压在他的喉结上。一瞬间,我的勇气全都回来了,不再做软弱无力的分辩,一字一句地告诉他:“离我远点,再跟来的话,当心你的狗命。”那些话,是我横行港岛黑道时经常挂在嘴边的,与所有年轻的社团龙头相同,我曾度过了一段一言不合、拔刀相向的灰暗日子。
“回家吧。”母亲站在篱笆那边招呼我。
“跟我动刀?你为什么不想想,是谁把你栽培成今天的样子?”男人冷笑起来,竟然是教官的声音。我盯着他的脸,依稀就是教官的模样。谈及用刀,他是世间唯一一个刀法在我之上的人,如果黎天能够被称为“刀术高手”的话,教官则可以被叫做“战术小刀之王”。
一辆破旧的老爷车吃力地吼叫着开过来,有个人摇下窗子向我打招呼。
我知道那是父亲,但不知为什么,自己却没有回应他,只是默默地收回小刀,抬头看天。一片硕大的雪花落在我的额头上,转瞬化为冰水,凉凉地滑落在脸颊上。我有种放声大哭的脆弱冲动,但仍然强行忍住,只怕自己会因此而彻底崩溃掉,不复所有人眼里的英雄形像。
老爷车一直冲向篱笆,父亲望着我,完全忘记了应该踩下刹车,一直撞向篱笆后面的大树。
我醒了,睁开眼睛时,首先看到的是房顶上的花枝吊灯,那是月光大酒店的独特标志。
“只是一个梦?”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仅用眼角余光扫视着房间里的一切。卧室的门半敞着,那是我躺下前故意留下的开阖角度,能够从卧室里清楚地观察到西墙的中心。没有任何意外发生,让我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却也有淡淡的怅然。也许我太急于见到龙象女了,总想尽早把这件古怪的事彻底了断。
“嗯?白小谢呢?他竟然也……一起失踪了?”我呼的坐起来,额头上迅速渗出了一层冷汗。睡觉之前,我大意地忽略了他的存在,假如他也被龙象女袭击致死,麦爷留下的一切线索就将不复存在,白离在金字塔顶拿给我的“攒心虫”也没什么用处了。
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这么多年来,只跟妹妹相依为命。教官介入我们的生活时,我才十一岁,就已经懂得带着水果刀浪迹黑道了。所以,我的脑海里应该没有他们的样子,并且他们也不会在意我到底成长为什么人物。
“你要倒大霉了”——教官恶狠狠的声音犹然在耳边回荡,但他从来不这样跟我说话。在梦里,老妇人和开车男人的脸始终模模糊糊的,我虽然认定他们是自己的父母,却辨认不得他们的模样。
这个梦预示了什么?我被困在一个漆黑空间里、死掉的冷汉南重新出现、母亲愁郁的脸、父亲开着老爷车撞在树上……一切毫不相干的环节组合在一起,立刻让我有种莫名的心烦意乱之感。母亲一直重复着“回家”两个字,但我自小到大,从来没有在任何人地方找到“家”的感觉,天生就怀着一颗不断流浪的心。
或许是夏洛蒂下在汤里的miyao产生了某种后遗症,我又一次感到头昏脑胀起来。
“也许,仅仅是个令人不解的怪梦?”我下了床,活动了一下有些酸痛的双臂,准备走到客厅去。
“啪嗒”,一颗水珠从吊灯上滴下来,正落在我躺过的位置。我下意识地在额上抹了一把,因为自己梦中看见雪花飘落,正好停在额头上化为水珠,也许就是吊灯上滴水所致。不过,我的额头非常干爽,没有湿漉漉的感觉。
水珠滴在床单上,立刻铺散为明晃晃的银色小球,那竟然是一滴水银珠?我飞身上床,仔细地观察吊灯根部,正有两颗稍小一点的水银珠渗出来,转眼间便无声滴落。
“老班?水银注地九泉追踪**?”我讶然自语。
妙手班门自创的这种探索暗道机关的方法代代单传,是江湖上不可能出现盗版的绝技。只要见到它,便知道是老班亲自出手了。因为有莲花小娘子和婴儿的事,我不想把他拉到这件事里来,没想到他还是自作主张地暗地查看我的需要,然后偷偷动手。
就像田七一样,老班也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我救过他,他便会毫无保留地报恩。二十一世纪的江湖,像他们两个这种人已经稀少如史前动物了。
我跳下床,大步走入客厅,向头顶的吊灯望去。果不其然,那里的房顶上也有水银珠渗出来。可以想像,此刻月光大酒店的很多房间里都有这种现象,水银珠会藉着建筑物的缝隙悄然渗透下来,由顶到底,不放过任何可疑的空间。
老班告诉过我这种秘技的粗略模式,但具体到如何操作便绝口不谈了。这是班门的家族秘密,事关几百年的班姓荣耀,他连莲花小娘子都不会告诉。
“好了,有老班出马,终于能够解开一个疑团——”我走到西墙边,在墙面上重重地拍了一掌。
莲花小娘子年轻时艳绝一时,曾被江湖通道称为“美貌、暗器双绝”,想必他们的孩子一定会长得会很可爱。我已经签了那张支票作见面礼,等到事情告一段落时,一定会去看看他们的小孩子。
龙象女始终没再出现,我很谨慎地再次检查了洗手间、衣橱、阳台的各个角落,到处干干净净的,保持着服务生清扫过后的原状。
最后,我停在冰箱前,想要拿一瓶饮料解渴,但刚刚拉开柜门,立即听到小型气球的爆炸声。半开的冰箱里随即喷出一道浓重的白雾。我急速后退,鼻子里已然吸进了少许,一阵天旋地转传来,身子一软,便仰面朝天地跌了下去。
起初,神智还算清醒,摸索着想要爬到沙发上去,但一分钟后,我的四肢开始发麻,手臂也无法用力。
“这是欧洲黑道上的‘老虎烟’,会不会又是‘阴间’组织下的手?”我摇了摇头,努力撑起眼皮,观察着阳台方向。门是反锁着的,有敌人出现的话,只能是从相邻的阳台上跃过来。刀在裤袋里,枪在枕头下和床头柜里,但我感觉自己浑身的力量一下子散掉了,根本无法凝集。
阳台上传来玻璃窗缓缓滑动的声音,随即有三个人先后出现,踮着脚尖走进来。
“快点,他们就要到了,咱们大概只有十分钟时间。”有人焦灼地叫着。随即,两只毛茸茸的大手伸进我的腋下,毫不费力地将我抱了起来,大步走进卧室。
这是一个高大健壮的俄罗斯人,腰间高高隆起,一看便知道是插着大口径手枪。
“桑,给你五分钟时间化妆成他的样子,越快越好。”发号施令的人脸色黝黑,正在弯腰伸手,将一只黑色盒子固定在沙发底下。
第三个人则是一个脸色苍白的亚洲人,手里提着一只金利来的公文包,跟着走进来,拉开拉链,把包里的瓶瓶罐罐倒在床上。他先盯着我的脸看了几秒钟,然后拾起镜子和眉笔,仔细地在自己脸上描画起来。
我瞬间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大约是要妆扮成我的样子,留在这个房间里等什么人。
俄罗斯壮汉掀开西装下摆,抽出一支银版沙漠之鹰,熟练地退下弹夹,在手里掂量着。
“喂,卡夫,你在发什么愣?”那个小头目暴躁地吼叫着,“龙堂是美国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