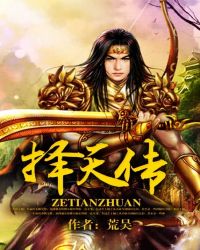韩少功评传-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圣诞。”
与韩少功一家朝夕相处了七年的狮毛狗三毛,没有等到记录它生平事迹的《山南水北》出版,就于2005年冬天在海口无疾而终。已经停止进食的它,似乎意识到大限的来临,表现出对亲人不舍的依恋。最后的时刻,它卧伏在韩少功的一只布鞋上,在这位人类朋友的抚摸中渐渐归于寂静。忍受不了这种寂静的韩少功一头冲进卫生间,将水龙头开到极限,久久不能出来跟客人见面。在那个时刻,他想了许多,还想到:“我将来到另一个世界去的时候,这家伙也会摇着尾巴,直愣愣地认出我,在那个世界的门口迎接我,结束我们短暂的分手。想到这一点,想到前面的迎候者不但有我的父亲,我的母亲,还有这样一对熟悉的眼睛,我就觉得那一天没什么可怕。那一天甚至是快活的时光,最终执手相聚的日子。不是吗?”(《山南水北?三毛的来去》)他和妻子把这位多年的伙伴埋葬在一棵老榕树下,还把它的相片扩印了几张。不论是到过他海口家里还是汨罗家里的,都可以在墙壁上看到三毛神色苍茫的遗容。
《山南水北》的封笔,意味着韩少功除了个人家庭隐私之外的绝大部分经验都转换成为文字,进入了文化出版。作为一个孜孜不倦的意义追寻者,如果不打算早早结束自己的文学生涯,写什么的问题对他来讲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这也许是里尔克诗中所咏叹的那个“严重的时刻”。在回答笔者关于将来的提问时,韩少功有所感慨,他说:可惜自己已不再年轻,要不真想到人类一些滴血的刀口上看看。
韩少功本人从不会轻言放弃,他的人生每天都在继续,他的文学履历仍在书写之中,他的身手也还相当矫捷,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设想的,也是可以期待的,但这本评传只能到此结束了。
后记
当杨莉女士辗转找上门来时,我没有过多的犹豫就接受了这个写作任务。韩少功先生的文学活动,几乎贯穿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历史,在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上世纪90年代文学思潮分化与冲突中,均有不俗的表现。进入新世纪之后,他也拿出了备受关注的作品。屈数下来,能够在那么长时间内保持创造力的作家已经不多。因此,通过韩少功这个特殊的个案,温习一下新时期文学的进程,刷新自己业已陈旧剥落的知识,阐发自己对一些文字现象的见解,成为写作的一个动机。现在看来,这个目的已经达到。
回想起来,与韩少功先生认识也有十五个年头了。也许是因为共同生活在美丽的海南岛上,经常可以在椰子树下见面说话;也许是彼此之间有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交流一直都在进行着,对他作品的关注也比其他作家要充分些,还陆续写过《马桥词典》、《暗示》等作品的评议文字。早在1994年年初,我还是一名报纸编辑的时候,就曾写过一篇三万多字的类似评传的文章。由于涉及一些当时认为敏感的话题,那篇文章没有在报刊上完整地刊载过。大约在三年前,有人因为要写韩少功评传找到我,便将其提供给了他们。后来发现,不仅叙述内容,包括一些评论文字也被不加注明地援用了。
尽管有了上述的因缘铺垫,在接受本书的写作任务后,本人还是对传主进行了颇为正式的专门采访,利用节假日到他汨罗乡下跑了一趟,与他一起走访山里的人家,他的邻居和农友。写作过程中,传的部分也咨询了蒋子丹女士和传主过去的一些同事,打探核对相关的情况。当然,还把能够找到的韩少功作品重读了一遍,查阅了少量有关这些作品的评论资料。不过,本书评论部分的写作主要依据作者对韩少功作品的直接阅读,除了其中注明出处的引据之外,没有过多借鉴他人的研究。因此,倘若书中存在悖谬不实的成分,本人也难辞其咎。
韩少功先生年庚未满甲子,他的生活和创作都还在进行之中。考虑到比他更年轻的人都已经立传,增加这一本也未尝不可,但这个时候来叙述一个人的生平还是早了点,也有一些不便的地方。有一些涉及人事的评议,可能违背了“勿谓言之预也”的古训;还有一些已经了结的事情,未能写进本书之中。至于更为详尽和隐秘的细节和内心活动,则只能留待他本人自述的撰写。
感谢韩少功先生接受作者不厌其烦的提问;感谢蒋子丹、单正平诸君无偿提供有关资料;感谢海南省作家协会和《天涯》杂志社同仁们的关心支持,还有杨莉女士的再三催促,使本书得以尽早收笔。
有清水流过的地方就会有草木生长。
孔见记于府城金花市场
2007年6月16日
txt小说上传分享
附 录(1)
韩少功、孔见对话录
孔见:你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记忆让你终生难忘?能否谈谈你最伤感的时期和最伤感的事情?
韩少功:对不舒服、不开心的日子总是记忆深刻一些,尤其亲人的生离死别更是如此。要说最伤感的时期,第一要算“文革”中父亲的去世和家庭变故。卡夫卡对他父亲说过:我之所以在作品里抱怨,就是我不能趴在你的肩膀上哭泣。我也是在那时候失去了一个可依靠的肩膀。第二可能是90年代初期,当时发生了一些事,使我有被背弃和孤立之感。在那以前,我觉得尼采很难懂。在那以后,我突然觉得尼采不过是通俗的实话实说。
孔见:新时期文学延续了三十年,有的作家走着走着就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新路,但你一直在这条路上走着,保持着一种活泼进取的姿态。我想,这其中除了你始终保持对现实问题的敏感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你保持着学习的态度,不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交叉阅读中西方的经典作品。我有一个叫洪小波的朋友是你的读者,他很钦佩你一直保持着精神上的成长。
韩少功:作家的兴奋点很重要。让他兴奋起来的,开始可能是好奇,是名和利,还有生活中积累的冷暖恩怨。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到后来,马拉松一样的文学长跑需要持久动力,那就需要信念的定力和思想的活力。我读书并不多,聊感欣慰的是,我喜欢把书本知识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抱着怀疑的态度读书。读书不是读古人的结论。古人再高明的结论拿到今天来也可能是无用的。我们需要读出古人的生活,看他们是面对什么条件和环境提出什么样的见解,以便解决当时的问题,回应当时的现实,这才能体会到他们的智慧。
孔见:也就是说,任何话语都是面对某种现实和谈话对象而说的,读书必须能够还原这种对话关系来理解所说出的东西,不然就可能把书读死了。因为换一种形势和对象,话就不能这么说了。法无定法,说的也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韩少功:是的。除了读书,还有一个关怀半径。有一个作家对我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里提不起神,觉得没什么好学的,没什么要说的。我问他,世界上每天发生那么多的事情,贫困、压迫、暴力、死亡、伤害、对抗,等等,你都看不见吗?或者看见了你都心安理得?当然,那些事情都可以与你没关系,有关系那是你自找的,是你关怀的后果。这就涉及一个人的关怀半径。如果你的半径足够长,你就是一辈子不停顿,也想不完和学不完,成天有忙不完的事。
孔见:说到关怀,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对人的关怀是文学的传统,但关怀人是关怀人的什么东西?是物质生活上的嘘寒问暖,欲望上的满足和放纵?还是人性精神上的升华和进化?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不好笼统地谈论关怀。
韩少功:这一点问得好,很少有人这样问过。人总是受制于人的基本条件。比如说,在粮食有限的情况下,我吃饱你就吃不饱,你受益我就不受益,因此人都有利己的本能。但人还有恻隐,有同情,有感同身受,看见别人受苦自己也不舒服,这是因为人还有意识和情感等精神世界的活动,成为群体联结的纽带。就物质利益而言,人都是个体的;就精神利益而言,人又都是群体的。这就是人的双重基本条件。没有人敢说他没有自利的本能,也没有人敢说他从无恻隐和同情的心头一颤——即利他的本能。人的自我冲突,或者说半魔与半佛的纠缠,就是这样产生的。
我们看到街面上一些可怜人,但不能停下来一律给以帮助。看到一条流浪狗恓恓惶惶饥寒交迫,也没法把它带回家收留。我们会有一种罪感。在另一方面,在复杂的因果网络里,恶因可能促成善果,善因可能结下恶果。比如,我们帮助一个人,给他一千块钱,但也可能使他变得懒惰,学会了坐享其成。那么这一千块钱是帮他还是害他?总之,一是我们能够做的很少很少;二是我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是错。因此我们会有很多视而不见,会有很多遗憾和欠账,如果说“原罪”,这就是原罪。
但我们也不能滑向虚无主义,不能说佛家“无善无恶”就是纵恶。康德说,道德是“自我立法”,并无什么客观标准。所以关键是你心中要明白:你是不是动了心?你是动了什么心去做这件事?我们对自己大概只能管住这一条。至于社会,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也不是完全糟糕的,情况总在历史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波动,在人性总体合力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波动。三千多年了,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理想社会,只是不完美社会的不同变体。这不是什么悲观,是一种现实态度。我们的积极能动性表现在:当社会状况比较坏的时候让它不那么坏而已。我们不能实现天国,但我们能够减灾和止损。这当然只是局限在物质利益分配方面的关切。至于在精神上提升他人,比如实现“六亿人民尽舜尧”,我觉得是一种美好的奢望。书包 网 87book。com 想看书来
附 录(2)
孔见:我不能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有些人之所以做一些不利于人,其实也不利于己的事情,可能是因为迷惘和困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和对的。也就是说是认识出了问题,并非品性的邪恶。因此,需要一种启蒙和警醒,一种“以心传心”。
韩少功:我们也许可以让他的行为符合某种规范,让他逐利时不那么狭隘和短视,但要让他生出佛心和圣心,那是另一回事。外因总是很有限的。《礼记》里说:“有来学无往教。”他自己如果没有道德要求,你的主动教育可能一厢情愿。即使有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前不久我到峨眉山,看到烧香拜佛的信徒很多。我发现有两种人占有很大比例,一种是穷人,生活绝望没有着落的;一种是坏人,脑满肠肥但紧张惶恐不安的,需要心理平衡和补偿。前一种人是求利益,后一种人是找心安,离真正的菩萨境界都还太远。我不会歧视他们,但也不会那么书生气,以为他们跪跪拜拜就有了可靠的道德。寺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内心的应急处理,管不了长远。
在我看来,逐利的理性化还是逐利,比胡作非为好一点,或者说好很多,但不能代替康德说的精神“崇高”。一个人的道德要经过千锤百炼,是用委屈、失望、痛心、麻烦等磨出来的。把自己锁进一个孤寂庙宇并不是捷径。殿堂其实就在世俗生活中。心里真有了一个殿堂,才扛得起千灾万难。
孔见:以前的作家,包括现在国外的作家,通常能够公然地讨论自己的理想关怀,这体现一种精神上的坦率。但在今天的中国,这变成了一个最私密的事情,你现在也是避免一种直接的表达。这是为什么呢?
韩少功:我也赞成谈谈理想,但理想不是一种理论,一种观念,而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状态和实践过程,很难简化成几堂课或几次讨论。从低标准来说,理想是可以谈的。从最高标准来讲,理想又是不可以谈的。理想通常是个人事务,谈出来就可能强加于人,做起来就可能对异己形成压迫,这就是历史上理想总是传薪不熄,但理想主义的全###动又很容易成为宗教狂热的原因。上帝的事交给上帝,恺撒的事交给恺撒。恺撒要当兼职上帝,总是失败和可怕的,甚至难免血腥暴力。这样,我以为,理想教育功莫大焉,但一个人如果不奢望大家都同自己活得一样,又不必经常高调布道,常常需要节制和容忍。
孔见:从《爸爸爸》到《山南水北》,你的作品都有神秘和超验的成分,对世界做了一些超现实的想象。这些想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韩少功:文学中总是活跃着神话元素,因为文学常常需要超越经验的常识的边界,实现心灵的远飞。广义的神话,并不一定就是装神弄鬼,只是保留和处理更多的可能性,引导想象力向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