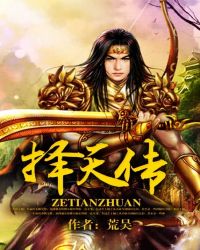韩少功评传-第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正面面对这个变革中问题丛生的国家现实,获得与自己过去记忆相对应的新鲜经验,哪怕是揪心的苦痛与忧愤,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也是一种生命的有机物。实际上,许多出走海外的才华横溢的作家,在异域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就,他们在市场社会能够照顾好自己身体的生活就不错。
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和省政协常委的职务,并没有带来多少事情,相当一段时间内,他都是一个专业作家。除了每月骑着半新的本田摩托车到单位领取工资和邮件,到街上去换煤气罐,偶尔拿着本子踏着黑布鞋去参加研讨会什么的,其余白天的时间他都在海南师范学院的怡园里看书写作。他养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晚上一般停止工作,只是看看电视或与上门的客人聊天,生活近似于一个山林里的隐者。邻居们记得,这个住在顶层六楼的人经常悠闲地拖着扫把,将一到六楼的阶梯打扫得干干净净,像学院总务处的一个勤杂工。寂静的日子里,又有《领袖之死》、《北门口预言》、《红苹果例外》等小说相继脱笔,一部至今都没有出版的长篇小说也陆陆续续地从电脑打字机里出来。《北门口预言》再度显示了一个专业写作者在意象的捕捉和氛围营造方面的功底,只是在立意方面似乎有些分散,凝聚不起足够强烈的力量来击打读者。
韩少功是一个在文体上有自觉追求的作家,一段时间,他都在捉摸一种称为“幻想自叙体”的叙述方式。这个时期出手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叙述方式的实验。在这种叙述中,现实和幻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扑朔迷离、似是而非的真实。当然,他感兴趣的“幻想”并非未来世界的科学幻想,不是人长出翅膀,机器征服人类,外星人占领地球之类。他的幻想是对同一现实多种可能性的演出,企图表达生活的模棱两可、恍恍若若,难以捉摸的真实,暗藏杀机,猝不及料的变数和恍然大悟的明白和会心一笑的开朗。这种文体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制造了神秘。
构成幻想和神秘的前提,同样是构成怀疑的前提,不同的是,幻想和神秘指向未知的领域,而怀疑则指向已知的常识和公理。许多年来,韩少功像一只狐狸那样怀疑着,从伟大的宇宙真理到亲人朋友的品质。怀疑主义的相对、否定、排除、破坏性格极大地帮助了他,使他取得了知性上的进步并区别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由于知性见地上普遍缺乏纵深和提高,不少作家在同一水平面上挥霍了自己大量才华,排泄了大量的精血,这是令人惋惜的。有的作家以烈性的感情浓度撞击别人的胸脯以获得共鸣,让人跟着他走;有的作家则以离奇怪诞、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和残酷的血腥以及色相暴露来刺戳别人的眼睛,挑逗别人阴暗情欲;还有一部分作家沦为工匠,把玩文体文字技艺走火入魔,把人学变成文学,把文学变成艺术,把艺术变成文字的嬉戏。重视文学知性意义的韩少功,其作品的魅力在于说服,不在于怂恿、引诱和打动。
在怀疑的激流和神秘幻想的旋涡之间,敬畏应当也只能是一个浮标。然而,当敬畏可以浮动时,敬畏便不足以敬畏,于是要敬畏和不要敬畏都同样困难了。许多事情的最后都是十分尴尬的。韩少功曾经表示:只有对人性的绝望和怜悯才能深深打动他。
尽管这一阶段的小说并不是韩少功十分得意的文字,但对于神秘之境的幻想自叙在他的创作中一直延续下来,后来的作品,包括《马桥词典》、《暗示》和《山南水北》,都或多或少地含有这种魅惑的成分。而它的源头,可能是寻根时期承接上的巫楚文化余脉。
txt小说上传分享
灵魂的声音(1)
20世纪90年代初期,文学已经丧失其轰动效应。韩少功零星发表的小说,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倒是他写作的《性而上的迷失》、《佛魔一念间》等一系列思想随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进一步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思想性作家的定位。
20世纪90年代对于中国是一个特殊的阶段,首先,知识精英们千呼万唤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过去完全由政府调配的社会资源逐渐转向市场调配,人们生存的自由空间不断扩大,带来了对有限机会的无限竞争。一马平川的地面开始浮动,原来在人民群众概念下过着同质同量生活的中国人开始分化,阶层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家庭之间地位和收入的距离越来越大。80年代得以复苏的乡村大面积凋敝,成千上万的农民潮水般地涌入城市,城市里又有大量的人员下岗待业。作为自由竞争补偿机制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时间还建立不起来,国民教育、公共医疗等许多本来应该由政府支付的公共产品,都在大力推行产业化、商业化,要求人们购买,在社会竞争失利的人将面临无底的深渊。于是竞争愈演愈烈,不断升级并且迅速恶性化,社会的道德底线也一再下降,许多人开始在道德和法律的界线之外寻找生存的机会。交易中充塞着欺诈行为,市场上到处是假冒伪劣产品,街面上铤而走险和见死不救的事情时有发生。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都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到处都有布设的陷阱和圈套,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总是处于一种焦灼、惶恐之中,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曾经为市场经济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们惊讶地发现,在正在建立的体制下,他们的位置也飘摇起来,而且不断下陷。面对真龙的降临,这些原本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有可能沦为弱势群体的叶公们心意徊徨,失去了对现实说话的能力和自信,更遑论要批判什么了。物质生活的迫切性使它赢得了远远超过精神生活的价值,对正在下沉的肉身的拯救优先于对灵魂的拯救。
此外,是西方后现代思潮的澎湃涌入,成为失语者最后的语言,成为一种所向披靡的学术时尚,将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学院知识分子如数收容,变成它的信徒和弟子。他们用中国生活的经验去理解、演绎西方的话语,并且不加检视和批判就拿来套解中国的社会现象,瓦解中国人心中所剩无几的价值理念,为中国社会的世俗化,乃至恶俗化浪潮推波助澜。
应该说,中国刚刚经历过为期不短的禁锢个人肉体欲望的历史阶段,人们对自身的身体和与之相应的物质生活的福祉还相当陌生并心存好奇,深明世道人心的人对这种世俗化的浪潮是可以理解和默认的,但理解之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则是另一个问题。是采取一种“勿忘勿助”的态度呢,还是采取一种怂恿激励的态度,像过去歌颂高标绝俗的极端理想主义那样来歌颂它,把这种生活取向抬举为唯一真实的货币来排除一切价值?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严格说来,人生面对的是由诸多问题交集起来的一个问题域,而不仅仅是某个单一的问题,因此对它的回答是一种道,而不仅仅是一个理。人生在世,既要解决与生俱来的所谓世俗化的问题,解决人能否在地面上站立起来乃至行走的问题,还要解决情感的慰藉与精神的升华与超越,解决人能否在天空中飞翔起来的问题——这关乎心灵的福祉。
处身如此跌宕与喧嚣的时代,面对生活提出的种种困惑,是一个作家欣逢的幸运。韩少功一直关注着社会和人心的微妙变化,对诸多问题都进行了沉静的思考。他接连抛出了《灵魂的声音》、《无价之人》、《性而上的迷失》、《伪小人》、《夜行者梦语》、《个狗主义》、《世界》、《佛魔一念间》等一系列随笔,对流行思潮和大众心理盲区和误区进行分析与批判。
《灵魂的声音》(见《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是针对时下文学中存在的精神失血状况而写的,文章指出:“今天小说的难点是真情实感的问题,是小说能否重新获得灵魂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与整个时代精神生活的荒漠化状况有关。“我们身处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周围的情感正在沙化。博士生在小奸商面前点头哈腰争相献媚。女中学生登上歌台便如已经谈过上百次恋爱一样要死要活。白天造反的斗士晚上偷偷给官僚送礼。满嘴庄禅的高人盯着豪华别墅眼红。先锋派先锋地盘剥童工。自由派自由地争官。耻言理想,理想只是在上街民主表演或向海外华侨要钱时的面具。蔑视道德,道德的最后利用价值只是用来指责抛弃自己的情妇或情夫。什么都敢干,但又都向往着不做事而多捞钱。到处可见浮躁不宁面容紧张的精神流氓。”丧失精神根基的人们,不可能自足自立,他们势必趋附并委身于权势和物质之上,造作出各种无耻和下贱的模样,失意时颓丧潦倒,得志时穷凶极恶,甚嚣尘上。“权势和无耻是他们的憎恶所在更是他们的羡慕所在。灵魂纷纷熄灭的‘痞子运动’正在成为我们的一部分现实。这种价值真空的状态,当然只会生长出空洞无聊的文学。”凭借一些从异域引进的叙述和修辞技术,变换缭乱的花样维持着虚假的形态。
灵魂的声音(2)
在批判众多无名氏的同时,他赞扬《心灵史》的作者张承志和《我与地坛》的作者史铁生,称他们是“单兵作战”的圣战者。“他们的意义在于反抗精神叛卖的黑暗,并被黑暗衬托得更为灿烂。他们的光辉不是因为满身披挂,而是因为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心诚则灵,立地成佛,说出一些对这个世界诚实的体会。”尽管存在某种视阈上的局限,但张承志获得了生命的激|情,拥有了与全人类相通的赤子的血性和赖以为文的高贵的灵魂,“至少不是一个纸人”。而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以个体生命为路标,孤军深入,默默探测人类心灵的纯净和辉煌,“显示出他出于通透的一种拒绝和一种对人世至宥至慈的宽厚,他是一尊微笑着的菩萨”。
《夜行者梦语》(见《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是对中国人文领域流行乃至泛滥的后现代思潮的解析;也是在作为绝对价值和绝对责任化身的上帝死亡,从而上帝说要有于是就有的光熄灭之后的暗夜里,对人们精神困境的一种探索;还是对圣者与流氓两种不同人格的一种勘误。文章首先提醒惯于引渡外来概念判断事物的人们,概念的内涵不仅仅是词典里的定义,“常常含注和负载着各种不同的心绪、欲念、人生经验”。因此,哲学是从生命深处涌现出来,而不是用脑子研究出来的。脑子的研究者感悟不到概念之外的指涉。就拿虚无来说也有两种:“一种是建设性执著后的虚无,是呕心沥血艰难求索后的困惑与茫然;一种是消费性执著后的虚无,是声色犬马花天酒地之后的无聊和厌倦。圣者和流氓都看破了钱财,但前者首先是看破了自己的钱财,我的就是大家的。而后者首先看破了别人的钱财,大家的就是我的。圣者和流氓都可以怀疑爱情,但前者可能从此节欲自重,慎于风月;而后者可能从此纵欲无度,见女人就上。”上帝死亡对于有些人来说,意味着承当更多的责任,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意味着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只有无边际的权利和无止境的欲求。
“人在谋杀上帝的同时,也悄悄开始了对自己的谋杀。”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人也被宣布死亡。在后现代的解构下,人的本原已成为虚妄,世界不过是一大堆文本,没有终极和根本的东西,“一切道德和审美的等级制度都被证明出假定性和暂时性”。于是,一切都被允许,怎样都行,“唯一不行的,即是反对怎样都行”。人不再为任何本真的、神圣的、绝对的价值法则活着,人的存在也被还原为身体一维,身体功能欲望之外的一切存在诉求都是虚妄。“身体”一词对“自我”的替换,“意味着人和上帝的彻底决裂,意味着人对动物性生存的向往与认同——你别把我当人”。
韩少功认为,欧洲现代精神危机不是产生于贫穷,而是产生于富庶。叔本华、尼采、萨特他们成长的背景,“是巴洛克式的浮华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锦衣玉食,是优雅而造作的礼仪,严密而冷酷的法律,强大而粗暴的机器,精深而繁琐的知识”。而他们的中国学生却是用迥然不同的中国经验来解读老师的精神叛逆,并且加以无条件限制的延用。这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差不多就是穷人想有点富人的忧愁,要发点富人的脾气;差不多就是把富人的减肥药,当成穷人的救命粮”。
在韩少功看来,“后现代哲学是属于幽室、荒原、月球的哲学,是独处者的哲学,不是社会哲学;是幻想者的哲学,不是行动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