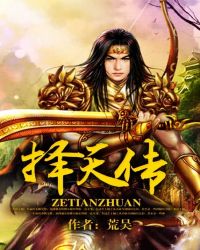逆袭水浒传-第4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晁盖大急,拉住两人道:“先勿辞行,有话说来。”当下一左一右携了两个到了门外,朝里面唤道:“扈官人,晁某来访。”扈三娘在内道:“请保正进屋说话。”
晁盖得了允准,方才动步,拉着两个进屋来,只见三娘从屏风后转出,手上提了两个包袱,显然也是收拾好了要走。晁盖见了更急,上前夹手夺了两个包袱,放在桌上,口中道:“三位稍安勿躁,请坐下听小可一言。”
三娘兀自不动,晁盖先请公孙胜与刘唐坐了,跟着来到三娘身边,拱手虚扶一回,请三娘坐了主位,如此三娘方才坐了。坐定后,晁盖当着三人面,朝三娘深深一拜道:“晁某是个不读书史的人,甚是粗卤,这几日多有得罪之处,还请扈官人万勿见怪,晁某这厢与官人赔礼了。”
三娘见晁盖礼重,暗想道:“晁盖这厮瞧不起我是女儿身,怎的忽然转性了?明知我是女儿身时,也能如此重礼,倒也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汉子。”当下受了他一拜后,方才起身,伸手去扶时,晁盖略略一躲,三娘柳眉一竖,硬扶起道:“保正躲我这般,我有麻风焉?”
晁盖急忙道:“绝无此念,晁某敬官人如天人一般,晁某一介村夫,污秽肮脏,只恐污了官人千金贵体。”说到这里,见三娘脸如寒霜,顿足道:“对着官人,我就是不会说话,是否又说错了?”
三娘这才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玉手拉着晁盖坐在旁边,自己还是坐了主位,正色道:“保正乃真诚之人,你我相交,做兄弟情义,只问义气,不提其他,你若不做我是兄弟时,我们三个便早早拜辞,生辰纲之事,自当守秘,今后无相往来,也便是了。”
晁盖急道:“自然当扈官人是兄弟,不做他想,更没有半分不敬之意,此乃肺腑之言。”三娘笑道:“如此便好,此前之事就此揭过。”公孙胜也笑笑说道:“保正知晓事情后,还能如此,便是真心敬重官人。”刘唐不知三个说什么,只是瞪大眼睛问道:“官人,那我们还走吗?”三个都是大笑起来,晁盖拉了刘唐笑道:“要走,但却是走去吃酒!”
当下晁盖命庄客杀翻一头牛,办下一桌筵席,请了三娘、公孙胜、吴用、刘唐入席,五人畅说谈笑,好不痛快。席间,晁盖见三娘豪饮,好胜心起,又想与三娘较量一番酒量,便命人取两坛酒来,口中道:“扈官人海量,今日高兴,可与我斗饮?”
三娘笑了笑道:“有何不可?”当下两个各取大盅来,庄客筛满酒来,两个都是连干十余碗面不改色,最后两坛酒都吃尽时,晁盖已然醉倒,三娘却还甚为清醒,只笑道:“保正,可还能喝?”晁盖醉得不省人事,吴用急忙请庄客扶回,看了看扈三娘,心头暗想:“此女子果然怪异。”自这日后,晁盖不敢小觑三娘,早晚仍旧相敬如宾,互相较量武艺,款待殷勤不提。
又过了数日,三阮按日期来到庄内聚齐,晁盖、吴用早差人唤来那黄泥岗安乐村白日鼠白胜前来,众人聚齐后,自然又是先摆下酒筵大肆庆贺一番。
酒筵后,九个人在密室内坐定,吴用将智取之法细说了一遍,果然还是那套扮作贩枣客商,然后白胜担酒来卖的招数,教各自言语、扮相记熟,只有三娘却无安排。三娘奇道:“加亮先生,各位都有司职,为何我没安排?”吴用道:“官人面相俊美,一望便不似行走客商,是以未曾安排。”三娘笑道:“那黄泥岗虽然多有强人出没,平素没人往来,但你们在那里干这大事,周遭没个望风之人也是不妥,我身手还算迅捷,就四下望风好了。”
吴用赞道:“官人心思细腻,小生都忘了此节,那黄泥岗虽过往人少,也并非无人过往,若正下手时,被人撞见,定会事败。”晁盖大喜道:“正是如此,就有劳扈官人在黄泥岗周遭巡望,下手这等粗鄙之事,我等来做。”
三娘笑了笑,颔首应了,心头却想:“当初只看这一段时,还真替几个捏把汗,几个人就这般去智取生辰纲,左近也没安排个人把风,真个是贼大胆。”跟着又道:“此去黄泥岗动手时便是聚在一处,但须得分成几拔来走,否则一路上七八人一起,又推贩枣江州车儿,甚是扎眼。而且大家装束不必变来,各自打扮行走便了,到了白胜家中再行换装也来得及。那江州车儿先教推去黄泥岗道边藏了,用时取出来便可。”
吴用一拍大腿道:“官人说得是,险些误了大事。”三娘肚子里好笑,这智多星真是只管头面,不顾身后。当下商议定,白胜与刘唐推两辆江州车儿先走,到安乐村排铺前路。公孙胜与三阮四个亦推了三辆江州车儿,做第二拔上路,晁盖、扈三娘与吴用三个推两辆江州车儿最后赶来。
议定这事后,三娘又道:“一路上自带酒食吃喝,决不许进路上酒店打尖吃酒,更不要与人多话,以免露了脸面,教人记下,日后官府追缉起来时,被做公的问出端倪来。既然不入酒店歇宿,便将就都在白胜兄弟家内安住下,得手后便回庄上来。”
吴用叹道:“官人真个儿心细,此等末节都能想到。”扈三娘望着众人笑道:“不瞒各位,四年前劫了第一趟生辰纲的便是我,如今官府便连是何人动手都不得知,但听我吩咐时,各位事成后,都能逍遥法外,否则早晚被官府追缉!”众人都是一惊,晁盖瞪大眼睛道:“扈官人,那趟原来是你下的手,难怪了。”吴用也道:“有扈官人提点,必能成事!”众人都轰然称是。
商议定后,便在晁盖庄上安歇一夜,翌日收拾停当,便分几拔人前后往安乐村而去,白胜与刘唐与两辆车儿先走,到安乐村排铺前路。公孙胜与三阮四个推三辆车随后,做第二拔上路,晁盖、扈三娘与吴用三个推两辆车儿最后赶来。
路上行了几日,扈三娘、晁盖与吴用三个都不曾进路旁酒店打尖,都是吃自带的干粮酒水。到了黄泥岗边来,循着记号先找到几个藏车地方将车藏了后,方才转到安乐村来。
白胜早在村口接住晁盖、三娘并吴用三个,只道其余人等都已在家中聚齐。当下白胜引了三个到了家中,只见那白胜家中却是:泥墙草顶蔫纸窗,家徒四壁黑炕毡。梁上鼠蚁蛛网密,后院蛇虫青草结。
白胜家中只有草房三间,他与浑家李氏自住了一间,另外两间,一间安排了公孙胜与三阮,已是甚挤,晁盖、吴用与三娘只得住最后一间。
当夜白胜自去买了酒食回到家中,各人饱食一顿后,三娘吩咐早早安歇,明日好干大事,各人都将就歇了。
三娘在后院打井水擦了脸,洗了脚来,到了草屋内时,只见吴用占了草铺最左边,已经和衣先睡了,料想这几日赶路辛苦,他一介文弱书生也甚受。晁盖占了中间位置,却还坐着并未入睡,看到三娘来时,低声道:“官人,要不我唤醒教授,我两个去屋外将就一夜。”
三娘脱鞋上了草铺,口中笑道:“教授已经睡了,不必再叫他,在西北军营时,多时都是这般睡的,和衣而睡不碍事,若心里没有邪念,你怕什么来?你怕就坐到天亮吧。”说罢便躺了下来,侧过身去自睡了。
晁盖见她如此,暗骂道:“晁盖啊晁盖,亏你男子汉大丈夫,难道真是心有邪念了不成?”当下心一横便也睡了下去,想想不妥,又起身将自己那口朴刀放在自己与三娘中间,方才安然躺下。
三娘并未睡着,见晁盖如此摆布,暗暗好笑,童心忽起又想逗他一回,便忽然翻过身来,低声软语道:“保正哥哥,把刀拿了,我怕割到我。”
晁盖听得那柔声细语,心头一震,急忙低声道:“刀口朝我,不会伤你。”三娘忍住笑,低声又道:“保正哥哥,说个故事与你听。从前有个书生与一女子相恋,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这天两人出游,错过宿头,在一户人家借宿,但那户人家只有一张床,那女子便让书生与她一床安歇,只是在两个中间放三碗水,对书生道:‘晚间你若翻过这三碗水时,便是那禽兽之人。’那书生自然不敢,规规矩矩的睡了一夜。第二天起来,那女子却狠狠打了那书生一耳光,你可知为何?”
晁盖道:“难道那书生暗室欺人?”三娘眨眨眼笑道:“不曾,都说了规矩睡了一夜。”晁盖道:“委实猜不到。”三娘低声笑道:“那女子打了耳光后骂道:‘没想到你连三碗水都不敢翻来,亏我如此待你,真是禽兽不如。’”
晁盖也听明白来,忍住笑低声道:“那书生可真冤枉,左右不是。”三娘忽然眨眨眼道:“保正哥哥,眼下你是要做禽兽呢?还是做禽兽不如呢?”
晁盖顿时笑容僵住,半晌作声不得,三娘暗笑一回后,方才低声道:“保正,我是作弄你的,把朴刀拿去,我们只是兄弟,不作他想,你放把朴刀在此,反倒成了那禽兽或禽兽不如了啊。”晁盖急忙听话将朴刀放了,又回来安睡,但仍是挤着吴用,都不敢靠近三娘。
三娘暗笑了一回后,坦然睡去。晁盖却半夜僵在那里,只恐夜里睡沉了,翻个身碰到身子。睡了片刻后,三娘似乎已经睡熟,那呼吸绵密均匀,扭头一看时,只见草棚破陋顶上月光照下,三娘那精致玉润的脸庞更显秀美,晁盖心中一跳,竟然忍不住心猿意马起来,当下急忙掐了自己一把,急忙紧闭眼睛,暗暗收敛心神。但眼睛虽闭了,但那身上幽兰的女儿香直往晁盖鼻中灌来,那香儿真个醉人,晁盖不知不觉之间便睡了过去。
(新书求收藏、推荐支持,感谢wongkuifung,草帽小子‰,麻衣的玲绪,大贤张角,我不吸雾霾等书友的打赏)
第六十章吴用智取生辰纲 扈岚辣手灭活口
翌日晁盖醒来时,吴用兀自酣睡,三娘却早已不见了人影。晁盖下了草铺来,转到后院看时,只见三娘早已结束停当,依旧做富贵官人打扮,却在那里使双刀练武不辍。但见:晨阳魅影如梭织,双刀流盈醉武痴。香汗满额流盼顾,花间只看一丈青。
晁盖看了一回,心头暗想:“今日要干大事,她都还早晚练武不辍,这身武艺果然不是平白而来。”又见三娘美目流盼时,想起昨晚她那声娇软的保正哥哥来,忍不住心头一动,暗想道:“她如此好武艺,难得又豪迈不羁、仗义疏财,正是好汉本色,难得又如此姿容,不同于一般妇人。此前未曾娶妻,便是怕了那些妇人成天只做水粉画眉之事,早晚又口舌啰唣。但眼下看她如此人才时,甚合脾胃,若真能娶了她,早晚一道习武,逍遥江湖,也是神仙事儿。”想到这里,晁盖陡然一惊,暗骂道:“晁盖啊晁盖,她说了只做兄弟,你竟然生出如此龌蹉念头,真是该死。”
“保正,起得也早啊。”三娘练武毕,收刀上前来时,晁盖闻声方才回过神来,口中笑道:“不及扈官人早。”三娘绰刀而立,晨曦阳光照下,更显英姿妩媚,只听她问道:“保正哥哥,有句话早就想问了,只是一直不曾有时机问来。”
晁盖爽朗一笑道:“你我之间,无事不可问。”三娘笑了笑道:“保正家中自有良田产业,富贵饱足,并不缺钱财,为何还要打这生辰纲的主意?”
晁盖道:“钱财身外之物,晁某劫生辰纲,的确不是为了财帛。”三娘道:“那是为何?”晁盖道:“一来,这些生辰纲都是梁中书那狗官搜刮来的不义之财,劫了均分给左近贫人,也是劫富济贫,出口恶气。二来,因此事能结识这许多兄弟来,晁某万分高兴,看众兄弟如此热心,晁某自然赴会,不可教众兄弟冷了心。”
三娘自言自语道:“原来只是为了劫富济贫和兄弟义气。”跟着又问道:“但假若这趟之后,被此案牵连,让保正丢失家业,可会后悔来?”
晁盖笑道:“莫说家业,便是身家性命也可交托众兄弟,有甚后悔的?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只讲信义二字,除此旁的都不打紧。”三娘微微颔首,若有所思。晁盖又问道:“官人,晁某倒是想知晓,为何官人一介女儿身,却也参与其事?”
三娘笑道:“问我啊?现下不是闲话之时,时辰不早,先做大事要紧。我这便去唤众兄弟起来,早作准备。”跟着从怀里掏出一包蒙汗药来,递上去道:“这是我配置的蒙汗药,比一般的要好,待会儿可用。”
晁盖应了声,接过那药来,见她笑颜如花,想起昨夜那笑话,忍不住上前低声道:“昨夜睡得如何?”三娘一愣,随即笑道:“保正哥哥,你该洗澡了。”说罢也不理会目瞪口呆的晁盖,一扭头径自去了。
少时,众人都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