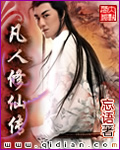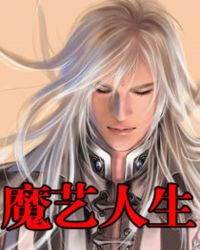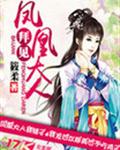明末有钱人-第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笑了一阵,忽然想到一件事情,便对姬庆文说道:“姬大人,你知道此次老夫受诏回京,为何却要到专程苏州来寻汤若望教友?”
“这我怎么知道?”这是姬庆文的实话。
徐光启说道:“就是方才姬大人说的《几何原本》和《农政全书》两部书。这前一部是我翻译自利玛窦神父那里得来的原本;后一部,则是老夫融合中原和西洋农业技术,编纂的一部农书。这两部书,乃是老夫半生心血,因此想要托付给汤若望教友,将其排版印刷、刊行后世。”
徐光启顿了顿,喝了口茶,又接着说道:“不过既然老夫今日有缘见到姬大人,又知姬大人对这两部书的意义了若指掌,因此想要将这件大事拜托给姬大人。不知姬大人愿意不愿意帮我?”
姬庆文欣然应允道:“那是自然。可惜我现在织造衙门里财政略显紧张,没法马上排版付印。不过不要紧,待我财政略微宽裕,便立即请能工巧匠刻字印刷,保证让徐先生的大名流传千古。”
徐光启听了高兴,摆手道:“老夫的名字流传也好,不流传也罢,没什么了不得的。就是这两部书关系重大,若是推行天下,便能多养活亿兆黎民,这才是造福百姓的大事。”
他们正说话间,忽从门外传来声音:“汤神父,久等了,我到了。”
第〇六九节 海商王郑芝龙()
众人听这声音极为爽朗,显然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都扭过头去,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张望。
只见门外走来一人,年纪不过二十多岁,长得英姿飒爽、潇洒倜傥,只有脸色略微有些发黑,看上去似乎不是那种稳坐书斋的读书人。
此人大步流星走到中堂之内,朝姬庆文、徐光启、孙元化等人团团一揖算是打过招呼,便又伸手招呼身后的几个从人:“来啊,别愣着了,都抬上来吧。”
说罢,就有八九个下人,各自抬了一只二尺见方的箱子走了上来,将箱子放在地上,便又听命退了出去。
汤若望租用的这处院子本就不十分宽大,这么多箱子摆放进来,便已占用了中堂三分之一的面积。
姬庆文是个好奇心强的人,见这些箱子分量不轻,便开口问道:“这里面是什么宝贝吧?”
那年轻人也是个开朗人,并不认生,笑着答道:“当然是宝贝了,是汤神父让我从海上运输过来的。”
说着,他便随手打开一只箱子,介绍道:“这是原本的《圣经》,每箱足有二百本,一共五只箱子,就是一千本,给汤神父传教用的。”
他又打开一只箱子,见里面金光闪闪的,便说:“这是六做西洋座钟,还是会转动发声的。这玩意儿可是稀罕物,我一共带了两箱一共十二台。”
“至于这箱,则都是些新奇的小玩意儿。”说着,这年轻人又打开了一只箱子。
姬庆文探头看去,只见箱子里面五花八门——有几颗玻璃弹珠、有几只小锡兵、有几套洋娃娃——活像批发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便宜货,然后出来练摊的。
汤若望见了,却不甚高兴,埋怨道:“我让你送些《圣经》来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带这些东西?”
那年轻人一笑道:“神父是个中国通,这种事情还不知道吗?汤神父这样传教实在是太慢了,要是能说服一两个大地主信教,再让地主叫自己手下的佃户信教,那只要弄成一次,就能有发展几十、上百的信徒,不是事半功倍吗?那怎么能说服地主老爷信教呢?先送一座钟进去,那地主必然是会好好听汤神父传教的,以神父的教义,十有八九就把他给说服了。”
汤若望立即斥责道:“尼古拉,你这想法是谁教你的?我这样就算传教成功了,那新的信徒,信仰的也是座钟而不是上帝。至于让地主叫佃户信教,那也是一种强迫,天父知道了,是要降罪给我们的。”
那年轻人赶紧低头诺诺连声地认错,脸上的神色却还有几分不服气。
姬庆文却道:“老汤你也矫情了吧?我看这位‘尼古拉’兄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很多事情,你只有先成功了,才有选择成功方式的余地,难道不是吗?”
那年轻人听了这话,立即喜笑颜开,附和道:“对对,这位说话中听。”他看了一眼姬庆文,问道,“却不知这位教友尊姓大名?”
姬庆文道:“我可不是你的教友,只不过是汤若望神父的朋友,过来看看他罢了。”
那年轻人听了一怔,立即拱手道:“原来如此……哦,对了,在下圣名‘尼古拉’,汉人名字叫做郑芝龙,表字飞黄。”
郑芝龙!
这又是历史上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当然了,郑芝龙的名气固然不小,可他的儿子名气比老爸还要大,就是从那位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国姓爷郑成功。
然而现在郑芝龙自己也不过二十来岁的年纪,他儿子郑成功就算已经出生了,也最多是在忙着吃奶罢了,还不是他大显神威的时候!
于是姬庆文两只眼睛若有所思地在郑芝龙带来的箱子扫视,忽然俯下身子拿出一样物件,惊呼道:“哟,望远镜啊,没想到这里还有这种东西。”
郑芝龙见姬庆文手中果然捏了一个半尺来长、碗口粗细、可以伸缩的金属筒,便赞道:“姬爷真是见多识广,居然连望远镜这样东西也认得。”
姬庆文含笑不语,那边的孙元化却来帮腔:“那是自然,姬大人耳目轻灵,什么事情不知道?”
“大人?这位爷居然还是位大人?”郑芝龙惊问。
姬庆文嘴角得意地一扬:“什么大人小人的?我就是个替皇上织布的呗。”
郑芝龙是个聪明人,立即品出姬庆文话中三味,忙问道:“看大人的年纪,又是姓姬的,莫非是苏州织造提督老爷?”
姬庆文含笑点头道:“就是在下了。”
不料郑芝龙一个一米八多高的汉子,居然立即趴跪了下来,连磕了几个头:“小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没有认出姬大人来,真是罪过。”
他这行动十分突然,就连姬庆文见了,也吓了一跳,慌忙将他扶起,说道:“你何必如此,有话好好说嘛,这样下跪磕头,不怕膝盖肿、脑门疼吗?”
郑芝龙站直了身体,个头比姬庆文要高出半个脑袋,口气却十分谦恭:“姬大人既是织造提督,那就是小人的衣食父母,只要您老手稍微松一松,我就吃穿不尽了。”
姬庆文满脸的疑惑:“苏州城里,就六百多个匠户织工指着我吃饭,莫非你也是个织工?要么你家里有人是织工?”
孙元化似乎对郑芝龙十分熟悉,笑道:“姬大人都想到哪里去了,他郑芝龙怎么会是织工呢?他是个跑船的,您是苏州织造,那还不捏着他的命 根子嘛!”
郑芝龙是明末有名的大海商,这一点姬庆文是知道的,至于郑芝龙为什么会有求于自己,那姬庆文就不太清楚了。
看着姬庆文一脸懵逼的表情,孙元化又掩嘴笑道:“看来是这个郑芝龙之前烧香没有到家,还没从姬大人这里拿到过勘合,因此姬大人到现在才认识郑芝龙吧?”
郑芝龙却道:“拿到过的,拿到过得。我上个月还拿到过苏州织造衙门摊派的勘合呢!”
“勘合?”姬庆文脸上懵逼的表情更重了,“什么是勘合?又同织造衙门有什么关系?”
他这话一出,这种懵逼顿时传染给了孙元化和郑芝龙两人,用同样的懵逼表情望着姬庆文,眼神中似乎在说:“你不是在装傻吧?”
还是徐光启年纪最大,也最老成一些,将海商、勘合、织造衙门之间的关系,细细讲给了姬庆文听。
原来是大明朝对海外贸易实施“海禁”,采取的是有限开放政策,无论是明朝人、还是外国人,是不能随意靠岸买卖的,想要从事交易,就必须持有“勘合”。
到了天启、崇祯年间,海禁已十分松弛,没有“勘合”一样可以进行海上贸易,但这种贸易只能在广东漳州月港进行,交易额受到限制,交易行为被所谓“十三行”垄断,还要向海关缴纳关税,因此海商每次交易的利润一大半都要拱手让人。
可若是交易的时候手持“勘合”,那就是代表外国过来进贡,这样就不仅可以在月港之外的泉州、宁波等处贸易,不用经“十三行”的中介盘剥,交易数额不受限制,且关税也只是象征性地支付一些罢了。
因此,一张“勘合”在海商那里的价值,堪比黄金百两。
而海商想要得到的“勘合”,首先是要朝廷礼部签发,然后再分派给沿海各地有司衙门。具体到南直隶这里,则是分别派发给江宁、杭州、苏州三大织造——每个织造衙门一年各有二十张的定数——再由织造衙门自行决定派发给哪个海商。
所以说,有了这样的海外贸易制度,手里掌握了“勘合”的织造衙门,自然就掌握了海商的经济命脉——郑芝龙口中的“衣食父母”四个字,竟没有丝毫夸张。
第〇七〇节 价格翻倍()
姬庆文不是笨人,又是个开了上帝视角的穿越者,听徐光启简简单单地介绍了一下,便弄清楚了“勘合贸易”的来龙去脉。
可郑芝龙手里的勘合确实不是从姬庆文手里分发的,于是他便问道:“郑船主,你的勘合有没有带在身边,我想看看。”
郑芝龙一面从怀中掏出一只皮夹子,一面试探着说道:“姬大人,像我这样的小海商,一整年也不过弄到一两张勘合而已。可别是假的吧?”说着,便从皮夹子里取出一张黄纸,递给了姬庆文。
姬庆文也是头回看到勘合原件,并不能分出真假来,可勘合之上礼部大印下面盖着的苏州织造衙门关防大印,他却是日日接触的,真假一目了然——果然就是用那颗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印章盖下的。
“这就奇怪了。”姬庆文倒吸一口冷气,“这勘合上的织造衙门大印是真的没错,落款的日期也是上个月,可我赴任织造提督之后,就没有签发过勘合啊。郑船主,你这张勘合,是从哪里得来的?”
郑芝龙伸手取过勘合,又一丝不苟地折叠好,放入皮夹、揣进怀里,这才说道:“不怕姬大人怪罪我。这勘合并非是我从织造衙门里拿来的,而宁波一个买办那里买的,花了我三千两银子呢!”
“真是莫名其妙。”姬庆文蹙眉道,“这段时间织坊绸缎产量高,入库、记账、销账,无时无刻不要用到这可大印,绝不会遗失的啊!”
还是徐光启老谋深算,说道:“记得太祖洪武年间,出过一起‘空印案’,是地方官员为了贪图便宜,故意带了空白文书前去户部销账,待对准了数字之后,再加盖印玺。依老夫看,勘合之事,似乎同‘空印案’情不同而理同……”
“好啊,我想明白了!”被徐光启这一开导,姬庆文已是茅塞顿开,“是郭敬这小子在这里头捣鬼!他拿了勘合,盖了织造衙门的大印,却空着日期又不移交给我,至今还在私自贩卖,这算盘居然打到老子头上来了!”
这几句话,说得徐光启和孙元化深以为然,不住点头。
郑芝龙却有些惶恐,问道:“姬大人,那这张勘合还作数吗?请你看在汤神父和这几位教友的面子上,别给我没收了啊。”
姬庆文摆摆手:“你放心好了。这几位面子大,别说给你没收了,就是你没有,我也要送你几张勘合。可惜了,我现在手里可是一张也没有……”
郑芝龙听了高兴,立即拱手作揖道:“大人一时不知情形,被郭敬偷了个空罢了。可礼部勘合是发给织造衙门的,又不是发给他郭敬的,待到明年,大人手里不就又有了勘合了吗?到时候,大人多赐我一张、两张的,我就受用不尽了。”
“那你放心,我给你留着好了,到时候发了大财,你可别忘了我的好处……”姬庆文一听其中有利可图,眼中立即放出银光,就连嗓音之中也回响着铜板撞击的声音。
那边徐光启提醒道:“大人,你年纪轻轻、前途无量,可别为了这点针头钉尾的小利,就犯了国法啊!”
姬庆文苦笑道:“徐大人,我哪还有什么前途啊?要是现在找不出将绸缎销售出去的门路,那我这织造提督也就坐不稳了。我想着既然这勘合值钱,那我干脆卖了,好歹也换个一两万两银子,给皇上交差。”
郑芝龙没有听过刚才他们的对话,便也不知道织造衙门进贡绸缎滞销的事情。
可他一听这件事情的本末,立即拍着大腿叫道:“哎呀,姬大人怎么不早说!这么多绸缎,何必一定要卖给苏州商会呢?全都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