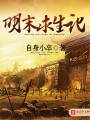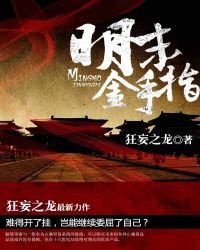明末之虎-第61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难道说,现在的朝廷已到了岌岌可危,形如累卵的地步,才让徐高这般急切到失态了么?
“徐公公,不必如此,快快请起。此处人多眼杂,不是说话之地,你且随本王入客厅说话。”李啸一脸凝重,上前一步,从徐高手中拿过圣旨,又伸手虚扶起徐高。
徐高涕泣起身,哽咽着抹去泪水,便跟着李啸直入客厅而去。
在客厅中,李啸快完看完圣旨,脸色顿是愈发凝重,拿着圣旨的双手都是在微微颤抖,最终他长叹一声,放下圣旨,一语不发。
“唐王,现在流寇出动五十万大军,已然攻占山西、宣府、以及北直隶大部,我大明官军连战连溃,即将迅速合围攻打京师,而外地兵马皆未回援,若唐王再不立即回保京师,则老奴只恐,只恐……”
徐高说到这里,已然说不去了,两道浑浊老泪,又夺眶而出。
李啸冷冷地看着徐高这般作态,心下可谓五味杂陈。
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会发生,那么它就几乎一定会发生。——《墨菲定律》。
自已最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
流寇刚刚建国,未曾稍歇,便立即调集大军,全力东攻,那些腐败无能的明军,在流寇这样生猛无比的攻势下,自是一溃千里,连接地丢城失地,终于让流寇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便从陕西打到了京师。
这样看起来,流寇的攻势,倒是与真实的历史完全一致。
而更令人无语的一点是,在这个自已穿越而来的世界里,流寇大举东攻,一路横扫至京师的时间,比真实历史上,反而提前了大半年。
这可真是完全出乎自已预料的事情。
说起来,对于崇祯皇帝,李啸的感受十分复杂。
想当初,自已只不过是个村野猎户,投军后凭自已努力,一步步向上爬。从百户、千户、指挥使、到总兵、赤凤伯、东海侯、唐国公、平辽王,直到现在成为明朝亲王的唐王兼太子太傅,这一长串闪耀的爵衔,虽然皆是自已的一路奋斗所得,但更是那个朝堂上的天子崇祯,对自已的欣赏提拔,才让自已在十余年的时间里,终于从一介毫无地位的乡野草民,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明亲王。
更何况,崇祯为了笼络自已,非但给了自已这般荣耀爵位,还先后把鲁王郡主以及亲生女儿坤兴公主嫁给了自已。现在的自已非但是大明亲王,更是帝王驸马,这身份之尊荣显贵,堪称大明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独此一人。
虽然在自已一路发展过程中,崇祯也与自已闹过矛盾,更曾因为台湾的归属权问题,还与自已兵戎相见。但归根结底,这些矛盾皆已过去,现在旧事重提,实无意义。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更何况,崇祯对于维持胆朝这个烂摊子,对于防止局面进一步恶化,还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故而,于公于私,自已都不能坐视不管。
”徐公公,您放心吧,本王虽不才,愿率亲兵,往救陛下!“
李啸直视着徐高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晰地说出这句话。
第六百三十三章 皇上有难 我当亲救()
李啸这句斩钉截铁的话,让司礼监太监徐高,瞬间瞪大了眼睛。
真没想到,唐王的表态这么快,又这么有担当。
他原本以为,现在贵为唐王,又几乎是完全独立状态的李啸,对于这道近乎哀求式的谕旨,必定会内心鄙薄,然后在表面大力叫苦,不停强调困难,推三阻四地不肯撤兵回国。却没知道,李啸这位曾经反叛过朝廷的重臣,竟会答应的这般爽快。
更重要的是,李啸贵为亲王,竟提出要亲去救援,这般置生死于度外的举动,足见忠义可靠,更显赤诚丹心。
一时间,徐高极其激动,几乎想要向李啸伏拜而谢了。
只不过,他又在瞬间想到,现在久处辽东的唐军,即使想要立刻撤走,却又谈何容易。
“唐王,听闻贵部皆在辽东,水师船只尚在山东未曾回返,那要撤兵的话,是不是也只能暂时等待?“徐高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眼下大规模撤兵,确是不及。但本王可以先亲率精锐骑兵,从营口搭乘现有船只回返,希望无论如何,也要把皇上给救出京城出来!”李啸目光灼灼,一字一句地说道。
望着徐高十分迷惑的神情,李啸轻叹一声,又继续说道:“徐公公,你从海路来时,流寇便已从宣府与北直隶两路合击,直取京师,京师的局面,已是形如累卵,岌岌可危,如何还来得及等本王全部安排妥当,再行撤兵回国。若要等到我唐军,全部从辽东搭乘船只撤兵回国,那京城只怕已被流寇攻取多时了!于今之计,只能是由本王统率亲兵,先行赶回京师,无论如何,要先把皇帝从京师救出,再作计较。”
徐高终于明白了李啸的意思。
原来,现在李啸已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在流寇攻势这般急切,如此凶猛的情况下,现在的京师,已是根本不可能保住的了。
现在的唯一可行之计,便是趁着敌人尚未攻城,好歹把崇祯皇帝这个大明帝国的首脑,赶紧从京城中救出,从而为整个大明王朝留住重新振兴的根本。
徐高想到这里,心下喟然长叹。
不过,他略想了想,又试探着问了一句:“唐王,咱家在想,流寇行动如此之快,我等纵然立即赶回,万一京师已被流寇围住,又当如何?”
听到徐高这句问话,李啸的脸色,顿是愈发凝重峻刻。
李啸知道,徐高所说的这种情况,可谓是最坏的状况了,而且极有可能会发生。
而一旦这种最可怕的事情发生,那么,哪怕是诸葛重生,孙武再世,亦无能为力了吧。
李啸没有立即回答,只转过头去,目光投向遥远的窗外。许久,才缓缓回道:“尽人事,听天命。纵是如此,本王亦要亲往救之,以期尽最大努力,把陛下从京城救出。此言既出,断无悔矣。”
徐高听到这里,对李啸顿是愈发佩服,他再不多话,一掀襟摆,有如参见皇帝一般,跪倒在李啸面前。
“唐王如此忠肝义胆,咱家叹服之至,请唐王受咱家一拜!
“徐公公何必如此,速速见身。”见徐高这般伏地跪拜,李啸急急上前,将其从地上搀扶而起。
“那,咱家请问,唐王打算何时率兵出发?“徐高从地上站起来后,又赶紧追问了一句。
”今天准备,明天一早就出发。徐公公远来辛苦,今天就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就随本王一起返回京城吧。“
”好,那咱家先行告退。“
徐高退下去后,李啸立刻派人去叫田威与刘国能两名大将,前来客厅议事。
很快,二人来到客厅,李啸也不多与二人废话,立刻开门见山进入正题。
二人听了李啸对时局的简介,皆是大吃一惊。
而接下来,听李啸他自已的打算后,二人更是目瞪口呆。
“李大人,万万不可啊!现在局势这般险恶,京师危如累卵,唐王乃是万金之躯,更是一军之主,如何可以身犯险,定要亲去搭救皇上!在下虽无能,情愿身代唐王,立即赶往京城去救皇上。”田威目光急切地望向李啸,脸上有难以言说的焦灼。
“是啊,田镇长说得对。唐王乃是一军统帅,是全军上下的主心骨,万万不可以身试险,亲自去救那皇帝。只要大人你下令,国能愿立率精锐军兵赶往京城,一定把皇帝给救出来。”在一旁的刘国能,亦是急急插话,决不同意李啸前自带兵前去。
李啸目光复杂地打量了一下二位爱将,微叹一声缓缓回道:“二位,本王刚被封为大明亲王,皇上有难,安可不出手相救。况且解救皇帝一事,既是臣子本份,又系事关重大,万万不可有失,此事本王若不亲历亲为,亦实难放心。故本王思来想去,只得由本王亲率兵马前去京城,方是最为妥当。至于辽东之地,尚需二位合力驻守,且待船只从山东装运粮食与辎重回来,再相机退兵回国。此事亦是干系重大,事为我军根本,万万不可出错,就全靠二位尽心了。”
田威与刘国能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眼神中皆满是无奈。
田威犹豫了一下,又问道;”唐王,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赶到了京师,那皇帝去不肯离开京城,硬要在城中死守,又当如何?“
李啸脸色凛然,沉声回道:“若如此,这般紧要关头,本王当采取断然手段,定要将皇上从京城撤走,这事绝无商量。”
田威与刘国能还欲相劝,被李啸摆手制止。
”不必多说了,本王心意已决,今天准备妥当,明天便要出发。其余诸事,请二位听本王安排。“
李啸说完,接下来开始立即安排各类重要事情,大致为以下内容。
1、李啸明天带亲随的五百名护卫骑兵,南下营口,从那里搭乘营口港处的剩余船只,径直驶往天津河间府大沽港。
2、辽东这边一切事务,暂由田威全权处置,假装与清廷继续进行谈判,然后暗中组织撤兵。
其中海城与营口的兵力,全部撤回山东,镇远堡的兵力,则全军退回宣府北路金汤城。全军在撤退时,需得将两座城池彻底毁为平地,附近的乡野城镇,也全部加以摧毁,总之不可留下任何物资或人口以资敌。
3、等从山东返回的船只抵达营口后,仅用一半船只运送自家军兵退回山东。另一半船只,则去装运山海关的祖大乐部与宁远城的吴三桂部。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李啸考虑现在流寇进军极快,那处于京城北面的山海关总兵祖大乐部,以及宁远总兵吴三桂部,估计是既来不及入京城救援,又没办法从流寇与清虏的夹击下逃脱,为防止其投降清廷或流寇,需得派出至少一半船队,紧急前往该处,协助其从海上撤走。
李啸确信,只要自已行动及时,那么,来不及撤走的祖大乐与吴三桂,一定会相当感激自已的及时救援。
田威与刘国能二人,大声应命,随后李啸复与他们商谈了一些细节,二人便告退而去。
次日,李啸亲率五百护卫骑兵,又带上了太监曹化淳以和徐高一拔人,一行人从海城直下营口,再从这里登上仅有的数艘船只,径往河间府驶去。
忧心如焚的李啸明白,现在的自已,其实是在与时间赛跑,一定要尽力赶在北京被流寇围城之前到达,方是唯一的希望。
李啸忽然觉得,现在的仅率亲随骑兵,便径往京城去解救皇帝的自已,倒有点象三国时的关云长,无惧生死,单刀赴会。
只是,自已现在纵然全力而行,又能赶得上现在局势的变化么?
李啸不知道。
他的担心,很快就变成现实。
就在他们在海上疾疾而行,一路南下,刚刚到了大沽口港时,流寇的大军,终于从南北两个方向,把整偌大一座北京城,牢牢地围在其中。
流寇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京城围得铁桶一般,至此,崇祯皇帝再无脱逃的可能了。
早在前些时日,大顺军进抵居庸关,总兵唐通和监军太监杜之秩投降,号称天险的京师“北门锁钥”,便在大顺军面前敞开了。
大顺军在一片顺利的局势下,快速逼近京师,让明廷蒙上一片阴沉的气氛,崇祯和他的大臣们,顿时陷入了焦头烂额又束手无策的境地。
在流寇快速向北京进军之际,崇祯与朝臣们在建极殿中,紧急商讨对策,便令崇祯大失所望的是,这些往日里高谈阔论互相攻讦的高手们,一个个噤若寒蝉,但相顾不发一论矣。
皇帝故作镇定,按照常例召对考选诸臣,以抵御满清和大顺军以及筹措兵饷为题,让他们挨次奏对。
说起来,在这厄运临头的时候,他做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官样文章,实在是毫无意义,只不过是借以安定人心罢了。然而,在这紧张万分的时刻,就连他本人,那内心的无限恐惧也再无法掩饰了。
朝中每个大臣都清楚看到,皇帝在听取诸臣奏对时,已经完全心不在焉,根本就未能听进几点。
“上或凭几而听之,或左右顾而哂之,是日帝笑语颇失恒度。或斟茶,或磨墨,皆亲手自为之。如忽忽无绪然,非平时庄涖景象也。”
崇祯明显表露的焦灼与恐惧,让整个朝堂顿时更加骚然不安。
奏对还没有结束,这时的内官太监王承恩,急急跑入殿中,向皇帝递进一件密封文书。
朱由检打开一看,立刻面无人色。
他大叫一声,竟在龙椅上,昏厥了过去。
见到这番骤变,参加奏对的朝臣们面面相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