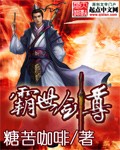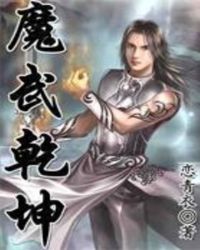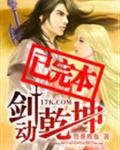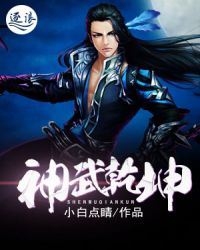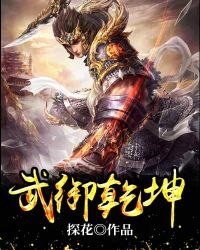莽乾坤-第4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换岫忠⊥罚W愿锌灰选�
当所有国子监与咸安宫的学生都把试卷交至殿陛之下,适才还风和景明的太和殿前,突然不知从哪里刮过一阵狂风,几名礼部的官员慌忙去追赶那些被风刮走的试卷。
“轰隆隆——”,“轰隆隆——”
一阵隆隆雷鸣之声仿佛从紫禁城地底下发生,就似十几万个巨大的铁球在铁板上来回滚动一般,瞬间,紫禁城一阵地动山摇,宫殿撼动,屋瓦滚落,一阵劲风吹过,灯笼纸张乱飞,也不知从哪来的灰尘,遮天蔽日,天空瞬间如墨染就,近在咫尺的日晷与嘉量都看不到了,紫禁城顿时变成黑暗世界。
殿陛之上,早有侍卫死死护住宣光皇帝,地动山摇中,一众大臣跟在皇帝后面,踉踉跄跄、东倒西歪地都跑到了太和殿跟前的广场上。
国子监的学生,发一声喊,四散奔逃,狂风中,桌子、人影乱晃,叫成一片。
咸安宫的学生也乱了分寸,狂风黑暗中,一个声音突然喊了起来,“稳住!稳住!我是咸安宫总学长肃文,大家听我命令,站立原地,稳住,稳住!”
几个咸安宫的官学生却是收摄不住心神,刚要拔脚,冷不防撞在一个人身上,“啪啪”两个耳光,瞬间清醒过来,“跟着我喊,咸安宫,稳住!”肃文大声叫道。
“咸安宫,稳住!”
“咸安宫,稳住!”
起初,只有几个人的声音,渐渐地,图尔宸喊了起来,麻勒吉喊了起来,海兰珠喊了起来,雅尔哈善喊了起来
“稳住!稳住!”
咸安宫九十名官学生的喊声高亢嘹亮,齐齐回荡在紫禁城上方,黑暗中,肃文不断在咸安宫的行列中穿梭,却见咸安宫众学生齐心高喊,昂然挺立,气势如虹,任狂风乱吹、黑暗漫布!
苏洵权书?心术篇讲道,“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
这是张凤鸣最为强调的,肃文也极为推崇。
狂风如长龙一般,带风而过,天空慢慢显露出青色来,仿似黑夜弥漫的紫禁城又重见天日!
此时,太和殿前的广场上,已是狼籍一片,掀翻的桌椅,吹掉的纸张,碰碎的砚台,应有尽有,那一众国子监的学生虽有坚守原地者,但更多地四处逃窜,三五成群聚于一处。
再看咸安宫阵列,却是人员齐整,桌椅齐全,众学生长身而立,面目庄严,挺胸抬头,精神抖擞!
宣光帝把一切尽收眼底,他一把打掉还扶着他的魏佳章的手,“放开!朕,难道还不如朕的这些官学生?!”
几位亲王及上书房大臣都陪侍一旁,此时见狂风已过,天晴日明,不禁都恍如隔世一般。
那郑亲王却指指咸安宫阵列,笑道,“王学正,还比吗?”
康亲王杰书笑道,“还比什么,高下立见。”
礼亲王济尔舒看看正微笑不语的端亲王宏奕,却是沉着脸不说话。
上书房次辅鄂伦察笑道,“呵呵,有士气,这帮官学生,依老夫看,竟似行伍一般!哎,适才那个总学长叫什么名字?”
“肃文!”端亲王宏奕笑道。
“报——宫殿俱无倒塌,无人员伤亡,太后、皇后俱已在殿外,帐篷已经搭起。”
“报——城内房屋,倒塌者不计其数,城墙也有几十处塌陷城内多处地面裂成隙口”
不断有内监跑过来禀告,宣光帝并众位上书房大臣都静静听着,看来,宫中问题不大,受损严重的是宫外。
也不知家里怎么样了?房屋要不要紧,关键是人不要受伤,肃文心里默默祈祷,保祐家人平安,保祐全城的老百姓平安!
国子监的学正王延年在侍卫及内务府的笔帖式帮助下,慢慢收拢起队伍来,国子监的学生重新又扶起桌椅,整顿纸张,太和殿前,又恢复了震前的样子。
但人心的倾向,却再也回不去了。
“着户部、工部、钦天监尽快查明地震范围,上报详细灾情,尽快制定救灾章程。”事先已作好安排,此时倒也不致于手忙脚乱。
“启奏皇上,三场课目已考两场,微臣请示皇上,剩余一课目”礼部满尚书贵祥见宣光帝把灾后缮后事宜布置下去,遂上前请旨。
他还没讲完,那国子监监正王延年就走上前来,打断了他,“臣启奏皇上,最后一课极为重要,四书五经与诗赋本属基础,策问才是考论人才的关键,臣请皇上恩准,继续考试!”
宣光帝冷冷看了他一眼,“既然,你认为策问最重要,那就——考,考得要令人心服口服。”他转身一看贵祥,“依朕看,原来的考题就作罢吧,既然王延年说,策问,才是考论人才的关键,那就以震灾缮后为题吧!”
国子监与咸安宫将来都要外放作官,策问本意旨在考校理政问政本领,宣光出此题目却应是应景,令人不得不信服。
肃文提笔在手,却是快速书写起来。
“皇上御极以来,孜孜以求,上合天心,下安黎庶,然,地震乃自然变化之理,大地运化之果,无关天人感应,无关政治修为”
这第一段是表明地震就是自然现象,警告某些人不要东拉西扯,动不动要皇上搞什么罪己诏!
“户部、工部宜迅速查明震后损毁,妥善拟定救灾赈济章程”
“宜拨银若干,开设粥厂,请医买药,赈济兵民”
“地震中损毁房屋无力修茸者,压倒人口不能棺殓者,需拟定具体补助标准”
“宜令富裕官员及商铺,出资救灾,使贫困之家,早获宁居”
这是针对当前地震的具体救灾措施,肃文又看了看云彩快速散去的天空,提笔又写。
“大灾之后有大疫,需提早预防,可选派太医院精通医术者数十名,并药铺志愿者,前往各受灾处提早防疫”
“震中受灾之全部百姓及商铺,蠲免全年钱粮,视明天生产恢复状况,再行议定”
“大灾之后,须防有人趁机作乱,传播邪道,蛊惑人心,宜令各级地方官佐,严加防范”
“好!”那礼部满尚书贵祥竟是一拍桌子,“素闻此人有大才,想不到不仅诗作得好,策问竟也是作得花团锦簇,此为经济之道,治国之道,这人有济世之才!”
他却没有放下手中的试卷,继续大声读道,“借此地震之机,应思虑施政之弊端,则地震不为祸患,反为革新鼎盛之良机,宜将先前之弊政尽情洗刷,一是各级官吏苛派百姓,税负过重,二是刑狱不公,积案不办,三是官员贪墨成风,索贿受贿,”
他越读声音越小,站在一旁的一礼部侍郎笑道,“这几条,历朝历代都有,也不只我大金一朝,不过,此人不只精通经济之道,胆量也是非凡!”
“唉,能写出这样诗来的学生,胆量小就说不过去了!”贵祥顺手把诗与策问一起递给侍郎,“如何选取,说说你的意见。”
“我看,诗与策问俱属一流,依大人意见为准。”那侍郎又把球踢了回来。
“诗嘛,皇上当场夸赞,当然应属第一,这策问嘛,”他顺手拿起国子监等学生试卷,“看看这些,腐儒之论,寻章摘句,离题万里,这些人,都是诸葛亮说的小人之儒!”
他默然沉思良久,忽然睁开双眼,“那日季考,皇上都说过,难道朕还不如这些官学生,难道我堂堂礼部尚书,还不如一个官学生,第一,肃文第一!”
他拿起笔来,郑重地圈了起来。
“皇上也不是什么昏君,此篇策问字字珠玑,字字椎心,传之朝堂,也必有公论的!”
可是,贵祥还是猜错了。
他猜出了开始,却并未料到结局。
国子监与咸安宫季考名次排定后的第二天,宣光帝对肃文的策论大加赞赏,并将策论发至上书房大臣并六部,第三天,他竟亲自召集上书房、六部、九卿、詹事、科、道等满汉官员,于左翼门前传谕,将自己的召诣与肃文所写六大弊端一并传达。
宣光帝严厉警告各级官员,“朕于宫中勤思救灾之道,缮后之道,臣工们务期借此地震之机,洗除积弊,痛改前非,存心爱民为国”
“咸安宫官学生肃文所上之策问,切中时弊,发人深省,自上书房大臣并总督巡抚,当常思己过,对镜自查,”
“奸恶之人,凡属六条弊端其一者,如自圣旨颁布之日起,仍不知改悔,一经查出,国法俱在,绝不饶恕!”
一时,肃问之策论洛阳纸贵,传遍京城,又经邸报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
第45章 卢沟夜月()
成功预测出地震的发生,并指出地震与天人感应无关,宣光帝亲自下召颁发肃文的策论,不但皇上不需再发罪己诏书,避免了一场风波,而且为新学的推行增添了新的筹码。
国子监与咸安宫的对决,咸安宫无论在诗赋与策问上都高出一筹,且地震当日的表现尤其令人瞩目,新旧教育与体用之争的结论也是不言而喻。
这些日子,上书房及六部把大半的精力都用在了震灾缮后上,新学的推广只等一纸诏书全国铺开了。
这日下学后,肃文匆匆走出西华门,家里在这次地震中损失不大,医院只是坍塌了一面院墙,他本想再回肃惠中医院免费发放药品给灾民,却不知毓秀早已守候在宫门,“肃文,上马,跟我走。”
“王爷,去哪?”
“卢沟桥!”
肃文一下跨上马鞍,笑道,“王爷您真有闲情逸致,卢沟桥离北京三十里地,我们此时赶过去,正巧欣赏卢沟夜月,呵呵,要不待到天明,也看一眼卢沟晓月。”
毓秀却盯他一眼,“赏月?哪有心思?走吧,去了你就知道了,想不出办法,恐怕真要一直待到天亮了。”
二人带着一干侍卫内监赶到卢沟桥时,却正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皎洁的月光下,永定河河水如练,西山似黛,月色与银河交相辉映,更显明媚皎洁。
“卢沟桥上月如霜,古人诚不欺我也!”肃文用马鞭一指,诗兴大发。
“先别急着作诗,”毓秀也用马鞭一指,“你看那是何物?”
借着月光,肃文一瞅,只见一辆练车上拉着一根巨大的石柱,石柱很长也很粗,估摸着不轻。
不等他发问,那毓秀却解释道,“这是从房山西山大石窝运出的,这一根石柱就重达十二万斤!”
“十二万斤?!”肃文暗自惊心,但响鼓不用重捶,他马上明白了毓秀的意思,难不成是让自己想办法让这根石柱过桥?不过,这桥能承受得了这十二万斤吗?
果然,毓秀毫不啰嗦,“卢沟桥是运此石柱的必经之地,这桥,”他下马上桥,拍拍桥墩上的狮子,“是京城的交通咽喉,去年河水泛滥,将桥冲垮,皇阿玛召令工部,花了八万多两银子才修好,如何让这根石柱从桥上通过?”
月光下,他定定地看着肃文。
工部的一举一动、花费多少都在他掌握之中,眼前这个恂恂儒雅颇象个公子哥的王爷,看来并不只关心算术天文历法,他对政局的掌握看来竟是分毫不差!
“肃文,”毓秀看他一眼,以为他在沉思,“可有办法?”
“请问王爷,为何此时石柱才运到永定河岸边?如果是冬季,结冰之后从河上而过,岂不妥当?”
毓秀看看肃文,“前日早朝之时,工部尚书齐勒泰提出,营造孝陵石牌坊的石柱已运到,却无法过桥,只能呈奏御前,想请咸安宫的教习与学生帮着拿个主意,皇上当场没有表态,今儿我才带你过来看看。”
“这是工部在使坏!”肃文道,“为什么早不运晚不运,偏偏等到推行天文历法算术时才运到?未雨绸缪,工部冬季就应趁河水结冰运过河去的。”
那齐勒泰是张凤藻的门生,与郑亲王交好,也与礼亲王相厚,难道是他跳出来给人当枪使?不过,三人到底是谁在反对新学呢?
毓秀道,“六叔也认为这是有人成心阻拦,想借此再作文章,但现在,新学马上就要铺开,不能再有什么闪失,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顺利地把石柱运过桥去!”
两人来来回回在桥上走着,却是无人再去欣赏那撩人美景,
“造桥花费颇大,不能毁桥,那就加固桥墩,这是一法,第二个法子是从桥下过,不过,河水湍急,浑河巨浪,势不可挡,难度更大,我还是倾向于从桥面过。”肃文考虑一阵,还真无别无他法。
“工部呈报的意见也是从桥上过,但这十二万斤的石柱从桥上面过,却需要三百匹马来拉动,且不说这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