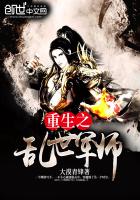南北乱世之倾国权臣--高澄传-第4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敢,郎主吩咐。”崔季舒急忙抬起头来。高澄幼时一直与他玩笑惯了,却总是笑骂戏打,何曾辞色温柔且呼之为“兄”?
“我们的濮阳郡公侯豫州既不放心关中,也不放心洛阳,既然要回来看一看,吾等自当以礼相待,不要给人家脸色看。有什么事放在心里,不要放在脸上,就怕别人不知道你知道似的。叔正兄,你听明白了吗?”高澄渐渐收了笑,看得元仲华竟心里一寒。
“世子,只怕现在贺拔岳大行台已经到了上圭。”陈元康语气凝肃。
一下子安静下来。元仲华忽然觉察到一种紧张,是临大事之前的紧张。她身为魏室公主,从尔朱荣河阴之变起,她虽年幼但听到的和经历的却不少,帝裔多难,她岂不知?正因如此,格外敏感。高澄感觉到了她身子微颤的紧张感,稍用力将她拉近身前,拢入怀中,丝毫不避讳眼前的两个重臣。
“大丞相知道吗?”高澄问道。
“豫州定然会告知。”陈元康道。
“他说是他说,叔正可曾派人给大丞相送信?”高澄转身看向崔季舒,蹙眉问道。
“按照郎主吩咐,平日不报,有大事报知大丞相。”崔季舒抬起头来,略一思索又道,“听大丞相回信中语气,恐怕回洛阳也是与侯豫州前后间的事。”
高澄似乎从元仲华身上感受到了什么,忽然低头盯上她,暗中用力把臂膀更加收拢些。
“盯着上圭,有事立刻回来报我,一定要快。此时误事,休怪我无情。”高澄语气冰冷,在陈元康和崔季舒身上目光逡巡。
陈元康和崔季舒辞去。
“你放手。”元仲华这才放开手脚用力推拒高澄。
“殿下如此性躁,是听说二弟要回来了吗?”高澄冷冷盘问。
元仲华一怔,想想才明白,刚才崔季舒说大丞相高欢要回洛阳,那想必二公子高洋也会随行。她没再说话,却缓和下来,不再推拒,似乎添了什么心事。
高澄却放开她向外面走去,只听到他身后传来的声音,“阿娈好好服侍世子妃,不许出去。”此时天色已亮,元仲华只看到他挺拔的背影。
几天几夜持续赶路,上圭城近在眼前。城外数十里,宇文泰下令驻扎。跟着的几个偏、裨将佐看骠骑将军虽昼夜无休地纵马奔驰难免面色憔悴,但是却精神矍铄,都心里暗自松了口气。
卫将军长史于谨静立一边,冷静旁观,看到一位裨将走近问道,“将军,上圭城就在咫尺,为何不入城?”
宇文泰蹙眉摇头道,“大行台恐怕早就到了上圭,但上圭却如此安静,一路过来又盘查甚是严恪,不知城中是何等情势,不必急于入城。等打探消息的人回来再说。”
又一副将恍然道,“将军所言极是。若是大行台和秦州刺史已经一同出兵去往灵州,定有来往的哨探,此时却安静得不近乎寻常。莫不是灵州处战败了?”
有人反对道,“若是战败,更不该如此安静。大行台和秦州刺史都是身经百战的大将,携手而征,岂会战败?”
宇文泰没说话,下了马,走到不远处的小溪边。一路到上圭,心里总是不安稳。若是细想起来,大行台贺拔岳亲赴上圭与侯莫陈悦共同征讨曹泥,这事是急了些,不稳妥,但细想来也想不出会出什么大事。最大不过战败而已,若不是洛阳朝堂上的几番纷争,就关中来说不过一时得失,都算不上是什么大事。他之所以不入城,就是因为侯莫陈悦并不知道他会来。因此若真是有什么事也才好应变。真入了城,情势难料,也许就成了瓮中之鳖。
这时于谨慢慢踱到溪边,又回头看看身后远处异常安静的上圭,闲聊般道,“使君看上圭异常,心中可有谋划?”
宇文泰猛然回头,盯着于谨良久,于谨坦然相对。沉默片刻,宇文泰又回头看脚下清溪,淡淡问道,“将军可有赐教?”
“赐教不敢,追随使君此心不改。难免为使君心忧,如同忧己身。只是此时使君不该犹疑,当直赴长安而去,何必在上圭城外相守?”于谨低语道。
宇文泰没回应。舍近就远,又是两处都情况不明,看似并不理智。他强按下自己心里潜藏的更大忧虑,转身看了看几天来劳碌的兵士,心里想着是就驻扎城外等消息,还是先让一部分人乔装潜入城中。这时忽听一副将大声唤道,“将军,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
不知怎么,心里一跳。偏能沉得住气,面上气静神闲,越是焦虑越要沉稳,缓缓走来。那打探消息的人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显然是急急奔回。见此情境,宇文泰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心里开始筹算。
“将军,侯莫陈悦杀了大行台!”这人声音高亢又透着嘶哑,显然是气血上涌,急火攻心。
一下子安静了。威镇关中的关西大行台贺拔岳竟然被秦州刺史侯莫陈悦杀死了?而且死得如此无声无息?这是个不敢让人置信的消息,是完全超越了宇文泰心里最坏准备的更坏局面。
“将军!”忽然有人大喝一声,“我等当杀入上圭报仇!”呼声一出,立刻一片响应。
那报信的人提刀便喊道,“走!我带路!给大行台报仇。”说罢转身便要上马。
“站住!”宇文泰眼见局面将要失控,怒喝一声拔出宝剑,“无我号令擅自行事者,斩!”
所有人都静止了,全都盯着宇文泰。有质疑,有询问,甚至有杀气。这都是宇文泰使出来的将军和兵士。宇文泰目中阴冷道,“大行台于我有恩,宇文泰誓报此仇。”这句话一出,态度暨明,气氛立刻有所缓和,将佐、兵士们都缓缓转过身来看着宇文泰,等他下文,已然是唯令是从了。
“大行台雄踞关中,以此为势,此乃岳将军一生心血,先保住关中才能自保,势尚在方可报仇。若是贸然冲入上圭,情势不明,被陷于城中,连残局都收拾不了,如何能为大行台报仇?”宇文泰口里说着,心里已经飞快地将前因后果,来往秩序梳理了一遍。
忽地想到离开洛阳前皇帝元修的话,还有到了统万之后几次接到南阳王元宝炬的密信,都是明里暗里急着平定曹泥、收服侯莫陈悦、河西流民等。洛阳朝堂尚且局势不分明,关中的事皇帝和南阳王等何以急切至此?大行台贺拔岳之死又真正是谁之过?
“将军明大义,所言极是,我等唯将军之命是从。”一个副将已经心服口服。
“唯将军马首是瞻!”
“听将军的!”
众人七嘴八舌。乱兵之中那股邪火被凝聚到了一起,形成了一股力量,控制在了宇文泰手中,只等他指哪儿打哪儿。
“上圭城内情形如何?”宇文泰问刚返回的哨探。
第53章 :几处早莺争暖树(下)()
荒村烟树,远山近溪,人丁萧索
“秦州刺史府第大门紧闭,侯莫陈悦并未出来。城内只是盘查极严,也没有任何的兵士调动。”哨探答道。
杀了贺拔岳对于关中来说是惊天大事,侯莫陈悦敢做这样的事,居然没有任何的善后和下一步举动,可见他事前并未计划周密。一是侯莫陈悦并不是有脑筋的人;二是很可能侯莫陈悦也是受人指使,因此才等待下一步的指令。
哨探好像又想起了什么,急道,“只是有两次见刺史府第派人往东边去送信。”
“何以见得?”宇文泰追问道。
“观察日久,知道是侯莫陈悦近前极重要的人。跟着出城便见往以东的方向去了。”哨探回道。
往东,大半便是洛阳。但也不排除别处。
宇文泰看了一眼于谨,此时忽然明白他为何建议直赴长安,不必死守上圭。不管成败,上圭已成定数,而长安才是真正关系全局的枢纽。
心里有了计划。不再迟疑,上马挥剑大声喝道,“听我号令,日夜兼程,直奔长安。”话音未落他已经是策马而出。
上圭城外,烟尘滚滚,宇文泰率众急赴长安,将上圭甩在了身后。
高澄起身披衣,没有看一眼熟睡中的侍妾,毫不留恋地出门而去。重重的关门声惊醒了床上的姬妾李氏,床幄间空冷,已是不见其人影,李氏心里叹息一声,又重新躺回了榻上。
在大丞相府中烦躁地四处游走。停下来时抬头一瞧,居然又走到了冯翊公主元仲华的门外。夜静得没有一丝声音,院门紧紧闭合。高澄刚要踹门而入,忽然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停止了动作。愤然转身,险些撞到身后另一人。
“郎主。”原来是府里巡夜的家奴。恭礼敬称,好奇地偷瞄一眼,又赶紧低下头,心里纳罕世子为何深夜不眠,徘徊在世子妃门外。看世子披发中衣,一副极度不满的样子,不由得又多口一句道,“小奴去帮世子叩门?”说着又看一眼那紧闭的院门。
“不要!”高澄断然拒绝却是极其委屈的语调,像是小孩子任性耍脾气。转身便走,一边走一边大声怒道,“传!传!传崔季舒来!主子忧心国事睡不着,他倒真是没心没肺!”话音未落人已经走远了。
家奴应声便赶紧跑向外面去传世子之命。
其实并没有过去几天,只是高澄自己等得心焦有些沉不住气而已。他深深明白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中之变势必涉及洛阳,甚至整个大魏。一个人沉思连连,甚至想到了宇文泰和长公主元玉英返回关中时,他也曾经追至河洛。救宇文泰于险境之中,现在想来不知道算不算是放虎归山。只看今日关中是否有变,又是如何之变。
高澄咳嗽了几声,这时恰恰门开了。抬头看时,果然是崔季舒气喘吁吁地进来了。
“郎主。”崔季舒回身关上门唤道。
一进来便是一怔,天气已和暖,这屋子里怎么忽然又燃起了火盆?让人躁热难耐。没有点灯,高澄也没有回答他。崔季舒借着火光看到他坐在往日里大丞相坐的榻上,支肘于迎枕上,手抚着额头,又像是在低头沉思,又像是睡着了。走到近前,看高澄束发,穿着宽身大袖的玄色衣裳,深夜装扮得如此齐整,不知是什么意思。
“郎主,叔正来了。”又轻声唤道。
“上圭可有消息来?”高澄没抬头,直接问道。
“没有。”崔季叔听到他声音有点黯哑,暗里仔细辨别。
“大丞相可有消息?”高澄抬起头看着崔季舒。
“也没有。”崔季舒看到他幽然闪着冷光的如绿宝石般的眼睛,眉头微蹙让人心生不忍,不由劝道,“世子也别着急”
“博陵处有什么动向?”高澄不耐烦地打断了他又问道。他站起身,忽然身子一摇晃。
“郎主!”崔季舒忙上前扶住了他。心里觉得奇怪,就好像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日日都精力无尽,突然变乖了,没了精神。觉得有点不对劲。伸手一触,高澄额上滚烫,心里大惊,竟是高烧!
“来人!”崔季舒扶着高澄,看他无力跌坐于榻上,便转身向门外唤道,他是要命人去传太医来。
“住口!”高澄怒道。他叫崔季舒来不是为了传太医,实在是为关中的事心里焦急。
然后还是有人被唤进来了。家奴刚进门,高澄便怒道,“出去!”家奴立于原地没动,只是回头看了看。
“阿奴唤谁出去?”门外竟然传来了大丞相高欢的声音。
“大丞相回来了!”崔季舒顿觉心头一喜,回头看看高澄,便急趋向门口处迎去。
“阿爷回来了。”高澄声音陡高,也顿觉身子一轻,神清气爽起来。
果然见门开处父亲大丞相高欢不急不缓,面上微笑地走进来。崔季舒行礼恭迎进来。高澄也从榻上起身急迎出来。刚要说话,忽又听崔季舒唤了一声“二公子?”语调极是惊异。说着又是行礼。紧跟着,二公子高洋已跟在父亲身后进来了。久不见面,高洋长高了好些。越发的肤色黝黑,眼睛里是和年龄极不相衬的深沉。他进来看清楚了情势,方才默默地向着长兄一礼,没说话,只是跟在父亲身后。
“阿奴在洛阳已取我代之,又因何不悦,反倒如此气急?”大丞相高欢稳健而入,昂然直上,高坐于榻上笑问道。
“上圭久无消息,实在心忧。”高澄下首而坐,坦然直陈。
二公子高洋默默在下侍立,一言不发,且低着头。
“世子忧心国事,焦虑过度,已是高热不退。”崔季舒见大丞相沉吟不语,便回道。
“既如此,阿奴打算如何应变?”高欢问道。
“若是上圭事成,便趁隙夺关中之权;上圭事败,作壁上观,以收取渔人之利。”高澄毫不犹疑地答道。
“想得如此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