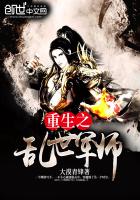南北乱世之倾国权臣--高澄传-第4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后来皇后宇文氏有身孕的消息很快就被皇帝公开地发布出来。这是天大的喜事,无形之中就冲淡了那天私下里的争执。
那一天的事皇帝绝口不提,丞相宇文泰也像是根本没有发生过这事一样。一切都看起来相安无事,甚是平静。
大丞相府里,本来还在为那天的事担心的云姜倒被皇后有孕的好消息给着实地惊喜了一回。与兼任长史的骠骑将军宇文护商量了几回,还有南乔私下里出主意,这几日时时往宫里给皇后送东西。
然而没几天,皇帝元钦在刚刚公布了皇后有身孕的消息之后就又下了明旨,赫然便是给宇文泰加授郡王爵位。这次加恩在皇后有身孕的消息之后,倒也算是顺理成章。
而最让人意外的是,皇帝居然连郡王世子一起指定赐封了。他指定的世子人选不是嫡夫人、长公主元玉英唯一的儿子、宇文泰的唯一嫡子:宇文觉。而是云姜所出的庶出幼子,是婴儿的宇文邕。
这御旨颁下,庙堂上尽是一片哗然。
宇文泰自然是辞而不受。他虽爱幼子,但和世系的传承无关。嫡子宇文觉是故去的妻子元玉英唯一所出,他绝不会弃了这个儿子重立继承人。此子虽然仁弱只要找对了辅佐之人,一定不会有问题。
皇帝加恩的诏书在皇后有孕的消息之后。显然是把宇文泰混同于一般的外戚,有意淡化了他本就有功于社稷的事实。这样的王爵就是接受了也心里别扭。这是宇文泰辞谢的原因之二。
但皇帝元钦公然驳回。说出来的理由条条都有道理。丞相是大魏立基开创的功臣,这一点谁都比不了。到如今连个王爵都没有,实在是让天子有愧。何况还只是个郡王爵而已。如果丞相不受,会让天下人笑大魏天子凉薄。
关于世子的事,元钦也解释得很有理由。嫡庶是礼制相关的大事不假。但仓禀实而知礼节,现在大魏正值当兴盛而起的时候,只论人材,何分嫡庶。宇文觉是极好的,但生来仁弱。幼子宇文邕生来不凡,天赋异禀,更适宜为郡王世子以继丞相之志为大魏开疆拓土。
当然皇帝也表示,等到宇文觉年纪稍长便再授以其它爵位,绝不会委屈自己的这位“表弟”。
皇帝说的话都合情合理,完全占据了主动的地位。不知不觉中,宇文泰就陷入了被动。
宇文泰从来没想到过,这个冲动的小皇帝怎么忽然之间变得有心机了。
丞相宇文泰的态度平静下来了。对此事不置一辞,完全是冷处理的态度。谁也不知道丞相心里是怎么想的。可是谁也不敢真的顺了皇帝的旨意称他“大王”。
然而,真正陷入到为难境地里的人却是云姜。
这事是宇文护委婉告诉云姜的。
云姜听了真是惊愕不已。旨意是皇帝下的,这事也轮不到她来出主意。但是此刻最为难、最尴尬的就是她了。
宇文邕还是个婴儿,她却是这个焦点人物的生母。连南乔这么熟知她的人,这些日子都看起来有些冷淡。更别提宫里皇后和嫡公子宇文觉名义上也算是一母同胞,岂能不为弟弟着想?
云姜并不知道,宇文护的态度其实不是她想的那样。
难得过了几日天气放晴了,节气真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都已经到了晚春时节,长安城是真正地云开雾散了。
连着几天,苏绰的府里都在忙丧事。丧仪典礼极其复杂,又非常琐碎,但总算到了将要落葬的时候。宇文泰的授意之下,苏绰先是被追赠光禄大夫,接着又追赠开国公爵位。
谁都看出来,大丞相对这位苏先生之死是深感痛惜的。
苏绰的棺椁按遗愿要归葬其乡里。定好了棺椁出城的日子,基本就可以暂时先松口气。因为自打卒哭祭之后,丧仪中琐碎的事就渐渐少了。再哀痛也要依礼减杀,这是儒家的礼。
阳光洒得大丞相府的院子里到处都是,天气已经渐渐热起来了。
宇文护在叔父的书斋里,就只有他和叔父两个人。宇文护亲手焚了甘松香。这样的细节也只有他才能发现。他确实发现叔父每次去小佛堂的时候都会命奴婢焚此香,而叔父去小佛堂的次数依旧不少。
宇文护知道这是长公主元玉英生前最爱用的香。
“叔父这几天太累了,也只得今天休息一日,等把苏先生的棺椁送出去才算安心。”宇文护亲手捧茶来给叔父,以尽子侄之孝道。
宇文泰忙于捡选苏绰的文章策牍,埋头案上对一切都置若罔闻。
宇文护在叔父面前坐下。一边瞧着宇文泰忙碌,一边像闲话似地娓娓道,“这事侄儿已经告诉云姬了,她像是完全不知情,再说主上指定四郎为世子也不是云姬能干涉的。”
宇文护说的是什么事宇文泰当然知道。
宇文护看起来似乎自己没什么倾向性。但他这么不着痕迹地帮云姜说话,他的意思也就很明显了。
宇文泰是何等的心思精深。
抬起头来看一眼侄儿。宇文护顿时心里一颤,觉得那双又大又黑的眸子里满是寒意。但他克制住了自己想下意识回避的举动,做出坦然的样子极力坚持,直视着叔父。
“这么说你也觉得皇帝说的有道理?”宇文泰淡淡问了一句又低下头去看简牍。
“道理这种事,”宇文护也极驯顺地回答,“全看言辞。言辞得当就有道理,言辞不当就没有道理。故此,谁都可以有道理。侄儿只听叔父的道理。叔父的儿子都是侄儿的弟弟,侄儿无所偏倚。”
宇文泰没说话,宇文护总算稍放下些心来。
“去传云姬来。”宇文泰忽然毫无征兆地吩咐了一句。
“侄儿这就去。”宇文护不等奴婢们说话,自己借机起身。他知道宇文泰传云姜来必有话要说,他是不宜在场的。
南乔步子轻轻地进了云姜的屋子。
这些天来,她看云姜依然是神态如常。不只自己,就是对几位公子,包括陀罗尼、弥俄突,也全都和从前一样,没有一点愧色。
对宫里的事也分寸把握得很好。
然而南乔刚进了屋子还没来得及说话,就有奴婢来传话说:郎主请云娘子去书斋。
奴婢是宇文护遣来的,他不会自己入内宅来传命。
云姜正好看到南乔进来。南乔自告奋勇要随同她一起去,云姜也就明白她的意思了。
一路向园子里走去,南乔和云姜谁都没说话。好像都在有心细瞧景致。
确实到了此时正是景色最怡人的时候。将到盛时又未及,好过盛极而将衰之时。
天气也将热未热。晚春时的微风拂在身上颇有几分舒适、惬意。
书斋越来越近。那不起眼的屋舍让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变化的云姜心里颇为感慨。她一霎时就回忆起她在书斋里做奴婢的日子。现在想起来也许那时候才是最好的吧。
虽有期盼,但只专注于此。没有那么多的忧惧,那种一心一意的牵挂现在想来就是享受。
南乔进了书斋就看到里面只有郎主宇文泰一个人。奴婢们早就被摒退了。
南乔先给郎主施礼。
“郎主要见云姬,云姬这几日身子不好,奴婢怕云姬有闪失,便送她前来。郎主要是没有别的吩咐,奴婢便告退了。”南乔是这么解释的。
宇文泰当然知道南乔是什么意思。他没说话摆摆手,意思是准了南乔出去。
南乔在丞相府里不同于别的奴婢,总有些故主、长公主元玉英的影子在。
当书斋的门再度关上的时候,屋子里就只剩下云姜和宇文泰两个人。
云姜无声地跪下来。她垂眸看到了宇文泰的玄色的袍子下摆。当那下摆处抖动的时候,她已经被宇文泰扶起来了。
他依然那么有力。
“身子不好就不必行礼了。”宇文泰握着她的手臂并没有放开,力道恰好地把她拉近自己身边。他也有好些日子没和她单独相对了,这时忽然心动了。
“是南乔护着我,郎主别信她。”云姜听出来宇文泰语气里的温柔和调侃。她担心了这么些日子,此时几乎热泪盈眶。但她还是垂眸不敢看他。
“你为什么不自己来?”宇文泰用手指钳着她的下颌慢慢抬起来。
云姜抬头之际眼里的泪轰然流下。
“我不能来见郎主,怕郎主以为我是来请罪的。”云姜的声音有点哽咽了。
“你不该请罪吗?”这话问得严重,但宇文泰极其温存地看着云姜,眸中含着一点笑。
“我没有罪,为什么要请罪?若真是来请罪,岂不是授人以口实,以为真有其事?妾心一片赤诚,没有愧对夫君之处,不愿自污。”云姜却语气决然。
宇文泰也没见过她这么倔强的时候。
“既然一片赤诚,就更应该早来见我,”他慢慢低下头来,“让我看看究竟是如何赤诚”
他的嘴唇温暖地贴在云姜面颊上的泪痕处。
云姜心里瞬间爆开不能自已。
第三十三章:棺椁出城()
?
长安城的郊野深碧满眼。碧草连天,树木茂盛。再远处能隐约看到田畴村落,能让人联想得到农人耕织的繁忙,蕴藏着欣欣向荣的气象。
多灾多难的关中平原,这些年不是兵灾战火就是天灾**,但总是顽强地一次又一次支撑了下去。
天气是阳光灿烂,但气氛却悲哀伤感。
故光禄大夫、开国公苏绰的灵柩要归葬其故乡武功,今日从长安城西门而出。
城门大开,然而并没有什么繁复的仪仗,素车白马简陋至极。寻常人不过如此,因此对苏绰就显得过于简单了。
但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乘马车拉着的棺椁,经过长安街市,却引得长安城中万人空巷。
跟在灵柩后面的是白花花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大魏官员,为首者正是大丞相宇文泰。从宇文泰起,朝臣个个都是熟麻布孝袍。
声势如此惊天动地,苏绰的哀荣也就可以想见了。
百官们个个都是徒步相送,也正是大丞相宇文泰带领。从苏绰故第,一直跟着拉载棺椁的牛车走到城西门,然后跟着牛车出城。
这段距离不短,但谁也不敢叫苦叫累。尤其是看到大丞相边走边哭的样子,稍有心思的官员也就跟着抹眼泪。管它什么自己和苏绰交情如何。
宇文泰已经痛哭到了需要人扶掖而行的程度。但他始终追着牛车不忍远离。当然也没有人敢真的越过他去抢在前面。
见丞相痛哭至此,也颇有一些官员受了感动,觉得丞相待人至厚,丞相惜才之心可鉴日月。
没有人想起来大魏的皇帝在哪里。
皇帝元钦当然也不可能随同百官一起徒步送苏绰灵柩出城。
在百官的队列里跟着人流亦步亦趋的大司马独孤信,还有太尉李虎两个柱国大将军是并列的。他们并没有像太保赵贵、太师于谨那样紧跟着大丞相宇文泰。
也没像另一位柱国大将军、司空李弼那样把握分寸,在宇文泰身后保持着一个适当的距离。
他们显然是有点有意落后了。人流几乎把这两位大魏的顶级显宦给淹没。只有当独狐信偶尔抬头张望时才会让他的气宇轩昂之姿浮现于众人之上。
“文彬将军,这些日子闭门不出,托辞养病,就没有人上门探望过吗?”独孤信有意低头,压低了声音向旁边的李虎问道。
李虎却根本头都不抬,把自己完全隐没在众人合力、哭声震天的百官丛中。
“如愿将军也无事不出门,难道也有人上门寻问大司马心里有什么懊恼之事?”李虎不回答,反过来问独孤信。
“正是如此。”独孤信不避讳,叹道,“试探不过是想加以利用。如此轻率岂能成事?势非得已不得不趋从。”
李虎稍一回头,看到后面落得更远的另一位柱国大将军、广陵王元欣。元欣正形容悲伤,然后举袖掩面,似乎是在拭泪,情状真如丧考妣。
“且坐等,来日总有机会。”李虎不知道是在说给独孤信听还是在说给自己听。他是“来日方长”的典型,最能沉得住气,定得了心的人。
独孤信没说话,依旧跟着往前走。
“今日要出大事啊。”李虎不自觉地感叹一句。
独孤信有点不敢相信地看了一眼李虎。李虎是很谨慎的人。他这种谨慎和于谨那种谨慎不同,李虎更带着一种老练圆滑。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发出这样的感叹呢?
然而更反常的是,居然没等独孤信问,李虎便凑近他低语道,“苏公灵柩出城,举国上下震动,这么大的声势,却不见天子。岂不是在向世人说大魏天子是可有可无之人?只有大丞相才是真正的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