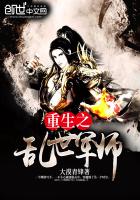南北乱世之倾国权臣--高澄传-第35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元仲华的屋子,哪里会有舆图?那奴婢沉吟不去,刘桃枝也没办法这时候马上就找舆图来。
高澄自己反映过来了,向刘桃枝吩咐速传陈元康、崔季舒等人去东柏堂,自己便返身回内寝中去着衣。
刘桃枝领命而去,高澄进了内寝。这时他心思已经乱了。原以为有高子通在础x,侯景也屯兵在豫州,不至于出什么大事。没想到宇文泰毫不顾忌又这么敢冒险,就真的命于谨率大军直入。柏谷重地,已落入西寇之手,高仲密之叛实际上等于虎牢重地也落入了西寇之手。
若是西魏军一鼓作气,直下洛阳,那么别说河南,河南诸州必定又会纷纷望风归附,彼时再战,宇文黑獭已经是占据了有利地势,实力大增。高澄想到此,心里焉能不急?
进了内寝中一眼看到元仲华正立于眼前,心不在焉地笑了笑,“扰了殿下”他自己去拿衣裳。
元仲华刚才在里面已经听到了外面刘桃枝说的那些话,知道高澄这时是要去东柏堂,她忧心忡忡地走上来,唤了一声“夫君”
“殿下勿忧”高澄截断了她的话,将她拥在怀里,又立刻将她放开,然后去拿起自己的袍子。
高澄一进了东柏堂就想起来了。他曾令李昌仪给她的夫君高仲密写书信。这书信是写了,当时他也看了。李昌仪的书信写得很简单明了,信中言明大将军既往不咎,她也安然无恙,请高仲密速回邺城。
当时高澄没在意,因为也根本没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李昌仪身上。只是手里既然有这个人质,顺便加以利用而已。也算是个没办法的办法。可这时再想起来,总觉得这书信哪里不对。
原本是要直奔鸣鹤堂的,这时按捺不住便直奔木兰坊去了。
这时已经是天色微明。
秋梓坊里的琅琊公主元玉仪倒是早早起来了。当媞女来告诉她,大将军来了,元玉仪端坐在铜镜前看着奴婢给她梳头发,只懒懒散散地应了一声“知道了”。这些日子高澄来东柏堂的时候不多,除了在鸣鹤堂中和心腹密议,倒也来秋梓坊探望过她。
元玉仪也知道木兰坊里现安置了高仲密的夫人李氏。其实她也早该想到了,既然高澄能把她安置在这儿做外妇,那么再安置一个也不新鲜。这时她心里反倒没有那么在意和难过了。至少如今她有了公主的身份和这个胎儿。
有一段时间里,元玉仪和李昌仪共居于东柏堂,但从未见过面。两个人都有意地深居简出,装作并不知道此间还有别人的样子。元玉仪是自矜身份,其实李昌仪也同样是自禁身份。
元玉仪总记得自己现在已经是公主,更没必要去主动亲近一个尚是有夫之妇的外妇。李昌仪却觉得自己怎么说都是个刺史夫人,并且根本没想过要去做高澄的外妇,自然从心底里看不起元玉仪这个原本还是舞姬出身的所谓公主。
高澄进了秋梓坊,倒是意外地看到奴婢们整齐有序地进进出出,看样子这院子里的主奴早就起来了。奴婢们看到大将军进来倒也不惊讶,纷纷施礼。恰好出来的苦叶看到高澄,迎上来行礼,起身问道,“大将军要见小娘子吗?小娘子就在屋子里。”
苦叶那样子看起来倒像是不亲不近,又不疏不远,让高澄心里有点不痛快。但他这时没心思和苦叶计较,直奔李昌仪住的那屋子里去了。
果然如苦叶所说,李昌仪听到外面的声音,正迎出来。李昌仪知道她此时被握在高澄掌心中,她倒也聪明,不会和他直面辩驳,见了高澄就上来行礼,话倒并没有一句。高澄见她这幅不喜不嗔的样子,和苦叶主奴两个人竟是如出一辙,心里更怀疑起来。
“夫人住在这儿倒甚是随遇而安。”高澄四顾扫了一眼,一边又问李昌仪,“夫人见了我没有话要说吗?”
李昌仪看出来高澄这次来和上次大不相同。尤其是看不出来他是喜是怒,心里便预料是高仲密在北豫州出了更大的事。据她私下里看来,高澄并不是个很会隐藏自己心思的人,这时这么淡定难辨的样子,连她的心也跟着悬起来了,不知道究竟事情到了什么程度。
“大将军要是有事,必会吩咐,何必还要妾多言多语。”李昌仪咬定了不肯顺从高澄的心思,把握着分寸淡淡回道。她知道此时若真是弃了高仲密来迁就高澄也未必会得好结果,反倒可能会被人轻贱。还不只是被高澄一个人轻贱。
高澄又把目光收回来,盯着李昌仪。“夫人写给高仲密的信算起来早就该送到了。夫人可知道?西寇攻下了柏谷,高仲密受了宇文黑獭封的侍中司徒之职,已经与西寇贼军合为一处,欲奔袭洛阳而去。”
看高澄的神色不像是在诈她,李昌仪心都冷了。其实她与高仲密是早就在约在先的。若是书信往来,一律正话反说。所以她送给高仲密的书信让他回邺城,其实意思正相反,是他别回来。
她之所以这么说,用意数重。知道高澄会看这封书信,为了这不让高澄起疑,故书信写得也简单。言语明了,让高澄无处猜疑,这样才能送到高仲密手中。其次也是借书信向夫君高仲密表达自己的心意。暗示他,她在高澄手里为人质。在高仲密看来,书信里的意思是让他不要回邺城。但更有一重更深的意思,让高仲密明白她也是身在危境,并且尚以他为念,希望高仲密见到书信能设法救她。(。)
第三十四章:相臣父子()
李昌仪之前一直相信,高仲密就算是想反叛,事前也是想先把她接出来,离开邺城的。不然不会千里迢迢命心腹来救。但这一刻起,李昌仪心里怀疑了。高仲密竟是真的弃她不顾了。这让她心里不但失望,而且顿生怨恨。此后她命运如何,恐怕就要全靠自己了。或者她往后就是真的握在高澄手里了。
李昌仪不愿意让高澄以为她在高仲密那儿是说话无效力的。她知道男人微妙的心理,如果她真的在高仲密那儿一文不值了,那么在高澄这儿恐怕也就没什么价值了。
“高仲密既是我夫君,我自然以他为念。社稷乃君子所执掌之事,妾一妇人与此无干。”李昌仪没把话说明白,她避开了高仲密反叛这个事实,只把自己降低到了一个无知匹妇的高度。这样就让人觉得夫君反叛这样的事不应涉及到她这个妇人。
看她这态度,高澄这时才明白,是李昌仪从中作梗。当然他也清楚,高仲密如果要反叛,不是李昌仪一个妾妇能拦得住的。只是第一没想到,李昌仪帮高仲密帮到底。第二没想到李昌仪对夫君这么从一而终。这倒让他有点看不明白了。
高澄心里还明白了一件事,之前还真的是他小看李昌仪了。纵然他阅人无数,但是像李昌仪这种心思精明,长于算计的女子,还敢来算计他,和他斗智斗勇的,真的是没有。这个关键时刻,他恐怕马上又要西征而去,若是再这么把李昌仪放在东柏堂里,不知道她又会生出什么事。
若是把她放回高仲密的刺史府第里去,恐怕也不是个好主意,她并不是个安分的人。
李昌仪看高澄这么盯着她,又是忽阴忽晴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心里突然有点后悔,觉得是不是没把握好尺度,过于相抗。可现在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既然夫人是一心为了高仲密,我也无话可说。”李昌仪心里正七上八下,听到高澄声音冷硬地道。她抬头看时,高澄满面冷酷,不似从前对她温柔玩笑的样子。“夫妇一体,我也只好把夫人交于廷尉。等到将高仲密这个叛贼捉回,夫人与他在狱中自能相逢,也算是成全了夫人对夫君痴心一片。”
高澄说完转身而去。
李昌仪目瞪口呆地愣在当场。她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可是现在她再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再看时,高澄的背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天亮了,鸣鹤堂中用不着再点灯。
高澄及他身侧的陈元康、崔季舒、崔暹等人一起面对着舆图。
高仲密叛魏已是事实,再不想承认,虎牢关也已经落入宇文泰之手。于谨得了柏谷。若是再这时宇文泰再命西魏军东进,再加上于谨、高仲密的策应,下了洛阳、金墉
“大将军,河桥危矣!”先是崔暹第一个失声叫出来。
他看着高澄的手指在舆图上沿着洛阳、金墉、柏谷、虎牢划着半圆,那个半圆的中心就是河桥,立刻就看明白了。
连崔暹都看明白了,那别人自然也明白了。
“大将军可令侯景引豫州所屯之军截住高仲密。于谨为人谨慎,没有高仲密策应必不敢轻进。宇文黑獭援军不会来得那么快,大将军可以有时日再调兵遣将。”陈元康眼睛盯着舆图。
“不可,不可,万万不可!”还没等高澄说话,崔季舒摇头如鼗,反正眼前都是自己人,也不必顾忌,“侯景岂能对大将军真心用命?这时用他,长猷不怕他坏事吗?”
“叔正错矣,”陈元康反驳道,“侯景其人诡诈是不假。但也要分对何人何事。若是宇文黑獭这时提兵已至,大将军必然不能信赖侯景。不但不能信,还要多防备。但这时局势未定,宇文黑獭未至,只有一个于谨轻骑冒进,侯景此人倒不是轻动之人,不至于立刻就与于谨合兵一处反了高王。倒是高仲密,本就是叛臣,侯景若截杀叛臣便是有功于社稷,有功于高王,又可保其河南之地无虞,他何必不为之?况且他儿子武卫将军侯和还在邺城,在大将军手中,他又岂能真的一点不顾忌?”
陈元康看样子是心里早就想好了,一口气反驳了崔季舒,又向高澄道,“大将军此时切勿心急,据长猷所知,宇文黑獭之前并未有立即便与大将军一战之心,只是高仲密反叛事出突然,让其觉得机会难得。黑獭是果决之人,正因为如此便觉得机不可失,趁势无防。西贼国力贫弱,又是劳师远袭,入我腹地,也未必就能节节而胜。况且,高子通书信来表其心迹于大将军,必然倾其所有,不令其兄与黑獭合兵作乱。大将军勿过分忧矣。”
陈元康平时不是多话的人,这个关键时刻倒如银瓶泻水一般说了这么两大篇,立刻就把崔季舒和崔暹的所有疑虑都给堵了回去。
连高澄都在心里镇定下来。他夜半被惊醒,闻知失了柏谷,一霎时心里难免惊慌。正是因为深知河南之地的重要。河南一直都是两魏相争的要地,况还有侯景这样的不稳定因素在这儿。他深怪自己没有及早下手,遣心腹在河南屯兵镇守。
柏谷一失,河桥危矣。河桥再失,大局已定,他又岂能不惊慌。
陈元康这一番设计分析让他重增信心百倍。只是他并不肯将自己的真心露出来。况且,宇文黑獭未至,一个于谨而已,还是他的手下败将,有何所惧。这时高澄心里更对高仲密百般痛恨,原先想劝归的心思全都没了,只想提兵而至,速速灭之。
高澄重新镇定下来,向陈元康笑道,“长猷兄与言与我所见略同。不过既如此,又免不了辛苦长猷兄与我再赴河南。宇文黑獭既然无端起衅,我若不应战岂不长了西寇的威风?此前在河桥,可擒了宇文黑獭,也可放了他,今日在虎牢再擒之又有何难?”
陈元康揖道,“臣元康乃社稷之臣,大将军之臣,必然尽心用命。”
不知怎么,邺城的天气又闷热起来。一丝风都没有,就好像空气都不再流动。纵然大将军高澄没有公布高仲密已叛的消息,但想也来是捂不住的。邺城这时的安静和过于沉闷,反倒不像是真的。
崔季舒站在铜雀台的高台之上,他心里出于一种怨念格外郁闷。即便是在这儿也感受不到有一丝风,简直是太邪气了。他胖大的身躯不堪这种闷热,里外几重衣裳几乎都被汗水浸透了。
可他再看高澄时,坐在半残的亭阁石阶上的世子,就好像感受不到这种闷热,一动也不动。
高澄略垂首,用手撑着额角,手肘支在自己膝上。所以崔季舒看不清楚他的表情。他不知道,这时高澄脑子里几乎就是一片空白。他心里思绪杂乱,别看在这儿安坐,其实根本静不下心来。
高澄急于调兵遣将安排战事,这时是时贵如金,他虽明白这个道理,却怎么也没办法沉下心思想这事。心里乱得一刻都难得安定下来。
正午时,太阳高照,虽然残阁高大挡住了强烈的日光,但高澄和崔季舒哪个不是如热锅之蚁一般?
刚才在鸣鹤堂里,高澄在无人时就已经有点浮躁起来。崔季舒陪着他出城散心,本来是想让他舒解心情。不知不觉到了铜雀台,这是大将军避暄之处,崔季舒本来以为他安静一会儿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