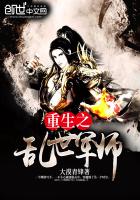南北乱世之倾国权臣--高澄传-第2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宋梗浠ビ惺じ海雌鹄椿故俏魑壕杂惺ぜ!V皇俏魑壕埠投壕谎鹗Р抑亍�
战事到了这一步,是退是进,都不宜再拖延。何况宇文泰和元宝炬心里还放着一件事:柔然世子突秃佳不日便要送柔然公主来长安举行和亲大典。立后这样的大事宜祥和,不宜有征战的不祥之音。皇帝元宝炬和丞相宇文泰应该在大典前适时地赶回长安去。
已经到了冬天最冷的时候,金墉城更是格外阴冷。宫殿虽不及旧日洛阳、现在长安,但洒扫、收拾了也勉强能用。可是此地非故乡,金墉城中所有人都无日不思归。
潮湿阴冷的宫城大殿,火盆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反增炭气。不过总是聊胜于无的,所以也就随它去了。皇帝元宝炬坐在上面的御座上,甚至连裘服都没穿。用他的话说,“将士尚饥寒之中,孤岂能忍心锦衣华服饱食终日?”
元宝炬看起来气色倒还不错。前些日子落马的摔伤基本已经痊愈。反倒是不计晨昏、风餐露宿的东征让他一扫久居深宫的胸中滞闷之气,记起了自己也曾经是满腔豪情的帝室后裔,鲜卑男儿。让他想起那个曾经等待他,给他中衣上绣了忍冬花的人。只是这个人再也不能提了。
此刻大殿里除了皇帝元宝炬还有坐在他身侧的大丞相宇文泰,下面席地而坐的骠骑将军赵贵、车骑将军于谨、督将李弼、李虎几个人。都在听赵贵讲斥候送回来的消息。
东魏第一猛将高敖曹死于西魏军之手这确实让西魏军为之震奋,并大有一鼓作气平河阴,过河桥,挥军直奔上党的气势。当然,气势归气势,形势是形势。所谓胜负要看怎么论定,东魏虽然损兵折将,西魏也因久战而后继不足,无论兵源、物资,都难以供应了。
既然两边皆有折损,也都缺乏足够的支持力,战事到此为止就暂停了。看起来东魏军似乎并不在乎西魏军这个时候的动向,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东魏军来打探过消息。西魏军派出的斥候也所获不多。
赵贵把斥候的情探做了汇总一一讲给大丞相宇文泰、皇帝元宝炬和几位督将。首先,河阴城现在防守非常严密,打探消息也非常不易。奇怪的是以高敖曹的身份,阵亡后竟没有人来找回尸身,丧事草草,似有若无。无论是以高欢父子和高敖曹之间的关系、情谊,还是以高敖曹在东魏军中的地位,都不应该如此。
更可疑的是,河阴城中凡事皆是濮阳郡公、豫州刺史、司徒侯景主持。虽然侯景是豫州刺史,这是他的治内,但有大将军高澄在河阴又是主帅,怎么也论不到凡事侯景说了算。侯景这个时候过分地专治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就算是大将军高澄中了一箭,负伤在身,也完全可以让他的心腹、辅国将军陈元康代行其事。可是陈元康从来没露过面。斥候也有难处,在河阴城中根本打探不到大将军高澄的任何消息,封锁甚严。
东魏军中当然也有西魏暗线,但也几乎不知道什么,关于大将军高澄的事讳莫如深,像是被侯景有意交待过不许外传。但蛛丝马迹总是有的。有两个细节赵贵格外留意,讲了出来。
高敖曹死后一日夜,消息传回河阴城。当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又过了一日夜,忽然营中哀哭之声惊天动地,如丧肝胆。这就奇怪了,为什么当时不哭,过了那么久才哭?像是为了高敖曹哭,又不太像,而且越细想越不像。
另一个细节,在河阴城中的侯景目前是无人能辖制的高爵显宦,除了高澄再也没有人能压他一头。斥候见到侯景,打探侯景的消息倒是很容易,就是这个万众侧目的侯司徒,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愁眉不展的样子,像是很担心什么,并且他着了丧服。
无论以侯景的身份,还是他和高敖曹的关系,他都不应该为高敖曹穿丧服。哪怕有大将军高澄在,箭伤尚自顾不暇,哪儿有精神管侯景穿不穿丧服?
侯景,究竟为谁穿丧服?
赵贵的一番详论让整个大殿里都安静下来了。
所有人都陷入沉默中。人人都觉得,东魏军如此忌讳,消息封锁如此严密,这其中必定隐藏了大事。这是不是西魏军可利用的契机呢?战事到此已经拖不起,如果天赐良机能趁隙大胜,这倒是速战速决的好办法。
所有人把目光都集中在大丞相宇文泰身上,连皇帝元宝炬也一样。
宇文泰眉头深锁,没理会任何人,显然是在绞尽脑汁。他并不是个犹豫而不果断的人,但是眼前事情并未分明,也说不定东魏军有意使诈,在这个关键时刻一步小错可能就是毁了整个西魏的导火线。
“主上,丞相,”赵贵忍不住还是开口了,斥候是他派的,关注河阴城中东魏军的动向这一直是赵贵职责的事。“会不会是河阴城中出了更大的事?所以无人有心思为高敖曹治丧?”
这话撞到所有人心坎里其实都是顺了心思的,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在潜意识里希望东魏军中有大事的。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确实有道理。如果不是因为有更大的事,还有什么理由不为高敖曹这样身份的人治丧而如此草草呢?河阴城中的安静和封锁消息难道不是因为在等待邺城的指令?
究竟有没有消息送到邺城去呢?
宇文泰抬起头来看了一眼于谨,“思敬,汝当做何解?”点名问于谨,是因为知道于谨心思细密。
“丞相,此时吾与敌都是守株待兔,万万不可心急,不妨静以观变。”于谨虽然也一时想不出来原因,但还是主张稳妥些,因为他知道此时的西魏军看似有胜算,但绝对不能遭逢大劫。
“思敬将军固然求稳妥,谁知东寇又是什么心思?以静待变不如攻其不备,事若生变其因自现,自然一切明了。”久不说话的督将李虎不知怎么忽然接了一句。
殿内沉默了。
元宝炬原本想说什么,但是看了看宇文泰最终还是没说出来。
河阴县衙终于归于平静。这种平静不是真正的平静,隐藏着随时会爆发的暗流。
大将军高澄暂居的院落完全被封锁了。太医们也被禁在这个院落里不许出入,另有几个仆役,都不得随意奔走。此外能进出的就只有大将军的心腹、辅国将军陈元康和豫州刺史侯景。
大将军高澄本人之前因为箭伤过重不能下榻,自然出不了这屋子。后来知道了大都督高敖曹阵亡的消息后,虽然他自己伤势日日见好,但是他像是自己给自己禁了足,没有走出过这屋子一步。
第242章 :争河桥慷慨多悲歌(十四)()
高澄烧退了,伤口也开始渐渐愈合,终于也能下榻了,然后能慢慢在屋子里走几步。陈元康****在此侍疾,也一样深居简出。他总觉得就是几日之间,世子与从前大不相同。默默旁观,他看着高澄还略有苍白的面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伤病憔悴,再也找不到从前少年时像女子般的细腻肌肤。这张面孔上这时也因为无心修饰而青髭横生,显得有些粗糙,但完全蜕变出了男子气。目光令人觉得捉摸不定,那双绿眸子不再像清澈见底的浅溪,更像是深不可测的寒潭。
陈元康穿着粗劣的生麻布衣裳,看着高澄穿着中衣,披着外袍在屋子里步子从容、缓慢地走了几圈。两个人各有所思,谁都没说话。这几日陈元康一直都遵世子吩咐,穿着这斩衰孝服在县衙的院子里招摇,虽不是全套斩衰,但也够引人注目让人猜测了。
两个人之前密议过,遵照世子说的,陈元康不出县衙,不会出现在河阴城街头,但是在河阴县衙的范围之内几乎无处不去,穿着这扎眼的生麻布衣裳曝光率实足。若说起高敖曹来,他和高敖曹之间的恩义谁都知道,陈元康自然是会泣府公之早逝。但若有人有意无意地问起大将军来,陈元康都是蹙眉忍泪红着眼圈,好像努力忍着要隐瞒什么事实。
越是如此越招人议论。那一日大将军中箭的情形是很多人都亲眼看见的,那疗伤的过程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只是忽然太医们全都被禁,大将军再没露面,心腹陈元康又是这么欲言又止,更加上豫州刺史侯景变成了河阴城及东魏军的主宰,事事独断专行这实在是太耐人寻味了。
“大将军,”陈元康看高澄走了好几圈,忍不住劝道,“重伤难以一时痊愈,不可过于心急,反有损伤。”
这时太医捧了药已经开门进来,奉上汤药请大将军进药。
陈元康也走到高澄身边,盯着太医。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气味,连他也禁不住盯了那药碗一眼。
高澄却一句没问,捧起药来一饮而尽。可能是因为草药的味道实在是不好,他下意识地蹙了眉头。等太医出去了高澄走回榻边坐下。
“大将军,这样一点马脚不肯露,宇文黑獭会上钩吗?”陈元康跟过来瞧着高澄问道。他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依赖少主,相信他、期待他。
高澄刚才不觉得,现在回到榻上才觉得很累。用手指了指,示意陈元康坐下,以免他再抬头仰视他,那样更累。“宇文黑獭自己就是个深怀计谋之人,若是有意露马脚给他看他岂能不知?”看着陈元康跪坐于地,高澄喘息渐渐平定,“长猷兄,你想多了。若是我真的死了你会如何?”他忽然盯着陈元康问道。
陈元康心里一沉,凉意顿时从后颈升起,他不由自主地跪直了身子,喉头酸涩,险些堕泪。想起前些日子高澄刚刚中箭抬回来时候的情景,心里更不是滋味。
陈元康终究还是个稳重的人,心里暗自平复,低头掩饰,慢慢坐回去,这才又抬头道,“长猷不愿做此想,情愿以己之命换世子。”
高澄笑了,一瞬间好像又回到了那个顽皮的少年,没想到陈元康这么容易被逗弄。意外满足了捉弄人的小心思,他很开心,笑道,“长猷兄,这不过是假说而已,你不妨想一想。想一想你究竟如何去做,宇文黑獭才会相信我真的死了。”
陈元康低下头,这事真让他很为难。
“长猷兄,你不想回邺城吗?”过了半天忽然听到高澄缓缓问道。
陈元康又抬起头,“想回去。”
高澄的绿眸子正看着他,其中温情脉脉。像是心里揣着什么期待,才让他生出如此温情。
“河阴城不是什么安稳的地方,久在此拖延难保不生变,到时候你我都是别人砧上豚彘。”高澄的声音又低又缓,“况带甲数十万,劳师远征,所需资费在此一日就是巨耗,不只是宇文黑獭拖不起,我们自己一样拖不起。”
“世子连日来都夜不能寐就是为此吗?”陈元康忽然看着高澄低语一句。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心神安定,谁先心急不定就是谁输。”高澄没理会他的问题,又低语了一句。这是他和宇文黑獭比定力的时候,谁先心动谁就会大败而归。
两个人都沉默了,各自陷入沉思,屋子里安静下来。陈元康开始认真想高澄刚才说过的话,想自己究竟该在这个时候做什么。
高澄最头痛的问题是自从知道了高敖曹的死讯以来,他便开始难以入眠。心里千头万绪,心头重负重重,但在这个时候他又必须镇定下来,要安静、要耐心,这种感觉有时候迫得他几乎疯巅,但又不得不把这些都安放在心里,以静制动,静以观变。
累极了,闭上眼睛,知道睡不着,只想休息片刻。这时元仲华的影子又涌上心头。他赠于她的玉笛摔碎了,她会不会伤心?这么久不见,她都在做什么?她会不会思念他?还是真的抛开不想了?为什么总是拒绝他?他真想这时候就出现在邺城,就回到大将军府第,见到她亲口问一问。
宇文泰也是个有城府的人,不会轻举妄动,他最终采取了于谨的意见,按下略有急切的心思静静等待。这一等果然又等来了河阴城中的动向。
天不亮的黎明时,河阴城最安静的时候,一直没出河阴县衙的辅国将军陈元康居然带了几个人飞骑出了河阴城。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陈元康好像预先就知道什么似的,很有目的性地抓了一个看起来和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异样的男子就回了县衙。
看来这个人必定不是没要紧的人,不然不会在这时候还能劳动大将军的心腹来亲自抓他。
“砰”的一声巨响,在黎明时格外震耳欲聋。这一声巨响不止震动了河阴县衙,甚至震动了整个河阴城。这是陈元康踹门的声音,他踹开了刺史侯景处理公务同时也兼寝居的那个院落的大门,完全不顾及有多少人此刻都盯在他身上。
仆役们从未见过陈元康如此暴怒,双目血红如同猛兽。吓得仆役们纷纷躲进角落里,若无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