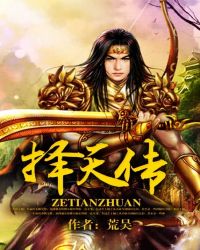痞妃传-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阿克敦贱呲呲的笑道,“爷儿,咱不跟那孙子辈儿的人置气,耽误那好心情莫不如教咱几招,到底是咋驯的咱那辣嫂子?”
咋驯的?
呦,于得水赶忙端着空茶盘儿退下去,就自家爷儿那撒谎脸不红的淡定样儿,他都不好意思了!
但听咱七爷儿那慵懒的动静儿道,“这女人吧,她再辣,也不过就是个属螃蟹的,外头的骨头再硬,里头包着的也是一身儿软肉,这必要时耍些爷们儿手段,她总是要酥的。”
嘿!就说咱七爷儿这道行高!
“来,来,也教咱几招!”
且说那阿克敦那头叫的欢实,这头的延珏是被这虚面儿拱的老高,自觉儿就忘了那昨日的糗事儿,这心情一大好,自个儿心头攒着些吹牛挂面儿的嗑儿,正准备拿杯茶水儿数道数道着呢,可这才伸手,一转头儿
这白玉杯咋这么软乎?这么肉乎?
让这指头间的触感弄的一楞,这延珏是懒懒的一转头,穿过层层烟雾热气儿,定眼儿那么一瞅
好家伙!
这不楞是一粉白儿似红的大姑娘么!
但见那裸着白嫩肩膀头子的姑娘,一双似醉非醉眼儿笑眯着,那红的跟樱桃似的嘴儿兹一轻启,一阵小的只有俩人能听见的天津味儿飘了过来。
“吹,接着吹,我介耳朵今儿不咋好使。”
呦喂!妈耶!
霎时,延珏直觉一股子热气上涌,只觉深处梦幻之中
这主!这主怎么无孔不入耶!
延珏只愣神片刻,差点儿失声叫出来!
这主儿她是不是女人!
这他妈跟这仨大老爷们儿一个堂子里头泡着,咋都没个异样!
按说这老爷们儿就是老爷们儿,就算这延珏半只眼睛瞧不上这俗气福晋,可这俩光腚老爷们儿跟自个儿媳妇儿泡一池子,他这心眼子再大也受不得这个啊!
说时迟,那是快!
只于片刻,咱这从睡梦中才醒过来的小猴爷儿就被这七爷儿一股子蛮力连头带身子的按到了池子里,接着那是一声走水了似的大喝,“都给我滚出去!”
且说那阿克敦和精卫被这抽冷子的一吓,全都傻了眼了,不知这爷儿这股火儿打哪儿来,立马是站起了身,急问,“咋了,爷儿。”
“滚!”延珏那动静儿已是带着火光杀气,震的俩人是灰溜溜立马光屁股爬上了堂子。
但说这平素再和气,可这主子就是主子,这爷儿说一,谁敢说个二!
可这二人脚前才要走,就听那身后猛一股子钻出水儿的大动静儿,接着一股子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天津味儿呛声喝道。
“我操你二大爷!介要憋死谁不成!”
呦喂!介……介……介介主儿咋跑这儿来了!
那阿克敦和精卫瞬间石化,纷纷狼狈的身手护住那后头光裸着的屁股蛋子上。
只听一声喝雷似的暴怒声,“滚!谁他妈敢多瞅一眼,我要谁脑袋!”
第十三回 浴中鸳鸯两纷飞 两双断掌皆似火()
诗曰:嬉笑怒骂一顽主,散漫无谓一痞爷。
两双断掌皆似火,见了棺材泪不垂。
话说这阿克敦和精卫慌慌张张出了玉堂后,这玉堂已是烟雾半散,水气挂壁,只剩得那未着寸缕的小两口儿肌体熏赧,坦诚相视。
如是这般,自当是怒意全消,不计前嫌,只瞧当下良辰美景,干柴烈火,一对赤裸鸳鸯如水波荡漾……
咳咳,列为看官,我劝着您还是别遥想了,您也不瞧瞧这二位是个什么主儿……
且说,兹听那头儿门一栓,延珏心中怒意聚胸,眉眼一横,便一把摔开那手中藕臂,扑通只得一声落水声儿。
半晌,只见那小猴儿一个猛子从水里扎出来,那一头长发在水面儿划过一道弧线,再站起时,已是酮体挂水珠儿,曲线毕露,在那满室氤氲的微醺油灯下瞧去,那真真是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有那么一时片刻,延珏不觉被眼前如画美景晃神,心中怒意尽消,然待思及那刚才赧事,心中又搓起一把火儿来,只见他倏的从水中撩起,一双狭长怒目居高临下的盯着那再度没入水中,只露一头的小猴儿,喝道。
“你丫他妈来这儿干什么?”
石猴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撩起胳膊,瞧着那小臂上红的似出了血的五指印,又瞄了一眼那精壮的身板子,翻一白眼儿,冷笑,“我来介喝汤来了。”
那暗地里的意思是,既来介玉堂,我他妈不洗澡还能做嘛!
按说在平日,咱小猴爷儿保不齐早就一脚断了他的命根儿,可只用余光瞄那么一眼眼么前那精壮异常的身板子,再思及今儿早上床上那几番交手,石猴子心知自己不是介主子爷儿的对手,要是这会儿动手,她纯是那黄瓜上案板,找拍。
再者说,她这性子虽是素日散漫却不是那傻小子睡凉炕,凡事全凭火力壮,她可不傻,按说介俩光腚拉查的一男一女在介水池子里头舞拳头弄脚,到了后来啥下场谁又说的准?
所以咱小猴爷儿也只能做那片刻胯下的韩信,躲在那水里只留一张卫嘴子逗壳子。
可奏是这张卫嘴子吊着那满口儿的不屑也让咱七爷儿这京油子气的心窝抽抽。
延珏突然一扫怒气,睨着那猴儿,只扯嘴儿轻笑,就她那话顺坡下道,“如何?汤可好喝?”
石猴子散漫的拨弄着眼么前儿的水波,也不瞧他,只道,“介王八汤味儿不错,奏是介王八烹的还差点儿火儿。”说了这句抬头瞧着延珏道,“要么你这再坐下泡会儿?”
噫~!
介拐着弯儿骂他睿亲王是王八,介石猴子绝对京中头一号啊!
可奏在这满堂子的水儿都等着怒极的七爷儿拍上来的当前儿,却只听得那水面‘咕吨’一声儿,接着一阵爽朗的笑声,您再瞧
呦喂!那七爷儿竟真真儿的落座到了那石猴子旁边儿!
“啧啧,福晋这张嘴呀……”他说着抓起石猴子的一双手,翻过手心那么一瞧,笑道,“呦喂,还真是个双断的烈货。”
这一倏的变性儿,可是给咱小猴爷儿弄一楞,待反应过来,立马要抽回手,却奈何力气不敌那延珏,反被他一把拉到跟前儿。
只听‘哗啦’一水声儿,那小猴儿已是被这七爷儿的一双铁臂圈到身前。
这抽冷子被裹到一滑腻如缎的身子里,那石猴子是全身一僵,鼻端一阵清爽体香袭来,片刻只觉骨头逢里窜着凉气,通体生寒。
如此无缝隙的贴合,她才发现,这延珏的身子竟是如此滑凉!
挣扎,挣脱,扒拉嫩胳膊,蹬那小肉腿儿。
咱小猴爷儿使出了那一连串吃奶的动作,也没撼动了了那延珏半分。
可不?
咱这七爷儿他虽是素日散漫,可要说这醉心的骑射摔跤,在这宗室子弟里,他敢叫头号,没人敢说二!
“用不着扑腾,这三条腿儿的蛤蟆少见,两条腿儿的女人这北京城多的是。”
嘿!
要说介话一般女人可听不得,可偏生咱小猴爷儿一听,倒是心落了地,只是这受制于人,难免这心头掰不开瓣儿,不由得紧咬下唇,憋的一张俏脸儿是通红。
那模样儿,瞧的延珏眉眼弯弯,皆是笑意,他弯下头附在那小猴儿耳边,吹着气儿道,“爷儿不过是想给你讲个段子,福晋听着便是。”
石猴子别过头,气道,“有话奏说,有屁奏放!”
延珏也不恼,只把玩着手里头那小猴儿柔嫩嫩的手,漫不经心,娓娓而谈,“这前些年爷儿刚玩儿鸟那会儿吧,皇阿玛赏了爷儿一只邢台将军墓的红子,那可是全国最好的红子鸟,那叫口,甭提多脆生了,就是那性大,才带会儿府上那会儿,那是成日里头伸脖压杠,在那笼子里头扑腾,可是给爷儿折腾坏了……”
“你介磨磨叨叨的到底是要说嘛?”受不了这鸟话,石猴子一口截断。
捏捏手心里小手,滑凉的指尖沾者水气轻划着那掌心的横纹,似是没听到她那话般,接着自问自答,“后来你道这鸟儿怎么着了?”
“爷儿只叫人撤了这鸟儿所有的食儿和水儿,不消两天,它就给爷儿服帖了,要么说呢,这鸟儿性大它得驯,这人性子太冲,她也得驯,”
诶,话到这儿,咱小猴爷儿是明白了。
合着这鸟来鸟去的,不过是借着鸟敲打着她。
驯她?
石猴子笑笑,轻嗤,“恁说着介绕着弯子放屁,他动静儿奏是不够。”
延珏朗声大笑,“福晋这性儿!还真像极了我那鸟儿!”
“你他妈才是鸟!”
但听石猴子一声和雷子,趁延珏放松,抽出手就是一个手刀抄延珏那不着调的俊脸劈过去,却才触及鼻梁,就又被那只滑凉大手钳住。
只听延珏一声似笑非笑的冷哼,“爷儿养的这鸟,它可以叫,但它要是太烈,爷儿可受不了。”
这话说完,乎得起身,一把把那身形娇俏的小猴儿甩到水中,他瞧都没瞧一眼,就登上那墨玉台阶儿,抓过衣服披上。
“我操你二大爷!”
食指剜剜那耳蜗的水,延珏只当那身后那天津味儿的娇骂是风凉话,只自顾出了这玉堂,出门之前,他顿步,勾勾唇角道,“爷儿得让你知道,这谁才是主子。”
石猴子才要还嘴,却只见那人已出门,半晌只听
‘咔’一声儿。
玉堂,落锁。
这外头,月上柳梢,乌鸦叫。
想必是才刚那光着屁股出来的阿克敦和精卫已经在这院子里闹出了不小的动静儿,遂这玉堂里头的事儿,外头已经是传遍了老婆舌,待只披着一件薄衫的延珏从那玉堂出来时,那院子里已经是候了一地的玉堂的奴才。
他们一个个的服帖在地,战战兢兢,只等这主子发落。
院子里,安静异常。
只听得那一漫不经心的寒凉动静儿
“给我把这玉堂的火烧起来,没有我的口谕,那扇门,谁也不准动。”
第十四回 这厢戏台来做戏 牵肠挂肚只一人()
延珏这尊贵精致的皮囊里,究竟包藏了几个不同的人,从来就没人弄明白过,人们只明白他绝不止散漫,无谓,纨绔不着调,也绝不止残忍,寡情,心狠性凉。()
“于公公,你通融通融,让咱见爷儿一面吧,这福晋都在里头一个多时辰了,再这么下去,会憋出人命的!”
正房门外头,谷子拿着那拳头大的珍珠一个劲儿的往于得水手里塞,那一长一短的两条腿儿急的是小碎步跺着,直蹭的那片儿地上的灰儿薄了一层儿。
“哎呦,我的小姑奶奶,你可别为难咱家了,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甭说咱七爷儿这会儿都睡下了,就是他这会儿醒着,任是谁求,也不会松口打开那门的,主子那性儿……哎……”被谷子整整磨了半个时辰的于得水实在是逼没招了,索性直接撂了话底儿。
“那要怎么办么!”谷子一跺脚,急的都出了哭腔,“一个主子这样儿,两个主子都是这样儿!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攥着那大珍珠,谷子憋着眼泪瞧着那玉堂方向,心里头恨不得冲进去那这珍珠砸了那猴子的头!
恁说是不是糊涂!这个犟种怎地就不肯求饶一声!
再这么下去,她真就成了那清蒸猴子肉了!
谷子红着眼儿剜着那身边儿一直小脸儿煞白的丫头春禧,抬手便是狠抽了几个巴掌,“都是你这丫头贪嘴坏事!”
“住手!”随着一声喝,但见那一身儿旗服的侧福晋舒玉带着几个丫头进了院子,瞄了一眼那春禧红肿的脸,眼神漫过一丝恼怒,遂道,“好个厉害丫头,我怎么不知道这府里什么时候由的你打罚下人!”
知来者不善,谷子使劲儿咬了下唇,扑通一声儿跪在地下,“是奴才乱了规矩,请主子责罚。”
“责罚?哼……”舒玉一声冷笑,换了张与白日完全不同的厉害模样,“是该帮着福晋好好磨磨你这些个规矩。”
“香姑,掌嘴!”
啪!啪!啪!啪!啪……
夜里的院子安静除了那房头儿的猫声儿,就只剩这清脆的巴掌声,一声儿接一声儿,跟本没有停的意思,一旁的小丫头春禧哭着连连磕头求侧福晋别打了,可那舒玉却瞧都不瞧,只一脸得意的冷笑,心念
相府小姐又能如何?
我舒玉照样儿梳理你的奴才!
一旁的于得水拿着佛尘摇头叹了口气,遂半闭着眼儿低头把在门边儿,像惯常一般,全当看不见这女主子间的勾心斗角。
这时,随着又一连串的脚步声儿,但见三个提着灯笼的女子进了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