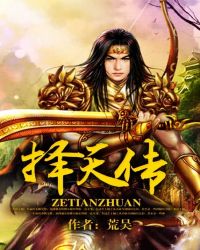痞妃传-第6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琢磨着
“七爷怎么……”
见才刚还好好的延珏,这会儿抱着小猴儿说倒就倒,僧格岱钦还一怔
丫又醉了。
难怪这主儿神智不清了
这就对了。
当一股子浓浓的酒气顺着那秋夜的小凉风儿吹过来,在那脑袋耷拉在颈窝儿的时候,小猴儿再度翻了个白眼儿,吁了一口气。
说时迟,那是快
“嗝”
“你吃过啊?”
“屎不好吃。”那迷离中状似认真的动静儿又在耳边响起,小猴儿连白眼儿都懒得翻了,偏偏头只嗤道。
小猴儿三次翻一白眼儿,“你他妈折腾我一晚上空着肚子跑来跑去的,我不吃饭我吃屎啊。”
二大爷的
“吃什么饭啊……”耳边儿那‘撒娇’的动静儿再次响起,直麻的小猴儿是一个激灵
小猴儿二次翻一白眼儿,压低声音道,“我求你了,你让我好好吃口饭吧。”
大爷的
“爷儿就乐意恶心你……”
延珏那两片薄唇上下一搭,弯着那精致的眉眼儿,懒嗒嗒的扯嘴儿一笑,在扯她坐下后,胳膊一使劲儿,把她的身子拉过来,贴着耳朵吹着气儿。
不成
我说你甭恁么恶心人,成么?
一个干呕,那‘撒娇’似的语气愣是让小猴儿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待朝那‘娇憨’的主儿翻了个白眼儿,她用只有俩人能瞧见的角度,上下嘴唇儿无声的嘎巴着
介嘛调啊?
呕
一只修长白皙的手伸过来,小猴儿伸手搭上去,那指尖所触及的凉意让她抬头瞄了那主儿一眼,但见延珏那狭长黑眼儿眯成一条缝儿,喷着酒气,勾唇轻声喃道,“怎么才来,就等你了……”
“七福晋客气。”醇厚温和的声音响起,瞧着眼么前儿这倏的遮住光线的一双织锦皂靴,小猴儿并未抬头,而是欠了欠身子,朝那坐上笔挺的尊贵爷儿走过去。
一边儿跟着的谷子都瞧着眼慌,直直心叹,呦喂,合着她不在这段儿日子,这小爷儿给塞了那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了吧,这架子,这派头,啧啧……不得了了。
华服旗髻,环佩叮当的小猴儿一阵碎步上前,低眉颔首,屈膝施礼,兹一眼瞧上去,那怎叫一个端庄持重了得?
“给王爷请安,僧王有礼。”
摊开双手,挑眉瞧瞧自个儿手心横切的两条线,小猴儿撇撇嘴儿,摇摇头,在进了院子前,翻了个白眼儿,来了一川剧大变脸,换上了一副矫情的‘谦恭’的模样儿。
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可那一得分多大的‘恩’,二得分是嘛人,就她们这种人么
再者说,当日他虽留她一命,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那都是基于她只是一闲散混混儿的基础之上,若说她是昔日‘叛国罪臣’石敢的女儿,石猴子并不敢保证自个儿的脑子能否还能好整以暇的在脖子上架着。
延珏那主儿虽素日瞧着不着流儿,可却是最精,若被他瞧出什么子午卯酉来,甭说察探,什么都没法儿继续下去了。
石猴子不是傻逼,延珏更不是傻逼,这正是其二。
恁是那僧格岱钦的英雄气她瞧在眼里,可这人如水,善流,善动,深浅不一,浑浊不定,全然相信一个陌生人的,那不是仗义,那叫傻逼。
这其一,她绝对不可能去傻不拉几的跑去跟僧格岱钦开门见山的说自个儿是一罪诛满门的罪臣之女。
小猴儿的脑子里这会儿被搅合的一团乱,可说到底,有两件事儿她始终是心明镜儿的
如果
那把阿玛亲手锻造,从小她佩戴在身的匕首他会认识么?
还有她的那把蒙古剔,究竟是他随口的‘推脱’政治,还是另有深意?
如果他知道,那么他在这其中所扮演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当年的事,他究竟知道多少?
而那所有的疑问都关于一个人僧格岱钦。
石猴子的脑子里,塞满了疑问。
第八三回 天女散花花非花 闺阁说戏戏本戏()
hello~我满血回来了,可还记得咱~
“嘶烈货,你觉不觉得咱两口子之间秘密太多了?”
小猴儿攥刀皱眉,还在怔楞,却瞧着此时那主儿只懒懒的扬着手中的‘信卷儿’,狭长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儿,故作愁容的道。
怎么如今看来,那眉眼之间除却漫不经心却没有丝毫醉态?!
不是去了讷敏的屋儿么?!
丫的,不是醉了?!
没错,但见那塌上半倚着方枕,长腿儿叠摞,拿着信卷儿,挑着眉眼一派悠哉的男人,不是延珏又是谁?
“怎么着,这大半夜的,你这塌上,除了爷儿还能有谁?”
此时轻谩的声音慵懒的响起
“谁!”小猴儿反射的一跳,随手抓起那剔刀,一把拨开那身后帐幔,甩掉刀库,刀刃向前,目露凶光。
就在塞信卷儿的时候,她都没瞧清楚怎么回事儿,只见自个儿手中的信纸嗖的便被一只修长的手扯走。
说时迟,那是快。
然
小心翼翼的把那信纸再度打卷儿,小猴儿拿起那空心儿刀把,想要把那证据再放回原位。
想必,僧格岱钦并不知道这把刀的真正秘密。
幸好,证据还在。
小猴儿伸进去两根手指,试探的把里面藏的东西夹了出来,只瞧着那完好无缺的信纸,她方舒了一口气
而这会儿小猴儿将那刀丢到一边儿,赶忙捡起刀把,但见那不过三指粗的刀把里,竟是全然中空!
只稍稍向下一推,但见那铆钉一动,那刀把竟咔嗒一声,掉了下来,与剔刀分了家!
借着光线,小猴儿将刀横在眼前,却没有抽刀,而是去摸刀把上的一颗不起眼的铆钉。
兹一想,她便一个灵巧的翻身下地,趿拉着鞋,拿着那盏室内唯一的煤油灯,将其摆到里间儿床榻旁的檀香木架子上,随后自个儿连那捂的热的慌的雪貂裘都忘了脱,只一屁股坐到那床榻边儿上,拿出那从僧格岱钦身上顺回来的蒙古剔。
已过子时,想必都已经睡下了,如今这屋儿,除了鬼,也不会再来嘛人了。
借着煤油灯微弱的火光,再瞧瞧那炕架上的洋钟已经指向正北方,小猴儿揉着太阳穴侧耳听着,只闻除却那洋钟时针的嗒嗒声,周遭可谓是一片安静
“喂~”扯脖子又是一声,仍是无人应。
“谷子!”小猴儿扯脖子唤了一声,然半晌,无人应。
呦喂!瞧她介喝的!竟把介折腾一晚上的目的给忘了!
“操,让一梦吓介逼样儿!”小猴儿啐着,想要拍下脑袋,然,这手才要抬,却发现竟是麻痒的动弹不得,而那其中早已握热的金属质感让恍然想起
心猛的一颤悠,小猴儿猛地一睁眼,对折的坐起来,一股子许久不曾有过的慌乱袭来,她下意识的扫向那屋内唯一的一盏煤油灯儿,看着火光跳动许久,才匀速着呼吸顺着气儿。
啊!
梦中的小猴儿不知,下意识去蹭自己的脸颊,然当那眼底的濡湿尽数蹭在手背儿上时,却是一片猩红
她哭了么?
延琮捧着她的脸,用那世间最好看的眸子看着她,怯生生的说着,“墩儿,别哭。”
不知跑了多久,他们终于停下。
闷驴蛋就那样拉着她的手可劲儿跑,跑啊,跑啊……
血红色的月光下,空旷的大草原上,便是草树摩挲的沙沙声,狼群吼叫的‘嗷嗷’声。
梦中,她又回到了十年前,归化的那个夜晚。
只消片刻,便睡了。
天旋,地转,眼皮发沉,胃酸的疼,四肢无力,恁是脑子里告诉自个儿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可一旦摊在了炕塌上,眼皮上下一耷,竟说什么都睁不开眼。
遂,小猴儿喝多了,真的喝多了,这种感觉可以说在她自立门户后,便再也没有了。
先不说那僧格岱钦并不是说糊弄就糊弄的人物,就兹说她身后那一纵王府的奴才在,若她不是真的眼睁睁下肚七八壶,谁会真的相信她醉了?
她借醉靠近是真,她借吐来制造混乱也是真,可她喝多了真真儿还是真。
咱这一不是传奇,二不是唱戏,三不是咱猴儿胃有毛病
嗨,我兹管说
诶,咱猴儿恁精,知道借醉靠近僧格岱钦,借吐来制造混乱,继而偷刀,那这会儿是不是装睡啊!
列为看官定是想问了。
当然,那些都是后话,咱们接着说现在。
这话说的没错儿,有的人生来为烛,命定自我燃尽,只为照亮别人,谷子之于猴子正是这一种人,她这短暂的一生,有喜有悲,有荒诞有滑稽,然过往种种都有如烟消云散,她这一生之诚挚,终究只为猴子一人。
摘着小猴儿头上的扇形冠和首饰,谷子摸摸小猴儿油光可鉴的发髻叹叹气道,“你这猴儿,就算你不愿意让我涉险,可你若有事,我又岂能看着?”
然她若只字不提,她也绝对不会问,这是这些许年来二人的默契,可恁是默契,谷子心里也总是有些不是滋味儿。
想着这一晚,这猴儿的几次不对劲儿,她却不道知为什么,谷子心里都微微发酸,精明如她,又岂能不知小爷儿待僧格岱钦绝非路人甲乙?
猴儿依然睡自个儿的,鼻息酣畅,当然,除却那拧紧的眉头。
见猴儿一动不动,谷子接着嘟囔,“你说你喝这么做什么!人家喝茶,你喝酒,自个儿求醉,什么劲儿啊!”
“嗨!你”谷子气的直跺脚,“我说才刚还有一点儿清醒,怎么这会儿又迷糊上了!我说你到底是醉着还是醒着啊!”
这一扯两扯的,不过是白费力气,她累的肩膀头子疼,小爷儿却是悠哉的闭着眼睛打着轻鼾。
“呦喂,小爷儿,你就脱了吧,这屋里儿这么热乎,这么就睡了,待会儿再捂坏了!”待屋里人都褪下了,谷子郁闷的扯着猴子身上那雪貂裘,可她力气哪里大的过她?
被谷子连着灌了三碗解酒茶后,小猴儿倚着炕几上的金丝织锦垫儿打着嗝儿,因那室内燃起的炭火盆儿和不肯褪去的雪貂裘,热的那原就醉熏熏的脸绯红一片。
少时,槐暖轩内。
瞧着那点头如捣蒜,跑腿儿如撒鸭子的春禧,谷子翻了一个白眼儿,心叹这真真儿是烧火没柴火,拿狗尾巴花来凑啊!
“诶!”
“呦,瞧我!怎还等你开这口。”那银扣儿失笑,赶忙回来跟自个儿姐姐一边一个的搀住了腿有些软的小猴儿进了屋,剩下谷子揉着尖酸吃痛的肩膀头子,挤眉催着那呆楞在前的春禧道,“看什么,傻蹄子,快去!拿解酒茶来!”
“姐姐慢着。”谷子忽的唤道,见银扣儿扭身儿,她又笑笑杵着人堆儿里远比众人矮小的春禧道,“这等小事,让这矮蹄子去!我这扛了一路,肩膀上伤口实在疼的紧,姐姐说什么也得换换我。”
“怪不得。”银扣儿了然的点点头后,又道,“你们先扶福晋进屋儿,我去备解酒茶来。”
知她们姐俩跟这儿套话儿,谷子堆着笑脸,只道,“今儿爷儿高兴,福晋便陪着多吃了几杯。”
片刻,金银扣儿端着茶盏上前伺候着主子漱口,只见小猴儿一张脸因为过度呕吐而满是胀红,直叹道,“福晋平素酒量不差啊,今儿怎么吐成这样儿?”
谷子一瘸一拐的才跟上,就赶忙边顺着猴儿的背,边喊着“快拿水来!”
却说咱猴儿在谷子的搀扶之下,是好一番晃晃哒哒才到了自个儿的院子,一堆奴才丫头披衣服趿拉鞋的迎上来,一口一个主子,个个一脸着急,结果还没等到跟前儿呢,只瞧着小猴儿是脸一白,嘴一鼓,一阵飞腿儿小跑,拄着院儿里那老槐树便呕,呕的吐了起来,但见那酸臭的一堆儿是青红交加,荤素搭配,好不恶心。
好,这厢说到此,咱接着瞧咱猴儿那厢。
……
……
“不用拿了,都退下去吧。”
“爷儿若不醉,又怎能留宿在此?”
那婆子再转过身听吩咐时,只见那正用手绢给主子爷儿擦着脸的讷敏失神的一笑,那笑中满是自嘲。
“是。”一婆子得令忙要去取,然就在要跨出门槛之时,忽听身后讷敏又唤住她,“慢着。”
给延珏垫了垫引枕,讷敏拭拭自个儿头上的汗,吁了一口气儿吩咐道,“去拿些解酒茶来。”
当讷敏吃力的架着那远比她高出很多的延珏,在几个丫头婆子的帮忙下扶到床榻时,身子羸弱的她已是汗滴点点。
当然,今夜无风,也无雨,品茹居里一片宁静,星光点点,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