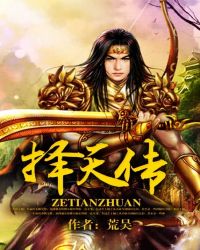痞妃传-第20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猴儿眼圈红了,却没有再哭,她转过头来,看了一眼延珏,扬起嘴角笑笑,转过身对那父母的牌位默默念道:阿玛,额娘,这就是我嫁的男人,你们可放心了?
“起来吧。”延珏从她手里接过那香火,插在香炉上后,把她笨拙的身子扶了起来。
彼时的于得水早已错愕的忘记了喊号子,是小猴儿自己说的:“该夫妻交拜了吧。”
延珏笑的邪气:“怎么着,就这么着急跟爷儿拜?”
小猴儿也笑,噙着泪的眼睛像是两个闪耀的星星,她看着眼前一如既往漫不经心的延珏,她忽然吃力的弯下身子,拔出绑在小腿的匕首。
刷的一声铁器磨擦声,听上去格外清晰。
“诶,你过来。”小猴儿扬着刀,利刃闪着寒光。
“干什么你?谋杀亲夫?”延珏玩笑着,全然没有点儿怕的。
当他走近时,却见小猴儿一把扯过他的手,笑着说了句:“忍着点儿。”
“嘶——”手掌心的那条断掌被刀划出一条血线时,延珏吃痛的倒抽气,他诧异的挑眉看着小猴儿,却见小猴儿摊开手掌反手用那把匕首,二话不说也划下一条线。
鲜红的血滴滴砸下来,那般刺眼。
“你疯了你?!”
“嘘,你别说话,听我说。”小猴儿打断他,走向他,用那坠着鲜血的手掌,抓住他的,两个因断掌阴差阳错走到一起的人,如今又自这两条断掌中渗出的血气交融在掌心。
一个滚烫,一个冰凉。
小猴儿笑着看他,用罕见的万般正经的眼神,她一字一字清晰的道:“避暑山庄那晚,我曾跟你说过,若是我石猴子没有那血海深仇,我这条命都是你的。”
延珏玩笑不在,一双狭长的黑眸直直的盯着她。
小猴儿扭头看看那身侧的父母牌位,笑笑道:“阿玛、额娘,能做的我都做了,恩怨纠葛,到此为止吧。”
延珏周身一紧,接着,他听到了这一生最美的诺言。
“延珏,今天起,我石猴子的命,是你的了。”
……
月上柳梢,银丝照地,彼时折腾了一天的几人都睡下了,唯剩蝉鸣、蛙语。
没人知道,阿克敦是什么时候起床走到院子里的,当披着衣衫的阿克敦,看着那仰躺在院中摇椅上双手抱头,仰头看星星的延珏时,轻易便捕捉道他眸中一天都未曾退却的深邃。
那深邃中,有幸福,有悸动,更多的是一种更为沉着的东西。
“怎么?觉得骗她心里过意不去?”阿克敦倚在旁边的歪柳上,自然的说着。
延珏没说话,涩笑不语。
阿克敦也叹了口气,半晌道:“算了,何必想那么多,再怎么说,您这俩月也没白折腾,她不是放弃了报仇么。”
延珏长叹一口气,看着月亮,眼神清冷,仍是没有说话。
“怎么了?后悔了?”阿克敦问他。
“后悔?”延珏笑笑:“当然没有。”
说他卑鄙也好,攻于心计也罢,怎么都好,延珏本就是个凡事算计三分的人,有了问题就要解决问题,逃避不是办法。
亡命天涯……呵,许是个不错的选择,却不是他的。
他不争权夺势,不代表他会放弃这些,他虽任性,却从来有底线,这次闹的这么大,他不过是想跟两个他都无法舍弃的人打个赌。
给皇阿玛的密信里,他写的清楚:阿玛若容她,儿臣速归。
而对于这烈货,他是什么办法都用尽了,真心也好,计谋也罢,通通无法断了她心中的那个‘仇’字。
既然硬的不行,他只能来软的。
恁是她一颗心硬成铁,冷如冰,说到底也是个女人。
她会对六哥那般毫无保留的好,说穿了,也是这‘愧疚’二字,既如此,他延珏何尝不能也在这‘歉疚’二字上做功夫?
她心中放不下家人,他就给她家人。
不过是一跪,他走不走心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吃心了。
延珏从来不是什么良善之人,他既然死了心要她,就必须要个完全的她。
“爷儿啊,您这苦肉计,狠哪,瞧瞧给您自个儿熬的,便是我这一早知道的人,都瞧不出个‘戏’字来。”
“我几时说是做戏了?”延珏笑笑,他自己心里清楚,管他初衷为何,日子是真的,心更是真的。
这段时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阿克敦笑笑,问了句:“什么时候返京?皇上瞧见那**可是气坏了。”
“不会的。”延珏扯扯嘴,道:“谁若小瞧了皇阿玛,定是要倒霉的。”
可不?阿玛若真能把这点事儿放在心尖儿上,他又怎么可能动了这刀去捅他?
一旁的阿克敦不再言语,想着主子临走前嘱咐他交给婧雅的那封信,忽然觉得脊梁骨冒着凉气。
彼时他看着月光下周身清冷的七爷儿,竟觉得寒意阵阵。
对身边之人尚能谋心至此,其人可怕真真可怕之极。
……
------题外话------
昨儿传了30点,不知为啥,更了就27点,我就纳闷了…。
第五六回 完全版看过的再刷一遍吧()
若是有仙人来扫地,定是会扫到一地的眼珠子。
在阿克敦、精卫几人小住几天后,他们都给自家爷儿吓着了,我去,这谁啊?
打小一块儿长大,您甭说十指不沾阳春这么矫情的词儿,就是简简单单的‘上手’俩字儿,他们也没见过啊,可您瞧瞧——
“于得水,那汤的火可看住了,要文火,别太猛了~”
“于得水,别忘了把鱼给喂了~”
“于得水……”
嗬,甭说七爷,就说于得水这自小跟七爷一块儿吃香喝辣的长这么大,这些个粗重活他都不曾干过,可如今?
“主子爷儿,瞧您这样奴才心里不好受,您这是何苦来呢?”给延珏剔头发茬子的时候,瞧着爷儿那晒的黑上许多的一张俊脸,于得水没出息的抹抹泪儿。
“哭你大爷啊。”延珏一张嘴,就是一股子小猴儿味儿,接下来一句话,让于得水的眼泪更甚。
“别哭了,憋着点儿,你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这话啥意思呢?
是的,就是那个意思,等他们几个攒攒热闹办了喜事儿后,如今都有任职在身的阿克敦、精卫得走,而于得水、谷子得留下伺候。
可不?
眼瞧小猴儿就要生了,他还真能两口子憋家挤崽子不成?
几番听这几个人叽叽喳喳,说这说那,小猴儿的眼珠子也掉过几次。
先说就是那果齐司浑之死,就连谷子说起时,也是一番惋叹:“说到底,这果相道是个程婴之辈,到头来,忠义也算都成全了。”
小猴儿当然不认识什么程婴,可果齐司浑的死她却实没什么感觉,谈不上大快解恨,也谈不上同情惋叹,道是在听说是那陆千卷出卖他上位后,有些同情仲兰。
其实在她知道当年的那些事儿的真相后,她就没那么恨仲兰了。
有时候想想,她也是个倒霉的,别说是那时一心敬父的仲兰,就算是她石猴子也一样,在那个当下,谁会真为了是非黑白推亲爹进火坑?
小猴儿从不是个大仁大义之人,她比谁都清楚,很多问题,没有是非黑白,只有立场问题。
自然,除却延珏这相当了解保酆帝的心中有数,所有人自然觉得那陆千卷是个不仁不义的宵小之背,说起他近日扶摇直上的时候,尤其是仁义为本的精卫,骂的可谓叫一个面红耳赤。
可骂着骂着,就渐渐不对劲儿了,因为但凡有点儿心思的人,都能瞧见那一直叽叽喳喳的谷子越来越蔫儿。
阿克敦一直挑眉看她,神色间虽是玩闹,却是关心不掩。
谷子咬着下唇反瞪他:“你瞅我做甚?”
“瞅你好看呗~”阿克敦嬉皮笑脸,一张狐狸面经京城的好食好水的一喂,褪去了几个月征战西北的尘土味儿,怎么看怎么精致,怎么看怎么像延琮。
当然,这许是小猴儿心中隐秘作祟,别人瞧来,像也没什么不对劲儿,再怎么说,他们到底是姑表亲兄弟。
小猴儿原就担心的问题,到底是发生了,她只瞧着这阿克敦和谷子的逗来逗去的,越看越上火。
也不知道是不是最近老七恶心她恶心多了,以至于她那根先天缺的弦儿补好不少,她一眼忘穿,谷子这回又掉进坑里了。
而且这个坑,远比从前那个深上许多。
自打她们几人回京后,谷子这已随着七福晋‘消失’的人,虽说是个没什么人盯着的丫头,但也不能大摇大摆的去住睿亲王府,于是故计重施,她又被阿克敦带回了府上。
照旧,她仍是贴身大丫头一般伺候他吃吃穿穿,管东管西,谷子是个管家能手,阿克敦也由着她管来管去,闲暇时,俩人吃吃茶,逗逗嘴,追忆追忆那跑路二人的往昔,种种相处两月,以至于原就情萌的谷子,又是一头栽了进去。
“吃一百个豆不嫌腥,说的就是你介种人。”小猴儿嘴刁毒的完全没给她面子,可谷子也是嘴硬,那点儿心事儿全画脸上了,可嘴上还硬辩着:“谁会念着那风流种!”
小猴儿故意把话反过来说:“人家堂堂一品领侍卫府长房长子,有才有貌有官阶,不风流才有毛病,我介不是非得拧着你,你若心里受得了当个小妾,那眼前一个个新娘们儿晃悠半辈子,他到也不失为良配,反正我说你也不听,你要是真想,我奏成全你,跟他说说去。”
“说什么说,别诨闹了!”谷子给她说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她这日日与他相处,又怎不知他对天下间的女子,都是一种好法儿!
可说是说,女子毕竟是女子,女子都爱幻想,自己在所爱的男人心中是否是与众不同的?
否则为何他行为轻佻,夜夜招女子侍寝,却从不对她动手动脚?
是尊重,还是在等她的一个态度?
说真的,在那日皇上口谕,给他指婚时,谷子心里虽不太舒服,却没过多的难受,她便是这门庭逃出来的人,她比谁都清楚这些大门大户的那些个规矩,诸如阿克敦这种家门长子,娶个门当户对的媳妇儿,名门贵族的平妻,那都是再寻常不过了。
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那都是女子哀怨的诗中所盼。
她谷子也盼过,也卖力争取过,可倒头来还不是卷回了千百年的规矩?
对她这种‘曾经沧海’的人来说,她反到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了,就是这般随波逐流,她的心里,却莫名其妙来了这么个曾经让她恶心不已,势要远离的人。
小猴儿当然不可能看着她跟那闹心扒拉的自我拉扯,反正恶人她是做惯了,也不差再丢一个土雷给她。
那日几人吃火锅时,阿克敦正拿着皇上委任精卫做从五品委署鸟枪护军参领的事儿热络的损着他。
“鸟人管鸟枪,皇上英明啊。”
“滚边儿去!你爷爷我再怎么也比你这狐狸强,哼,正五品步军校,说来好听,说白了还不是持刀清道的!”精卫也不甘示弱。
“清道怎么了?落得清闲,潇洒自在,诶,黑鬼,你现在管着那么多鸟枪,上门瞧媳妇儿的时候,没给打两只鸟儿玩玩儿啊~”
精卫哪里说得过阿克敦这京城第一侃爷儿,三两句就给他气的脸红脖子粗的,恨不得把他脑袋揪过来插铜锅里给涮了,可阿克敦那嘴可不消停,他没完没了的接着跟人损他:“诶,主子爷儿,您是不知道啊,呦喂,果府出事儿那两天,这傻狍子还跑去求见人家大小姐去了,好话我都嘴皮子磨烂了,跟他说了一百遍如今果府再不复从前,反正爷儿是口头下的聘,硬说也不算数,他道是好,压根儿不听劝,愣是去求见人家了,您说,他是不是脑子有泡?”
精卫不服,憋着黑脸顶他:“你以为我是你呢!这口头聘礼也是人尽皆知的,我不娶她,不是磕碜人呢么!”说完这句,精卫又实成的骂他一句:“你就是造孽太多,活该你娶个全京城最丑的媳妇儿!”
阿克敦一脸不在乎的玩笑道:“得,甭损我,你还不是收个瘸子。”
“瘸子怎么了?你丫不瘸咋的?”精卫嘴难得还这么快一回,然才说出口,一眼扫到颇为尴尬的谷子,就后悔了。
“丫头,我不是说你,甭往心里去。”实在人说实在话,就是越描越黑。
谷子笑笑:“两位爷儿逗嘴,掺合我做甚。”
这番玩笑哈哈而过,待半晌小猴儿插着空,拿筷子指着谷子,没头没脑跟阿克敦来上一句:“诶,要不别让她跟我这儿了,你给带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