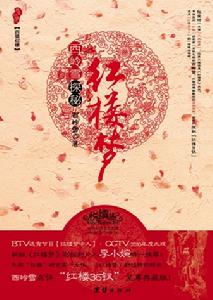西岭雪人鬼情系列:女人都不是天使-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西岭雪
女人都不是天使 第一部分
一个真正有钱的男人A(1)
在雪地上行走的人看不见自己的脚印是很惶恐的。
不敢回头,却频频回头,心中的恐惧在积压,膨胀,终至撕裂。想号叫,喉咙似被掐住了,声音窒息扭曲至不可闻,犹豫着是不是要停下,却终于忍不住狂奔,哪怕前面是万丈悬崖,也宁可纵身而下,在毁灭中享受尖锐的痛感,于死亡里体味真实。
然而没有,奔跑的方向只是奔跑本身,雪野无边无际。
每一步,都踏不到实处……
我只不过想毁灭。
人生已经没有什么可追求可期待的了,奇迹永不属于我。
我只不过想毁灭。
昨夜,那个女人又来了,大红缎袄,高绾双髻,很古怪的装扮。喃喃地诅咒着。
其实我从没有见过她,不过,我知道她是谁。
她的面目模糊不清,有血从眼耳口鼻缓缓地流出,腥红黏稠,渐渐弥漫开来。
她的声音,那恶毒的血腥的诅咒,敲击着我的耳膜,在雪野里追逐着我。在她的诅咒声中,漫天的大雪都变得腥红,如血。
为此我将音响开至最大,希望盖过她的声音。
“Sunday is Gloomy; My hours are slumberless。”
我听的歌叫做《黑色星期天》。一首关于死亡的歌,我的挚爱。
幽灵的声音。从地底挣扎着倾诉,又似呼唤,求着,找人与她同行。
传说里找替身的水鬼,如果会唱歌,便是这样。
我抱膝听着,坐在V8包厢的角落里,抽着烟,倚着音箱。声音先到达我的背,然后才是耳朵。
先感到,后听到。身心的双重震颤。
烟头在黑暗中闪烁。
星微的光亮。因为那一点点的光而使黑暗愈发深沉。
也只不过是夜里八九点钟吧,室外应该是灯火通明的。但是时间在这里是静止的,密封的包间,只有门没有窗,四周还要拉上深紫色落地厚丝绒帘子,既为装饰也为隔音。
我像蛹一样被裹在深紫色的厚丝绒的茧里。《黑色星期天》唱得再哀伤也不会打扰别人的情绪。
V8靠近走廊最深处,最小,也最潮湿。黑暗中坐在地毯上听音乐,总觉得四周有无名菌类在默默滋长,而另外一些生命在枯萎、腐烂。除非客满,否则很少会有客人点这一间。
如果有事,服务员会知道到这里来找我。不唱歌也没有客人请的时候,我总是在这儿的,吸烟,听音乐。偶尔也会骂人。
在“夜天使俱乐部”里,我表面上是歌手,暗地里则是不加冕的副经理,老板高生身边的红人儿,操生杀大权。
连经理秦小姐也要畏我三分。
“夜天使”,夜里的天使,以灯光和音乐做翅膀,舞在醉生梦死的嫖客的笑影里。
世上人,无非嫖客与妓女。我姥姥说的。
她说弄明白了这一点,才好做人,不然总是处处碰壁。
我就是在碰了壁之后才明白的。
明白了,却依然不肯信。总有例外吧?总会有的。
曾经以为高生是个意外,无关财色。
我生日那天,他从香港航运来刻有庄子《秋水》全文的巨幅玉石屏风。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岸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
我很开心,拼命地张开双臂去拥抱画屏,闭着眼睛大声背诵:“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笑于大方之家……”
高生问:“每个人都有物欲,有些人集邮,有些人集火柴贴花,有些人攒钱,有些人收藏美酒或老爷车……但是你,你的嗜好是搜集各种版本的《庄子》,为什么?”
我不答,只抱着屏风摇头晃脑:“北海若曰:井龟不可以语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道者,束于教也……”
他不放过我,仍然追问:“有人说通常执著于物欲的人,是因为对生活没把握,所以才渴望拥有,借实在的东西来安慰自己。你呢?你为什么这样喜欢庄子?”
我仍然笑着,闭着眼睛接下去,“高生不可以语庄子者,吝于情也。”
他笑起来,忽然将我高高举起,恐吓道:“你不说,我就把你从楼上抛下去。”
是百花楼。
听起来像个妓院的名字,位于广东梅州郊区的百合花园。
百合花园别墅区,每一幢都有一个很好听的惹人遐思的名字,百草堂,百鸟轩,百尺阁,百步亭,百色坊……我们这一幢,叫百花楼。
对物的拥有是生命最真实的痕迹。无论是别墅,还是庄子,都只是一种占有。
我占有庄子画屏,高生占有我,我们占有百花楼。
百花楼上,庄子屏前,醉在龙飞凤舞泼墨如画的《秋水》里,我以为高生是与众不同的,至少他对我用了心。
是在那夜委身于他,自以为并不是卖。
但是后来知道,一切仍然是场看起来挺美的交易,交易终究是交易。
V8的门轻轻响了一下,Shelly走进来,通知我演唱的时间到了。
我盯视她,心里犹豫着要不要找个借口刁难。
但是在我还没有拿定主意的时候,她已经转身走了。
我有些悻悻然,捻灭烟,在手袋里取出镜子来补妆。
Shelly是我在俱乐部里惟一的对手。我一直想降服她,让她像其他人那样对我小心翼翼,随便她在背后怎样骂我都不要紧,但是当着面,她必须对我毕恭毕敬,俯首称臣。
可是不行,无论在任何人面前,经理、老板、客人,或者我,她都是这副不卑不亢的样子,像个贵族。
呸,扮高贵,何必来这种声色场所打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经理助理而已,就是经理也对我谦恭有加,她凭什么可以永远这样从容不迫?
走出V8,领班阿容立刻满面笑容地迎上来,甜甜地叫一声“Wenny”,话音未落,笑影儿已没了。
就冲这一点,我猜她早已过了二十三岁。
可是她赌天誓日地说自己只有十八。十八?鬼才信。这里的女孩子,个个都说自己只有十八岁,但是眼角的鱼尾巴沾水都能游了,不化妆像主妇,化了妆像怨妇,就是怎么看都不像少女。
很多人想尽办法除皱祛斑,可是,有没有一种护眼霜可以抹上去让眼中沧桑尽去,清纯无邪?
睁着一双厌倦瞌睡的眼,就算把脸上的粉抹得再厚也盖不住那股风尘味儿。
在驻颜有术这一条上,没有人可以比得过我们云家的女儿。
代代都是不老的妖精。
姥姥算年龄怎么也有七十了,可是看起来只像五十多;妈妈该有五十了,可是说她三十岁也有人信;而我,连我自己都快说不准自己的年龄,因为妈妈从来不肯承认自己的真实年龄,连带我的年龄也一改再改,如今,我对外声称自己十九岁。
十九岁的脸,二十九岁的身体,三十九岁的灵魂和心。
阿容冲我鬼鬼祟祟地笑,很亲密的样子:“Wenny,上了台,别忘了注意一下T2穿深色西装的男人。”
“怎么?”
“那是吴先生,他已经来了三个晚上了,是大主顾。”
“梅州会有什么大主顾?左不过哪家酒店经理罢了。”
“正是大世界假日酒店的,不过不是经理,是董事长,香港人,梅州是他祖籍,像大世界这样的酒店他在全世界至少有十几个,是真正富翁。他每次给公关的小费都三四百,光是猜猜拳喝喝酒,连包间都没进过。”
“没进包间就给三百块小费?”我微微上心,这样子才是真大方了,“他都点过哪几个小姐?”
“从没点过,都是秦小姐安排给他的,安排谁就是谁,他不挑不拣,见谁都散钞票,整个一散财童子。那几个公关为了争他都快打起来了。”阿容的声音里充满妒意,恨不得立时三刻就脱下工装去做公关,可以赚那三百元小费。“Wenny,要我说,你把那个吴先生抢过来算了,只要你一出手,那些公关算什么,吴先生瞄都不会瞄她们一眼,看她们再轻狂?”
我笑了。在俱乐部里,表面上虽然等级森严,总经理、经理、经理助理、总管、主管、领班、服务员和公关小姐、打杂的小弟小妹,一层层分工明确,秩序井然。但是说到底,是谁最能拉拢客人最有本事,赚到钱声音才大,所以阿容虽然是领班,对比她低半级的红小姐却只有瞪眼吃干醋的份儿,看不得别人赚小费,自己又没本事,便巴不得一拍两散,出动我去杀一杀那些小姐们的威风,让她们别太得意。
梅州的款爷不少,真正的富翁却不多。但是富翁不等于“凯子”,能不能钓上他,要凭技巧。
我有一点点技痒。
阿容察言观色,打蛇随棍上:“刚才那吴先生特意下单子点歌,说很喜欢你唱的《黑色星期天》,请你多唱两遍。”
“没问题。”
一个真正有钱的男人B
今天如此绝望
我的时间从此无边无际
我爱;我沉睡在黑暗的底层
白色的小花不能唤醒你
悲伤的黑色灵车哦,它们引你去哪里
天使们不肯将我还给你
如果我想要参加你,他们会生气吗
绝望的星期天
《黑色的星期天》,我自己译的歌词。
这是一首死者唱给生者的歌。每当唱起它,我的身心就完全沉浸在音乐的凄凉无奈中,不能自已。我的灵魂出窍,追随着白色小花黑色灵车远去,红尘中的一切将不能再诱惑我,羁縻我,摧毁我。
我知道我唱歌的时候是最美的,尤其全情投入时,“会有一种遗世独立的圣洁感”。这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何教授告诉我的。哦,何教授……
今天如此绝望 我消失在暗影中
我和我的心都已经决定面对结束
鲜花和祈祷文如此悲伤
我明白;让他们不要哭泣吧
让他们看到我微笑着离去
死亡不是梦;我在死亡里爱抚你
我的灵魂祝福你直到最后一次呼吸
绝望的星期天
英文唱完唱中文。一曲唱罢,没有人鼓掌。
我非常满意。在灯红酒绿的夜总会里,掌声和口哨都不代表什么,脱衣舞女郎站上台不必表演也会有吁声。沉默的聆听才是最好的赞美。
他们全被我感动了。
只有这一刻我是活着的,是他们的主宰,凭借我的歌声,而不是身体。
我讨厌用身体赚钱。可是逃避不了。
毕竟用身体赚钱比用头脑赚钱更实惠,更快,更多,也更直接。
我喜欢直截了当。
无需经过任何引见或邀请,下了台,我直接坐到吴先生身旁。
他微微惊讶,更多欢喜,站起身子来拉座位。他的朋友起哄地说欢迎,争着递烟,递酒,递瓜子儿碟子。
我点燃了烟,同一干人轻轻碰杯。
坐在一旁的陪酒小姐的脸涨得绯红,我看也不看她一眼,推开碟子说:“我从不嗑瓜子儿。”
我从不嗑瓜子儿。
因为妈妈说过,瓜子儿和妓女是分不开的,是她们的道具、营生、手段和标志。
儿话的尾音使吴先生更加惊讶:“你是北京人?”
是。我吐出一口烟,并不顺着话题往下说。
多话的女人总是容易被看轻。名正则言顺。没有地位的人最好少说话。
如果不能为自己辩解,那么沉默也是一种选择。
一个真正有钱的男人C(1)
收工后,吴先生约我去江边宵夜。
江上有很好的月亮,和灯光彼此争辉。江边情侣如云,邻座有人在猜拳,“孟加拉呀孟加拉”,叫得很大声。在别人眼中,我们未尝不是一对情侣。
我点了桐花雀、椒盐黄鳝、牛奶炸菠萝,还有一只海鲜盅。
吴先生扬眉:“你很能吃,不忌油炸荤腥,年轻人很少这样。”
“很少哪儿样?”我两只手一头一尾地掐着黄鳝,用牙齿撕着吃。吃相无比难看。如果妈妈看到,一定又会训斥我太不像一个淑女。
淑女,妈妈苦心孤诣地想将我培养成一个淑女,可是现在的我,从头到脚,哪一点儿像个淑女。
我不过是个歌女。在夜总会转场驻唱的小歌手。优伶的一种。而且尚未跻声名伶的行列。
名伶叫歌星。可以灌唱片上电视。再成功点的叫艺术家。
但是无名之伶,就叫歌手,或者直接点儿,叫歌女,甚或歌妓。
所谓十伶九妓。说得对极了。而我是那十分之九里面的一个。
想到母亲使我感到由衷的恨意,而想到“妓女”这个词则使我痛快。
痛,并快乐着。这种词是为我这种人准备的。歌者的快乐与痛苦从来都分不开。
我唱歌,逢迎客人,玩弄翻云覆雨的小手段,换取我想要的香车、香闺、香水、香衣,一应生活所需,皆来自男人,来自我的歌声与容颜。
但是吴先生,他约我来江边宵夜,目的当然不止是宵夜这么简单,他感兴趣的,究竟是我的歌声呢,还是容颜?
这有很大的区别,决定了我要采取的献媚方式——对一个自以为尊重艺术的男人过于主动,他会败尽胃口的;然而同样的,对一个欲望汹涌的男人扭捏作态,也会令他索然无味。
最好的办法,是陪他大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