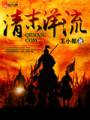再会吧南洋-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千八百多名南侨机工永远地沉睡在滇缅路上。
“可以说,我们南侨机工回国抗战,没有一个人当逃兵,也没有一个人给南洋华侨丢脸!”
这是如今健在的几位老机工在回首那段往事时发出的感言!
1945年,抗战胜利了。幸存的南侨机工自发地组织成立“华侨互组会”,向国民政府提出请求,要求复员。
若干年后,我在查阅南侨机工档案时,无意间触摸到那段历史。沉寂已久的历史档案让我走近和了解华侨,认识了南侨机工团结互助、亲切温暖的“华侨互助会”。
华侨互助会,于1943年9月发起,1944年1月成立。
1942年5月,惠通桥被炸,滇缅公路运输中断。之后,大部分南侨机工无以为业。他们谋生无方,流离失所,浪迹街头,急待救济。热心于侨胞事业的南侨机工及侨胞白清泉、侯西反、胡春玉等,发起为难侨施赠医药。同年12月,又酝酿成立华侨互助会,并呈请备案。1944年1月21日,华侨互助会在昆明南强街福建会馆成立,分九批从南洋归来的机工们在昆明有了“家”。
在华侨互助会1944年的工作总结中,这样写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相继失守。滇缅路中断,侨工陆续失业,流落街头,无人垂顾,侨童无书可读。本会旨在于为华侨和侨工解决困难,热心侨胞展开侨之收容训练。并提出:‘侨应自谋力更生,以侨救侨’”(云南省档案馆44…2…314)。
由此可见,华侨互助会完全是根据当时南侨机工的生存状态,由归侨自发组织的自救、互助团体。
华侨互助会在筹集到救济资金后,用途如下:
1、聘请昆明惠滇医院的陈永祥、周文辉两名医师为生病的侨工义务诊疗;
2、会内设疗养室,由专人照顾病侨的起居饮食;
3、会内设收容所,收容失业侨胞,介绍职业。
设在昆明黄土坡观音寺的南侨机工收容所,人数是逐天增加。华侨互助会还制定出训练概要:
1、智能训练:政治、军事、技术;
2、精神训练:讨论抗战、批评与自我批评;
3、劳动服务:每日一小时;
4、课外娱乐:南洋音乐演唱或演奏(云南省档案馆44…2…314)。
真是巧合,1984年我从学校毕业后,来到了昆明市儿童医院工作。在多年后,当我整理南侨机工史料时,方知昆明市儿童医院的前身就是与南侨机工有一定历史渊源的惠滇医院。难怪父亲在生前谈及我的工作时,老是重复念叨着一句话:“惠滇医院!”我当时是莫名其妙,叹他病糊涂了!
……
在海外华侨呼吁下,在联合国远东国际难民组织的帮助下,经华侨互助会造册登记、核实,国民政府开始安排南侨机工分批复员。
父亲在办理复员登记时就职于空军第五军粮所。军粮所设在昆明柳坝。该所纪律严明,不允许随便外出、请假。在他复员登记表中清楚地写着,回归地——新加坡。毕竟,南洋是他的第二故乡。所发临时护照号码为473201(云南省档案馆92…2…146)。
1947年9月12日,父亲奉命出发在渝蓉线驾车运输物资,错过了大批机工启程复员的时刻。翌年2月5日回昆后,他曾向云南省侨务委员会提交申请,要求延期他的护照。在1948年8月1日,由华侨委员会、云南侨务处刊出的《侨讯》第十六期中,登载了包括父亲在内的留昆81名机工复员名单,要求他们即日内乘机飞抵广州,转香港乘轮出境。而此时,父亲却再次受命出差,在送车到南京的途中,回昆明已是1949年2月初(云南省档案馆92…2…152…8)。
1949年2月19日上午,云南省侨务委员会向空军第五军粮所供应中队发文一份,“希尽可能准予暂缓调遣陈昭藻、林熙庾等,以便等待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广州办事处来人核办处理”。
空军第五军粮所回函:
侨委会云南侨务处:
(1)侨务字第0049大函收悉;
(2)查该库不隶属本队,所请未便照办;
(3)请呈向军粮股洽办。
昆明巫家坝空军供应中队中队长:蒋方锦(云南省档案馆92…3…8…33)。
但是,父亲已经再也没有复员的时机了。
次月,该军粮所郝绍连所长对父亲在内的三名南侨机工说,已没有机会再返新加坡了,要派遣他们随部队前往台湾。
或许是出于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向往,父亲选择留在大陆。
他辞职离开空军第五军粮所,开始了新的生活。
父亲、母亲
留在大陆昆明后,父亲与母亲相识了。
1949年底,伴随着共和国诞生的欢呼声,父亲、母亲开始了他们的婚姻旅途。父亲、母亲年龄相差整整三十岁。
心路漫漫(6)
母亲幼年丧母。过早地失去了母爱,在她的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她的一生都不善于言笑。在她那过于严谨的神态下,蕴藏着女性的善良、淳朴。
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就职于昆明裕成商行。“新社会,要有新知识!”父亲送母亲到文化夜校学习。
“你父亲送给我一支派克笔,上课的时候拿出来,班上好多同学都羡慕。”每当掏出藏在母亲心底的那一份回忆,她的脸上就会闪烁起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那是我们平时很难捕捉到的。
“你父亲身材魁梧,身子特别直。休息天他就穿西装系领带,头发还打上发油,走出去,有点与众不同。”
不知母亲特别爱整洁的习惯是否是从她的婚姻开始。
母亲先后生育了姐姐、我和弟弟三人。
1952年,父亲无职在家。当时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新加坡姑母寄过来的侨汇。华侨事务处派人来家,问是否需要救济。父亲说不想白拿国家一分钱,需要的是一份工作,在任何地区做任何工作都行。
于是,经华侨事务处介绍,父亲来到云南垦殖局蒙自分局做驾驶工作。同年10月,由于工作的需要,父亲连人带车调往森林工业局开远分局,往返于林区运送木材。
父亲在祖国大跃进时期,工作干得不分昼夜。
“我们南侨机工,不管是在国家民族争独立时期,还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都是为国家付之心血的。”这是我在对尚健在的老机工王亚六访谈时,他的肺腑之言。
在父亲的档案中,记录有他的诸多荣耀:1956年参加森林工业局先进生产者会议,得奖章一枚;获物质奖励六次(胸前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1958年到1959年,分别获得安全行车十万公里以上和先进生产者的奖状各一张。
工作单位欲送父亲去疗养,父亲说:“我身体好好的,怎么去浪费国家的钱?”
对那几张无任何装裱的奖状,父亲收藏如宝,直到“文革”中才被撕毁;而那几件印有“奖”字的纯棉内衣,则一直紧紧地陪伴着他的身体,直到临终随父亲化作了一缕轻烟……
那个“奖”字,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童年是在多彩的记忆中度过的。
由于父亲常年在林区工作,很难有机会回家。在我4岁以前,我见不到父亲的音容笑貌。于是,大我十岁的姐姐背上我,从昆明乘上火车,沿途又几次站在路边招手搭车,终于到达罗平的林业局车队。
父亲看到我们姐妹俩,顿时惊喜得发呆了!
“你们怎么来的?”
“只要看到写有‘林业’字样的车,我就招手!”姐姐大声地说。
“我告知他们您的名字,他们都说:‘知道,老华侨!’”
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父亲,从此,留在了我幼年模糊的记忆中。
之后,父亲调到昆明近郊工作。
休息天,父亲偶尔带我们到南屏街当时昆明少有的咖啡店喝咖啡。那一刻,我总是高兴得跟着父亲一路走、一路跳。一次,邻桌的人看着我和父亲的样子,对我说:“小姑娘,你的爷爷真好!”顿时,我的心沉了下去。以后,再也不愿跟随父亲一同上街了。
20世纪60年代后期,父亲被隔离审查了。母亲被迫带着弟弟随时代的潮流下放到了农村。
又要离别。临行前,父亲对母亲说:“凤英,你带着孩子先去吧!我虽然年纪大了,还挖得了地。等我回单位接受完审查,就到农村来,你不要嫌弃我!”“相信我,我不是特务……”
每当母亲回想起父亲的这番话语,她总会鼻子发酸。
我们一家开始了分居三地的生活。父亲回单位接受审查。他的审查一直延续到1973年1月。
母亲带着弟弟在农村起早贪黑地干活,全年所挣工分收入只能维持基本口粮。母亲吃苦耐劳的本领扶持着整个家庭生活。
1975年,在农村的母亲得以落实政策返城了。
次年,父亲退休了。但他还到离家很远的汽修厂工作。每天早晚两次赶公交车,有时被挤得摔倒在地,或是手被车门夹破,但他回家从未有过一声叹息,还哼着他的家乡小调找家务事做……
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红岩》等革命小说成长的我,最大的向往就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我接受多次的家庭出身审查和团组织对我的考验。看着和我一起写入团申请书的同学已经成为一名共青团团员,那一刻,我恨透了父亲。是他影响了我,影响了我的进步,影响了我对组织的渴望……
可生活中,父亲在养育着我。再苦再累,他都默默承受。
每当家里炖汤煮肉,母亲总要把我和弟弟拉到一边悄悄交待:“你父亲年纪大了,让他多吃一点,你们年轻,有的是机会。”
在困难时期,父亲总是抢着吃玉米饭,母亲很无奈。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年过八旬的父亲再也累不动了,躺倒在病床上。
在医院的三个月中,不知何故,医生查房或来人探望,父亲讲的全是海南话。医生用问询的目光回头看我,我学会了简单的海南话。
回家养病的父亲基本不能下楼了。
心路漫漫(7)
那天清晨,母亲焦急地打来电话,说父亲不见了!
我连忙赶到家里,母亲告诉我说,她出去取牛奶,回来就不见了病床上的父亲。实在想不到,久病的父亲居然能走动,而且还下了六楼,不见了!
晨风中;我与母亲四处奔寻。终于在昆明的翠湖公园湖畔,看到了伫立在湖边的父亲。一根拐杖支撑着他瘦弱的身躯,纹丝不动!
“你!你来这里干嘛?”喘息不已的母亲急忙搀扶着父亲。
“我,我想回海南岛!到新加坡!看‘天和堂’!”
听着父亲一字一句地从嘴里蹦出来的这些想法,我和母亲感到非常的惊异。
“好,等你病好了,就回海南岛、到新加坡。”我和母亲劝慰着父亲,慢慢地把他扶回了家。
从此,再未下楼的父亲一直躺在床上深深地惦念着他的家乡,他的第二故乡——直到病故。
父亲走了,留下一张行军床、一只美国军用水壶、一本华侨登记证。
心路漫漫
人们经历过的种种事情,时间久了便沉淀为许多记忆。有些记忆是需要拿出来回放的,并细细回味。酸的变甜,甜的发酸。
人生需要有回忆!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幼稚园的老师特别偏爱我。我的衣裙在当时穿的总是与别的小朋友不同,色彩鲜艳,款式独特。印象最深的是一条紫红色的连衣裤,开口在左肩上有一排纽扣,每次方便,都需老师帮忙。此时,老师就说:“看你这衣着,就知你家与众不同!”
回到家,我问母亲,母亲告诉我:“你穿的衣裙是你新加坡大伯母寄来的,当然就与别人的不一样喽!”
“新加坡在什么地方?”
“听说在南洋,很远很远。”
母亲把她所知的点滴向我输入。若干年后,我从父亲一些往来的信件中得知,新加坡的伯母一直盼着父亲回去,因伯父在新加坡沦陷后不久生病去世,父亲和伯父与两个海南同乡共同投资开办的“天和堂药店”需父亲回去照料。但父亲在两次机工复员时都因被派工作,没有赶上再返新加坡。后来伯母曾来信说,若父亲实在回不去,送一孩子回新加坡也行(伯母身边没有孩子),父亲没有把身边的孩子送过去。新加坡“天和堂药店”的股份和经营全留给了伯母。
……
我的家庭的确与别人的有点不一样。尤其是和我同龄人的父亲相比,我的父亲是一位老人,我出生时父亲已62岁。在我家居住的四合院里,邻居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陈爷爷”。
我家居住的四合院里,共住着五户人家。楼上两户、楼下三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双足被缠成三寸金莲的彭奶奶。她随时穿一身整洁的对襟衣服,说话总是很温和。据说,彭奶奶是个大家闺秀,受过良好教育。她能读书、写字、知书达理,很受人们的尊重。
那年我七岁,在我刚步入校门不久,不明白一家人怎会各居一方。母亲带着弟弟下放到了农村,父亲被隔离审查。
独居的我经常得到彭奶奶的照顾,冷暖、温饱她都会过问。夜晚我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