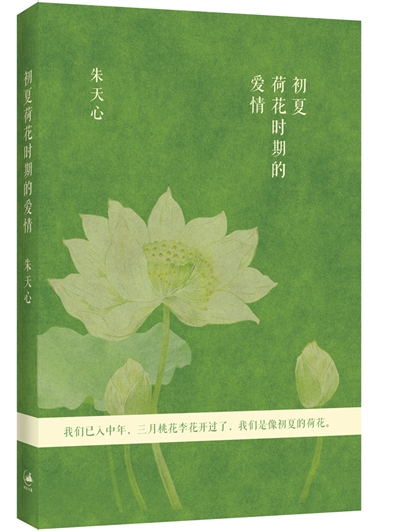荷花香残-第2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给他另一种性质的打击,在目前家庭破裂的情况下,他对不幸事情的承受力几乎已到极限。不管怎么样,他在一步步往上爬。虽仍有树木挡住视线,明知看不到那座山谷却不断把目光投向那个方向,那个山口。现在那个山口好像成了一种关乎他情绪好坏的地方,如果山口处没人,他的焦虑将在瞬间消失干净,并将因之得到更大的轻松甚至是愉快,而若山口处有人,那他将立刻陷入巨大的悲伤之中,然后这种悲伤将与他从家里带来的痛苦混合,再后来的情形将怎样,简直不堪设想。妻子已经背叛了他,他真不希望在这节骨眼上最亲密的朋友也离开他,他的心已经脆弱了,受不了重创。这种担忧使他不再向那山谷方向眺望,而是低下头。这是一种类似于掩耳盗铃式的自欺,以为只要看不见,不幸的事就不会发生。不知不觉山雾加重了,看样子似乎很快就将笼罩整座山峰。山雾中有清新气息钻进他的鼻孔,滋润他的心肺,可他一点不觉得舒服,反而感到恶心,仿佛嗅到了血腥味。落叶乱飞,飞出串串细碎的声音,像人的低泣,很叫人伤感。
终于看到了那处山口。他的害怕成了事实,那里尽是人,有警察把住不让人进,有些好奇心重的青年便悄悄从一处岩石上越过去,想方设法进入山谷。他跌坐于地,酒瓶和牛肉干掉在了地上。酒瓶碎了,清脆的声音向山谷飘去,浓郁的酒香则飘进了山雾中,跟愈来愈重的血腥味融在了一起。那声音是想追问亡灵的苦痛,那酒香则是想探求血腥的意义。可亡灵无语,血腥味惨淡无声,永恒的山峦也陪它们沉默,只有轻轻的风儿,从天边吹来,发出几丝无奈而幽怨的叹息。
直到夜幕降临,他才从地上起来,慢慢向上爬。山口处的人已经散了,也没有警察守了,便走了进去。那间茅房依旧,在晚风中飘着几缕枯草,附近4、50米的范围内到处可以看到已经凝固变黑的血迹,空中的血腥味浓得几乎令人窒息。三具尸体早被抬走,警察仍在现场勘察,他们把茅房翻得乱七八糟,不知在找什么,煤油灯打翻在地,到处散落着诗稿,有的已被践踏稀烂。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还在这里搜查,徐景升认识他,两人打了个招呼,徐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副局长说顾都活得不耐烦了,用斧头把妻子和英妹姝劈了,自己则吊死在树上,昨天下午的事,今天才被人发现。天色完全黑了下来,警察们都离开了茅房。徐景升便去云麓宫找老道,他想老道应该知道一些情况。
老道说虽然我修行多年,老实说这次我并没发现顾都有杀人之心,大概他是诗人,他为了诗在完成一桩上天赋予的任务,道与诗截然不同,所以他的暴虐逃过了我的道目法眼。不过老道还是有些惭愧,话虽如此,毕竟道乃包容万象之物,尤其对善恶本质之透悟为各法各派之学说所不及,而竟未能及时阻止发生在眼皮底下的杀生之罪,实有负于道家之大义,由此观之,人世的修行尚未臻化境,道德经还须日日诵吟、天天研习。徐景升想知道事发前顾都有没有反常言行。没有,反而比平常显得兴奋,老道回答说。徐景升深以为怪,他觉得顾都死前是应该反常的。老道说顾都虽是诗人,但对道家心神向往,又常住山上,与云麓宫仅山谷之隔,更时常和我探讨道家妙义奥理,自然染了几分道气,懂了将欲弱之必欲强之的精玄妙法,化成将欲死之必欲生之的隐术,正因他已明道家法理,所以我以道法参他,却不能参透,正可谓相生相克,呜呼哀哉!徐景升问,这么说他生于道也死于道。老道沉吟片刻,说他生于诗,死于道,再由道化诗,最后以诗入道,他是诗道一体,可谓死得其所,死得其时。
天很晚了,徐景升心里装着三张死去的熟面孔,有些害怕,不敢独自下山,借谈道为名在山上逗留了一夜。次日上午才下山回到文联,他想今天文联里一定热闹,便来到了文联大楼。碰上的第一个人竟是高青莲,她问他怎么夜不归宿。他恼怒地看着她,说我回不回家关你屁事,我又不要跟你睡觉。夫妻就拌了几句嘴,有人来了,都要面子,各憋一口气分开。不出他所料,平常清静的文联今天来了很多人,都是听了顾都的事后来问情况的。文联主席谭谈昨天专程去了山上,晚上又去顾都的家和顾都妻子家做采访,今天还去了市局,刚回来,了解一些情况,对大家做了详细介绍。顾都的妻子要他离开英妹姝,英妹姝也要他离开他妻子,否则就跟他分手,他一直不同意,希望妻子和英妹姝能互相包容,做了长期的说服工作,但那两个女人死活不答应,近来态度更是一天比一天强硬,妻子已经向法院递了离婚诉状,英妹姝也打点好行李,准备移民澳大利亚,他好像很痛苦,给姐姐写信说命中注定这一关是过不去了,他几乎疯了,动了杀心,前天把两个爱他的女人叫到山上,说是喝分手酒,灌她俩半醉,再两斧子劈了,自已吊死在树上。
诗人和作家看待此事的态度泾渭分明,诗人都同情理解顾都,作家一致谴责,评论家则有赞有弹。诗人们认为顾都是为了诗歌事业杀人的,因为这能使他的诗传诸后世。作家则认为顾都完全丧心病狂,是一种极端自私的畸形心理,居然异想天开要两个女人共事于他,只要稍有理智就会知道这绝对不可能,猪也比他有头脑。诗人王业宾对作家们的态度非常不满,涨得满脸通红地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诗圣,我相信他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诗人都会活得长久。他还不时翻着眼皮遥望天空,好像在向他认为准定已升天堂的顾都之魂行注目礼。他知道他的诗已经写完,再写不出更好的诗,就想对自己的诗来一个总的交代,便选择了这种方式,表面他是为情施暴,实际是为诗添彩,虽残酷,但从诗的角度说无可厚非。作家汪兴邦顶着一颗硕大的脑袋鄙夷地说,你这是在为杀人犯辩解,诗人想找死,这是他自己的事,碍不着谁,我不管,但自己死不算,却要拉上两个垫背的,算什么东西;显然他内心深处已产生了他本人无法解决的道德危机,他长期受制于这种危机,逐渐丧失理性,而诗人又是天生的感性强于理性的人,于是就运用诗歌幻想力制造了这么一出悲剧,可恨而且可耻。诗人霍新朋反驳说什么感性强于理性,你根本不了解诗人,你以为诗歌来自幻想就不是现实的吗,诗人确实爱幻想,但他们是靠幻想来表现现实,因为只有这种表现才能使现实更合理更美好,所以诗人其实是最理性的,顾都正是因这种理性才以这种方式解决现实的矛盾。作家武东方说,以前只知政治家最擅长红口白牙说瞎话,今天算开了眼,原来诗人的这种能力丝毫不比政治家差,看来我今后应该对政治家多几分好感。
双方唇枪舌剑,争论十分激烈。评论家大多打圆场,劝两派别动肝火,活人为死人干仗,值得吗。大概都吃饱了撑着没事干,所以两派之争平息不下来,只有湘楚出版社的社长扬沙志和副主编黄国华对这种争论毫无兴趣,他俩考虑的事情显然实在得多,对他俩来说,顾都的事情不算悲剧,而是喜剧,又可以让他们捞一把,悄声议论说这家伙的书一定火,得抓紧时间把他所有的作品整理编辑,慢一点就会让人抢先手。黄国华问是不是去找找他家人。扬沙志说不能去,他母亲是个保守的老太太,跟她商量这事,不骂你一顿算客气。那以后她找麻烦怎么办。跟她软磨硬泡,她刚死了儿子,还怕磨不过她。黄国华问谭谈听说顾都一直在写一部名叫《英妹》的小说,有这事吗,写好没有。谭谈说他跟我说过,有这事,也写好了,听说被武汉一家什么出版社拿走了,好像是长江出版社。扬沙志便对黄国华说你赶快去一趟长江出版社,趁他们还不知道顾都出事把书要来,就说顾都委托你去的,想再修改一下,动作要快,今晚就走。王业宾在一旁听到两人对话,讥讽说你们这些出版家就喜欢挣死名人的钱,恶心。关汝屁事,黄国华骂道。当然不关我事,我只是看不惯文人的堕落。你错了,大诗人,我们不是文人,是商人,唯利是图。王业宾说那也应缓一缓,等人家入土为安了再揩油不迟,现在人家尸骨未寒就抢肉吃,说好听点太馋,说不好听点简直没人性。黄国华没好气地说入土为安了揩个屁的油,要吃当然得趁热吃,像你这种不温不火的吃法,出版社都得倒闭,如果我们失了业,今后谁来供养你们这些整天张着嘴要吃要喝的诗人作家,这叫吃死人养活人,懂吗。看来我现在就得立个遗嘱,将来死了,即使让狗叼了,也绝不准你们吃。黄国华愤愤地说你以为自己很值钱是怎的,身上除了骨头,哪有肉,我看即使一条饿坏了的狗也未必会对你有兴趣。评论家康沙首问霍新朋,听说顾都老婆有婚外恋,那人是谁。王业宾被黄国华骂得心里十分恼恨,一时又不知如何回敬,便拿这记者出气,你们记者也是,怎么比出版社的人还无聊,就喜欢打听这种事,然后报道出来,似乎对人家很感兴趣,其实人家的诗从来也不读一行。要介绍他的诗,当然先得介绍其人,有什么错吗。介绍诗就介绍诗嘛,干嘛非得介绍人。为什么不能介绍人。黄国华一旁说风凉话,这还不懂,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有一个最好的例,就是那个大文豪……噢,别说出名字,当心有人跟你没完……,就是他,当年他跟他兄弟住在一起,曾打过弟媳的歪主意,弟媳告发了他,那以后就兄弟反目,一辈子再无往来,这种丑闻,几人知道,几人敢说,在中国,凡是有地位有成就的人犯男女错误,就是风流,就有人用他也是人嘛来把这事一笔勾销,你要揭露真相,他们就对你群起攻之,叫你遗臭万年,可如果凡人犯了男女错误,那就是下流,就是无耻,就是道德败坏,所以,你想介绍顾都的家庭情况,我看趁早灭了这个念头,不然立刻会有铺天盖地的谩骂和批评落在你头上,别看你现在人模狗样,在文坛还算号人物,但怎么挡得住人家的千军万马。王业宾对黄国华怒目圆瞪,恨不得吃了他。黄国华笑道,大诗人息怒,我不是说你,也不敢说你,还望海涵。洪冶刚觉得这股火药味不好闻,急忙驱散,说顾都的诗是近代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诗人金学知不太服气,太抬举他了吧,现代诗歌大师不少,顾都顶多其中之一,要说他超出众人之上,我看他还差点。说罢征求徐景升的意见,你说呢。
徐景升一开始很认真听大家的议论,后来就走了神,又沉浸到沉重而忧伤的遐想中去了。顾都怎么就死了呢,还捎带去了两个无辜的女人。他的妻子,最是一低头的温柔,恰似荷花绽放的寒秋;而英妹姝更如出水芙蓉,光彩照人,有让人无限怜爱的情愁。怎么就去了呢,他竟舍得走,竟如此暴畛天物。扪心自问,我如去天国,绝不会这样自私。心里就是一颤,噢,天啊,怎么这么不吉利,怎么一下想到自己身上来了,我跟他的死毫无关系啊。他不禁在如瀑布一般狂泄的阳光中哆嗦了一阵。思绪飘飘,仿佛在天地间飘浮,仿佛在寻找那3个人,经过两天的飞行,他们这会到达了什么位置呢,月宫,还是玉帝的天庭?他比较相信那两个女人能回归月宫,人世的纯情使她俩具有这种资格,更因为她俩也许本就来自那里。至于他,如果说他能在玉帝庭前高吟美妙的诗篇,他只能半信半疑,因为玉帝可能给她俩放的是下凡游乐的长假,现在他率性而为,擅自带回二女,定惹玉帝生气,多半要将他打下天庭,塞进龌龊的地狱。徐景升的思绪在宇宙间飘荡了一会,没有结果,很不甘心地回到了尘世间。噢,顾都,我的朋友,我的兄弟,你在哪,为何匆匆而去,为何把我孤独留在人世?有人说顾都自私,当时他很恨这样说的人,因为他跟顾都从本质上说是一类,这样说顾,就等于说他。现在他理解并承认了这种评价,顾都的确自私,他俩同病相怜,既然你要回归天国,怎能撇下我,我跟你一样需要回归啊!但能怪人家吗,似乎是不能的,因为好像他曾给过暗示,自己不够敏感,当时没在意。把上次在茅房喝酒消愁时顾都说的话认真回忆了几遍,那话里的玄道和奥妙,以及顾都说话时伤感的表情都越来越清晰地说明他的话是有深意的,是在预示这个悲惨的事件。既然同病相怜,自己应该更能理解、透视顾都的这种心态才对,却连这么一点点的预兆都忽视了,有什么道理怪人家。严格说来,他该深自谴责,不是为能够以顾都为榜样,而是为这件惨事不至于发生。虽然他已经很赞赏顾都的这种彻底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