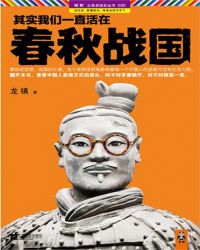无量春秋-第4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为什么都听不得真话呢?
难道水员外连这点雅量也没有?
“你……你好像哪里不太舒服?”许佳蓉又问。
“我很好。”水员外木然应道。
“那为什么一向诙谐幽默的你,突然间变得不爱说话了呢?难道只为了我刚才所说的话?”
“不,我不是那种开不起玩笑的人。”
“你知道吗?如果你再夸着个脸,我将拂袖而去,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真正原因,那就是我欣赏你的多话和诙谐,如果你失去了这些,我宁愿回家去对着我的北京狗说话。”
水员外苦笑了一声,他还真没想到这个冷绝的女人会坦率的那么可爱。
“为……为什么?”水员外有些不解的问。
沉思了一下,许佳蓉道:“这个血腥的江湖,已有了太多的杀机、痛苦、烦恼,我只希望找一个能让我欢乐和发自内心微笑的朋友,而你正是我想要找的朋友。”
甩了甩头,水员外难过的像天即将塌下,他说:“你说实话,我像什么?”
“你像什么?!你是水员外啊!还能像什么?”
“那么为什么街上的人,看我的眼光都像看到一堆牛粪一样?”水员外哭丧着脸道。
许佳蓉超前两步,她回过头仔细的看着水员外一会,然后再看看街上的行人。
她笑得弯下了腰,甚至连眼泪都已流出。
她不停的笑,不停的笑……。
水员外的脸现在真和一堆牛粪差不了多少,他只能看着她笑,看着她不停的笑……”
许久以后,许佳蓉才直起腰,一面擦着眼角,一面还是忍不住的笑的说:“你……你是不是认为……认为我和你在一起……就像一朵鲜花插在……插在牛粪里一样……”
“不,不是我认为,是他们认为。”水员外很艰难的抬手指着街上的行人说。
许佳蓉突然收起剑来,她正色的说:“你为什么要管别人怎么说?为什么会那么想?难道你的自信心、你的荣誉感已全消失殆尽?”
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新衣,水员外叹了一口气道:“我……我已不是水员外了……”
这的确是种悲哀,没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
她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她也感染了这一种无可奈何的忧戚。
没有酒,没有莱。
水员外请许佳蓉吃的竟然是冷硬得可把人牙齿给啃掉的“火烧饼”。
看着许佳蓉望着手中的硬饼,一口也没动过,水员外尴尬窘迫的说:“对不起,本来我是想好好请你吃一顿的,但是……但是你知道我不得不赶快离开……”
“难道你要一辈子躲着他们?你这样逃又能逃到什么时候?你要知道你躲得了一时,又岂能躲得了永久?”许佳蓉轻叹着说。
“我……我知道这也不是办法,可是刚刚迎面而来的是我们丐帮的‘残缺’,我本来已成了他们眼中的叛徒,再加上我又杀了‘怒豹’楚向云,你又要我怎么向他们解释呢?水员外心有余悸的说。
“你可以向他们揭发郝少峰的阴谋呀!”
“我要如何揭发?有谁会相信我?”
这还是句真话,许佳蓉只得默然。
想起了一件事,许佳蓉突然道:“喂!大员外,七月初七望江楼你和‘快手小呆’决斗,听人说你没到场,能不能说来听听?”
水员外最怕人家问这个问题,但是对这位救命恩人,他已没有什么好隐瞒,于是他说:
“不,那天我在场,可是因为某种原因,我不能亲手杀了‘快手小呆’,这是我这一生中最懊恼的事……”
面露孤疑,许佳蓉问:“你吹牛,你怎是‘快手小呆’的对手?”
提起小呆,水员外就想到自己屁股上的“胎记’,就想到欧阳无双。
他愤恨的道:“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可是我那使针的绝招是他从来不知道的,我敢说他一定躲不过我的绣花针,你又没有和他打过,又怎知我不是他的对手?!”
许佳蓉露出古怪的笑容,她说:“我虽然没和他真正的打过,可是我们却差点打起来,他的确是个高手,一个真正的高手……”她回意着“川陕道”上和小呆的对峙,她又说:
“他也是个鬼灵精,那天我被他骗了,要不然那个时候杀了他的话也就没有‘望江楼’他和你的约战了……”
水员外本来是和她同坐在一方大青石上的。
现在他已站了起来,微胖的圆脸已因惊异快成了马脸,他难以相信的问:“你……你什么时候碰上了小呆?在什么地方又差点和他打了起来?!”
许佳蓉吓了一跳,她说:“有什么不对吗?他是你的敌人,你干麻那么紧张?”
是的,水员外简直恨透了“快手小呆”,虽然他已死了,但是他们总是一块长大、也曾经好得可共穿一条裤子。
人既死,一切都已过去,再提他又有何用?
水员外缓缓坐了下来。
他没再问,可是许佳蓉却思索了一会道:“我记得那天是六月十七日,我在‘川狭道’上足足等了他一天……”
六月十七?川陕道上?
水员外回意着六月十七到底是个什么日子。
他又在想川陕道正是小呆到平阳县必经之路。
她等他?还足足等了他一天?
她等他做什么?她又怎和小呆在六月十七那天会从“川陕道”经过?
水员外这次不是站了起来,而是跳了起来,就像他的屁被蛇咬了一口。
他虽然没有被蛇咬,可是他现在却像发现到了一条最可怕、最毒的蛇一样,他紧紧瞪视着对方。
他牙齿打颤,语不成声的问:“今……今年?!”
“什么经验?”许佳蓉简直被他弄得哭笑不得。
也难怪她听不懂水员外的话,一个人在牙齿打颤的时候又怎么说得清楚话?
“我是说……我是说你在‘川陕道’等……等‘快手小呆’是……是不是今……今年的事情?”
许佳蓉也站了起来,并且点头。
“你……你肯定?”
“我又没像你一样得了失心疯,我当然记得是今年的事,现在是十月,四个月前的事我怎会忘记?”
“怎么会?又怎么可能……”水员外退后了两步。
许佳蓉已经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她只愕愕的看着他。
水员外记得很清楚,六月十七那天他也整整等了小呆一天,从天刚亮的时候起,一直到子夜。
他更很清楚的记得,他还打了小呆的肚子一拳。
小呆从洛阳赶来,这是个秘密。
秘密别人怎会知道?
她既拦截过小呆,为什么小呆见了自己却从没提过?
他没提是不是怀疑自己?
水员外冷汗直冒,虽然小呆已死,可是这总是一件令人不得不弄明白的事。
“你怎么会知道‘快手小呆’那天会从‘川陕道’经过?你又为什么要拦截他?”水员外像审犯人似的问。
许佳蓉,有些不悦冷冷道:“这很重要吗?”
也发现了自己的语气不太得体,水员外展露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他说:“对不起,我一时心急了些,抱歉,抱歉……”
面色稍缓,许佳蓉笑道:“嗯,这还差不多……我是奉了外公之命才去拦截‘快手小呆’。”
“‘左手剑客’白连山?你外公又为什么要你这么做呢?”
“这是因我外公曾经得过一种怪病,一种心智逐渐丧失令天下群医束手的怪病,我们只有见着他老人家一天消瘦一天,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直到他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走方郎中,他说他能治这种病,这对我们来说当然喜出望外……”
“然后呢?……”水员外急迫问。
“然后?!”许佳蓉露出苦笑。“然后病虽冶好了,可是我们却永远都要受到他的摆布……”
“为什么?!”
“因为外公必须三个月服用一次他的独门解药,否则全身痉挛不止。”
水员外叹息道:“我明白了,那么拦截‘快手小呆’必是此人的授意对不?”
痛苦的点了点头,许佳蓉说:“三个月一到,总有人受他所托带上解药,那一次却附上了一张纸条……”
“怎么说?”
“六月十五至十七日,川陕道杀小呆,务必全力以赴。”许佳蓉道。
“那神秘的走方郎中是谁?难道你们就没查出来?”
“谁知道他是谁?谁知道他在哪里?谁又知道他竟会卑劣的留了那么一手?”
水员外默然了,他不得不佩服这人的厉害。
这是一个圈套,就像自己一样,还不是陷人了一个解也争不开的圈套里。
脑际灵光一闪,水员外蓦然想到一件可怕的事。
“‘菊门’!一定是‘菊门’。”他吼了出来。
“何以见得?”许佳蓉不解的问。
水员外扼要的述说了一下自己和小呆的关系后。他苦着脸道:“当初我飞鸽传书找快手小呆来平阳县,是用我丐帮的‘千里鸽’,这件事只有丐帮的人才知道,郝少峰既是‘菊门’中人,我想消息一定是他泄露出去,这整件事情……”
水员外打心底泛起一股寒意,他没想到“菊门”真的可怕到这种地步。
“只是……只是‘菊门’为什么要杀‘快手小呆’呢?”许佳蓉不解的问。
她不知道,水员外何尝又知道呢?
现在他对“快手小呆”的恨意,仿佛已消灭了许多。
因为他已想到似乎有人要故意的挑起自己和他的猜忌,甚至他已想到“快手小呆”约战自己也是别人安排的一种阴谋。
——小呆、小呆你真的死了吗?
——小呆你为什么不讲呢?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会遭人拦截呢?
水员外心理懊恼的喊着。
他真希望他现在能好好的和小呆谈谈。
毕竟他发现到朋友之间,如果不能坦诚相见,这就是许多误会的起因。
他哪又知道他当初隐瞒了发现绣花针之事,不也正是造成了误会的原因吗?
不吃狗肉的人,就算你打死他,他还是不敢吃。
吃过狗肉的人,这到机会总要来上那么一碗。
而吃过水员外新手料理、烹调的“狗肉大餐’”,恐怕他一辈子都要回味无穷,连作梦也会垂涎三尺。
水员外在最不高兴、最烦恼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想到弄只狗来消消气、化化痰。
他这说不上来大毛病的毛病,还真是个毛病。
就像有的人一生气,就想大吃一顿、就想杀人放火、就想上吊。跳河、骂人、甚至跑到坟堆里睡觉,抱个女人猛搞,是同样的道理。
这世界本来就千奇百怪,也难怪有千奇百怪的人做出千奇百怪的事情。
也活该这双黑狗倒楣,它偏偏在水员外最烦心、最不高兴的时候被他碰上。
平常,或许有女为伴,水员外不太敢显露本性。
但是他今天实在无法克制住那脑袋快爆炸的痛苦。
于是——
那只倒楣的黑狗,连一声修叫也没有,它已倒地。
传说狗能嗅得到死亡的气息,每在黑夜只要狗嚎,这附近不出两天准有人会死。
为什么它也不能嗅得到自己将死?
这是许佳蓉身上香气,已完全遮掩了水员外身上的杀狗之气?
狗若有知,必将追悔莫及。因为只有隐藏在浓郁香气中的杀气,才是最令人防不胜防及最可怕的杀气。
火已旺,灶已热。
灶上的大锅里更是香气四溢,弄得这间农舍的主人、以及两个小萝卜头不时在厨房门口探头探脑,只巴望着早点尝到这一辈子也没吃过的好东西。
拔弄着灶里的柴火,水员外茫然的不知想些什么。
许佳蓉却坐在一旁,她已好几次想说些什么,可是就不知该如何打开这僵局。
这个白衣素服、貌美如霜的女人,恐怕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坐在这里。
人总会常常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来,不是吗?
水员外用手轻拍了两下自己的后脑勺,像记起了什么,又像要想忘掉什么。
他有些歉意的望着许佳蓉说:“你说什么?”
许佳蓉乍听此言,杏目圆睁,一付不明所以的问:“我什么也没说。”
“是吗?”水员外眼里突现一丝笑意。
“什么是不是?我根本没有说话。”许佳蓉也看出了水员外眼里的坏意,她心跳了一下说。
水员外笑了,原本僵凝的空气一扫而空。
“我好像听到你的肚子咕咕在响,也好像听到它在说搞什么鬼嘛!怎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