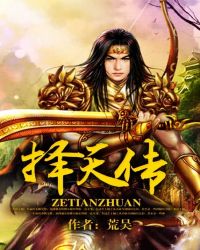���䴫-��5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ں�����˵������������š�ԶԶ���š�
��������һ�Ѷ����ɫ�����ƣ��͵͵�ѹ�Ŵ�ء�����������֣�����ɯɯ��Ħ��������������Ŀݻ���Ҷ�������������ǵ������赸�������������赸��
���������������ֽ���һƬ��Ҷ�������ǿݻ�ҶƬ�ϵ����硣��Ȼ�е���һ�����еŶ��ͱ����С�
�����������ǵ���ʱ����ˮ��ʱ�⣬�ǵ��������������ӡ��ǵ��������飬���鷿��ϸϸ��ζ���ζ�������ӣ�Ҳ�ǵ������������������ֱ�����ӡ��ƺ�Ҳ������ɫһ�㣬�Ƿ����������ҝ������죬�����ķ磬��Ǩ�������Ҷ����¶��������į��������
�����������A�����߹����������������Ů�ˣ���Զ�����ǣ��������Ų��£���ķŲ��¡��ƺ�������˯���ж����������Ӱ�ӣ���˼��࣬����˭֪��
�����������������һ���ر��Ů���������̲�סҪ��������ǻ���������ȴ**�ò���Ҫ�κΰ�����ԭ���������Ի������������飬ȴ���������������ͬİ·����������̵�ʹ������ͬ���½���Ҷ����������һ�㣬����ʹ˭�ֶ��ã�
������������������۾����η�������½ǣ����г�����̾Ϣ��
��������������������������������ĵ������������ۿ�ȥ��������ֵ���վ������IJ����ſڣ���������Цӯӯ�����Լ���
�������������֣��������ˣ��������������Ҳ���˹����������������һ�²����һ��Ů���ң��⺮��Ķ�������εù�����������������ţ����ݵ����ϣ����ǹ��С�
�����������ǰ������ⲻҲ��������λ�ٹ�����Ȱ�أ������ǿ�úܣ��Һ�������Ȱ�˶��գ�ȴ����Ҳ�����������ڼ���Ҳ�Ǽ���ʲô�Ƶģ�����˭����˵�ö����������ֿ��˿������������ү��С��Ҳ�������ѣ�����һ��Ҳ����ȰȰ��Ҳ��������ġ���
�����������ã�ֻ��������Ϻ���˵һ�仰�ɣ��������Ц�ţ��Ӽ�������ӹ�һ��������˵����������������õİ�ƤëΪ�������һ�����£�һ������ϣ�����ܽ����ҵĺ��⡣�캮�ˣ���Ҳ������Υ��Т������
�����������Ŀ�Ц��������Ը��ˡ���
����������˵�ţ�����㦵˺�͵��Ѵ�ͷɥ�������˹����������������˵������û�õģ�����������Ƥ�ӿ�ĥ���ˣ���Ȱ�˼����ˣ����Dz��ϻظ�����
�����������ǰ����Ҷ�˵�����������ˣ���˭֪��ȴ˵Т�IJ����档���������õ�Բ���۾���
�����������ĵ���������Ҳ���������ү˵�ţ�����ҲȰȰ����λ�ٹ��ӻ�ȥ�ɣ���ȥ���ˣ����˻����ġ���
����������������Զ����������������IJ���ǰ������ǰһ���IJ����ӣ���紵��������ʱʱ�ƶ�������������ۣ�˵��������������������ˡ�����һ��ɺã���
���������������������������������һ����̾����������˵���������ˣ���ô�����ˣ���
�������������˾������ˣ��㻹�������������������ҿɺã�������������������������һů���ճյ�˵��
�����������Ҳ�������˵�Ļ�������˵���ˣ�������˵�ڶ��顣���������ָ���䣬������䡣
��������������紵�룬һ����ɫ���������������ϣ�����Ҳ��һ��ůů�����屧ס��
�����������ſ��ң������������������˦�����죬ȴ�������ø��������Ҳ��ţ�ʲôʱ�����Ӧ�ҵ�Ҫ���ˣ����ٷ��㣡��
���������������������ڸ�����ǰ���һ����һ���ӣ����������ŭ�£�ȴ���������Ļ�����
�����������㲻��Ӧ�ң��Ҿͱ���һ���ӣ��һ���ߵ˴��ˣ��һ��������һ���ӣ���������Ͳ������ˡ�����������������ͻ��ͣ����������������λ��ҧ�Ŵ����ƺ�Ҫ������
����������ɵ�ϣ������������ң��ͻ�ůһ�����𣿡�������ͻȻ��ú����ᣬ����������Ķ����ˣ���̾Ϣ�ţ���ͷ��������ļ䣬������������ۣ��ؼ�ȥ��Т�����ⲻ����һ��Ů���Ӹ�ס�ĵط�����Ӧ�ң��ص�����ȥ����������ٽ����أ����촺�����������𣿵�ʱ���������㣬���𣿡�
�����������⻰���Ƕ�����ˣ��ҵ����⣬��ñȱ��˸��������֪���Ҳ����ߵġ��������������ģ����������ľ�����Э��
��������������ʹ�Ӧ�ң����Ұ����С��������һ�£�������Թ���ȥ������죬�����Ҵ����ĺ��£�������Ϊ���ȼ¯����Щ�������ⲻΥ��Т֮�����������ֱ�����������������ӡ�
�����������ðɣ��Ҵ�Ӧ�㣬�����ڿ��Էſ��˰ɣ������������˵�ţ������ߵ��������ǰ�İ�ë�
�����������ſ����ԣ���ת��ͷ�����ҿ����㣡��
��������������������쵰�����������ҧ��������������������ô�ˣ���ˣ����������
����������������������ˡ�������ͻȻ�ŵ��������������������յ����������С�֡�
�������������죬��������Т������ô�����������ң������ٲ��ſ����ұ���������ǰ�����������D����ȴ�������ģ������ܶ�ҡ��
�����������úã�������Ҵ��ˣ��ҷ��֣��������ɿ���˫�֣����κεĿ������ı�Ӱ����֪������Ǻá�
�������������ȥ�ɣ��㲻��Ҫ���������𣿡����������ͷ��ȴָ����������ʲô��
���������������ε����˳�����������һ��ƤЦ�ⲻЦ�Ŀ����Լ����������ż��ԶԶ��վ�ţ�Ҳ֪�Լ�����һ��嶯����Щ���ݣ������ε�Ц��Ц������Զ�������ĵ��������֣�����Ѵ�Ӧ�������ֻ�ǻ��Dz��ϻظ�����
�����������ĵ�������л����������Ѿ�����õĽ���ˡ���ү���ҵIJ���һ���ɣ���Щ��ˮ�����䲻�ã�ֻ������ĥʱ�⣬���Ǽ������������ɣ���
�����������ã�������Ը��깤���ɻȴ�Բ������������ֻ�ó�̾��һ�������������˲��
��������һ���ʱ�䣬������������һ��ľ�壬��϶�䶼�����Ĩס������ľ����������һ���ţ�������Ӧ���Ǻõö��ˡ�
����������Ҫ��ʱ����������ƤЦ�ⲻЦ�����˹�������������һ���������������˵�����������ү�����������ǿ�����Ȱ��С��ķ��ϣ��������治֪��ô���㡣����С��д����ģ���úÿ����ɣ���˵�Ž���������������С�
������������ӹ��˱���������ּ�δ�ɣ�Ц�ſ��˿���������������С�㣬������дʲô��ֻҪ�����빬�������һ�첻�����ģ���ֻ�ǵ�������������Ȼ��һЦ����ʹֻΪ��ӵ����һ�̵�Ц�ݣ�ֻΪ����������������������������������Ȼ����������������IJ��ﺰ������������˵������������Ȼһ�������ֺξ壬ֻԸִ��֮�֣��������ϡ���
������������������Ļ������еı��䵽�˵��ϣ���ˮ�ٴ�ģ����˫�ۣ�ֻ����������ĸ��������ڿ�Զ��Ϧ���£��þò�ɢ��
�����������ҹ��ñ�������Ψ�Բ����ˣ���
��������������
����ʮ���¡���̣�����
������һ��ɨƽ��������ϼ��ŵ�����֮��ʼ�������¡���ÿ�������ٳ�����ҹ�������£���ÿ����һ�εĴ��𣬸ij�ÿ�մ��𣬴Ӳ��ĵ����£�����������Ϊ��
����������������ƶԴ���������Ҫ�ԣ���������³������µף����������������һ�����������е�����һһ��̨�����������dz���һ��ʮ�������������֮�֡�
���������������������������塣
�����������ڰ����������һ���й������졢�����Բ���˵���ʹ����Ǵ�����ͭǮ��˿������������Ϊ�Լ�����༪�٣�ȴ��������ø���ֻ�ж��÷��㵻�棬��������ƽ����
�������������ַ�ܵ����ٵ��ñ������������˺Ӽ��������統�˳������������굱�˹����������ҽ��ַ��������������������ʰ�ݡ�һ��һ�����ֵܺ����������������ط������Ĺ�����
��������Ψһ�����������ѹ��ľ���˾���������Լ�ѡ��ǰϦȥ�š����ش����һ���������ͺ��ᣬ���ڹ���գ����˾ũ����Ϊ̫ξ��¼�����¡�
��������ʮ�¼���������������Ϊ˾�ա�����⳹��������ϵ���ͳͳ�չ���ְ��
������������Ҳ��������������һ���������ڼ����¶���Ϣ���ã�������û��ʱ��ϴ�衣�������������ֺݺݽ���һͰ��ѩˮ���Դˣ����һ���ѳɾ�����
�����������ã��о��£�̫ξ���ɱ�ָ��Ϊ��ϵ��������²���������ɣ��������±������ɱ��
�����������ɽ����磬����������й�ϵ������ְ����ر����ᡣ
���������Ѿ�����Ԫ����ȥ���Ĺ��������ķ�ر��������Ķ��ӹ���̳У��������ں�����й�ϵ�������������
����������ʱ���Ѿ��������Ƶ�̫���˱롣�����϶ಡΪ�������ȥ���������Ҫ��ְ��������گͬ�⡣��Ȼ�����ܹ�Ա�����˺ܶࡣ������ȴ������ȱ������֮�ˣ����ڹ�Ա�ľټ�����һ���е�����֮���ܵ������á�����������������֮��
��������������Щ���У�ֻ��һ���˵Ĵ�����������ԥ�������Ǿ��ǰ�̡�
����������ܵ�����ʱ���Ͷ������ܡ���Ϊ������ı���ͱʳ�����ܰ���֮���ڰ�̵IJŻ��������ж���֮�С�
�������������Ȼ�����á����Ƕ������Ķ��ӣ������Ȼ����������ǡ���˰�̵ĺ������������ǰ��֮�Ӷ�����������Ϊ��������Ѱ�����£����˺ܶ�Υ��֮�¡�
���������ܶ��˶�����ξ����������档��������ȴ�ð�̵���Щ����û�а취���Ͼ���̵ĺ���������
�����������Ժܶ���ն������̡���Ա��Ҳ������Ļ�������
����������̲����Խ����Լ��Ķ��Ӻ��ް취��Ҳ��Լ���Լ������ˡ���һ�Σ��������־������Լ���С�����У������·�Ͼ������˰�̵ļ�ū����λ��ū�ȵ��������ģ������ľ��������ڽ���ˣ���˾Ʒ裬˵ʲô�������־��ij�ͨ����
���������־�����һ��ū�Ÿҵ����������·��ʮ�����������������¹����������뿪��˭֪���˲��������ƿڴ����������־��������������������˴���һ�١�
����������ʱ�Ǽ�ū�Ż������ž�����������ǰ�̸��ϵģ�������ô�Ҵ��ң���Ҫ���߰���ˣ������dzԵ��ͷ��
���������־�һ�������Ƶ�ū���ǰ�̸��ϵģ���������һ������ƽʱ���̵Ķ���Ϊ�����������ӵ��˶�εĸ棬ȴ��Ϊ��ܵ�ԭ��ֻ���������������һ��СС��ū����������β������������Ҳ��һ�����ٻ����������Ƶļһ���Dz���������
���������־�������ʰ��һ��֮ʱ��ͻȻ�����̵ĺ�̨����ܣ���ֻ�����̲������Ǹ�ū�������£���������£��־�ȴ�����������Ѱ��������̡�
��������������Ԫ���꣬��ܱ����ҵı���Ҳ�����������ʡ��־��о�������Ļ������ˣ��������Ѱ�̹��������������ʡ�
�������������һ���ң�Ҳ��ʷѧ�ң����ı�����д��������ԩ�����У�����������û������Լ�Ҳ��������һ�졣�����־������ֿ���֮�£��������и����ܲ�����������Ĺ��£�����������У�ʱ����ʮһ�ꡣ
��������һ����ʦ��һλƷ�кܶ����Ĵ��壬��Ȼ��Ϊ�Լ��Ķ��Ӻ�ū��Ϊ�����������˼��ޣ�����������С������������ꡣ
������������������ԥ���������ð��ʱ��ȴ�õ��˰���������е���Ϣ�����ɴ��һ����
���������������־��ͺ��⣬����ѯ��ԭ��
��������������ڰ�̵���Ҳʮ�ֳԾ�������û�����˴�����̣����Ա��Ŀ��Ͷ�����־���
���������־��������˵�ǣ����������������£������֪������죬�������������գ���
���������������������ɣ������ر������ڵ����������ţ���������������ȴ���ֶ�����ʯ֮����ǧ���ش����û����־����ġ�
���������������һ�����壬���ʹ����������ʩ���̣����߿������ɽ�Ҳ���ɽ���������Ҳ����ɱ��������Ҳ����������̣���ɱ������Ҫ�ѹ���׳ʿ���軹Ҫ��һ�����㣬������ڣ�������̫���ˡ���
������������Ŀ��һ������Ц�������ִ��ˣ�����˵��Ͱ������Щ���ڵģ�����Ю˽�����ɣ���
���������־������ϳ��ֵĺ��飬��������ץ�����֮����������Ǩ֮�У����Ժ������������Ǵ���һ˿������������������������У��ҿ����������һ���Ĺ�ϵ����Ҳ��ְ��֮�ڣ�����֮�У������ˡ��������������ݡ���
�������������Ҫ˵�������ش������˵��������û��ɱ���֮�⡣�����������ɱ����
����������ͣ�����־�����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