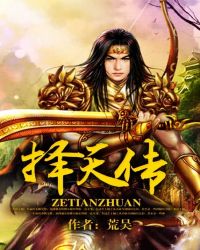和熹传-第4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赵玉惊讶地看着她,小声道:“……”
邓绥看也不看她,仍淡淡道:“去吧!”
赵玉无奈,只得转身回房而去。
邓绥抬起头,看着清河王轻柔心痛的目光,竟也是痴了,四目相对,泪眼盈盈。
一阵凉风吹过,绥儿不由打了一个冷战,清河王忍不住将她拥入怀中,觉得柔若无骨,叹道:“绥儿,你怎么瘦弱如此?”
绥儿略挣了挣,也便随他,轻声道:“病了几日,不想竟然瘦了些。”
“绥儿,我,我一直在想你,那日李夏去京中办事,遇到了我,我便问起你的情况,才知道你病了,实在是担心,便来探望。绥儿,你怪我吗?我,我有我的无奈!”
邓绥自他怀中抬起头,望进他的眸中,深深的凝视着,许久才道:“那日分别时,父亲和兄长是否提起绥儿将来会入宫之事?”
“是,我那日向邓大人提亲,却不料,他说将来绥儿必入宫为妃,让我死心。我知我一个被赶下台来的,已无资格与绥儿相爱的。可是,可是我,我却一日也忘记不了绥儿的一颦一笑,每日梦回,总见你立于我床前的身影。绥儿,我实不知怎么办了!”
“你也瘦了好多!”绥儿主动伸出手与他相握,他的手有一点点温暖,可以感到那掌心凛冽的纹。刘庆紧紧拉住她柔弱的纤手,只觉恍然和蒙昧,想念如潮水般袭来,扯动了心肺,泪水潸潸而落。
绥儿浅浅一笑,将心中的伤心哀痛强自忍住。“王爷,母亲告诉我,出了正月,宫中便要选秀了,我自是在选秀之列,你我的缘分,想来,想来,到此罢了!”
“绥儿!”刘庆的全身力气都被一丝丝抽空了,他将绥儿紧紧的抱在胸前,心痛得难以呼吸。
“王爷,忘了绥儿吧,我自小便担着入宫的重责,永不能变,绥儿虽无奈,却不能让家族为难。自小受的孝道,绥儿自是永记于心。我们都不是随着自己的心走的人啊!”她用力推开刘庆,心却随着这剥离碎裂成了无数片,泪水再次倾泻而出,止也止不住。
“绥儿!”刘庆的胸口似被人硬生硬抓了一把,疼得难受,“绥儿,我让你流泪了,我无权无能,除了一颗心是你的,还能为你做什么,如今还让绥儿为我伤心,我这样的人,不嫁也罢。”他仰起头,强自忍住泪水。
绥儿含泪苦笑道:“错也罢,对也罢,无心也好,有意也罢,一切都是命数,王爷,我知你已重回宫廷,皇帝待你厚重,今后要小心为人,小心做事,安安心心做你的清河王爷,也是上天的眷待了。”
刘庆轻笑:“是啊,上天的眷待,不薄了,绥儿!”他轻轻捧起绥儿的小脸,轻叹道:“你好好养病,刘庆虽是无能,却决不负你,一生一世,只要绥儿一句话,死不足惜。”
“嗯!”绥儿点头,含泪一笑,如梨花带雨,美艳无比,刘庆竟又看得痴了,便欲向那樱唇吻下!
一声轻咳,赵玉已站到了二人身侧,邓绥觉得脸上一烫,红滟滟的一直酡红到了耳根,忙与刘庆分开,低声道:“那绣拿来了吗?”
赵玉也红了脸,不过还是没有好气的说道:“取来了,,你别忘了夫人和夫的话。”
“嗯!”绥儿点头,将那梅花争春放入了刘庆手中,“王爷,这是绥儿第一件绣,如今送给王爷。”
刘庆接过,贴于脸上,望着绥儿,万千不舍,说道:“绥儿,我只恨我自己,也恨这清河王的身份。”他声音悲凉快如弦月,目光竟比满地黄花还要萧瑟。就如冰封的湖面裂开了无数条细碎地冰纹,再难复合。
绥儿眼神微微一晃,故意将心冷了下来,说道:“王爷,秋寒了,多穿些衣衫,绥儿回房去了。”
刘庆悲反笑,“绥儿,你去吧,我已是破碎成千万片的人了,还管什么秋寒冬冷吗?”
绥儿心中难过,停下了脚步道:“你无恙绥儿才安心,你若不想我哭,你好好的,不要让我牵挂着。”
刘庆闭了眼睛,让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冷风贴着面颊刮过去,如泣如爽呜咽难听,更显得他的身影冷冷清清。
绥儿硬生生将泪咽下,望进他的眼睛,咬了下唇,生生地说了两个字“珍重!”便捂着脸,踉跄着回房去了。
风更冷,如一柄柄钢刀般,将世间的情斩落得一丝不剩,却还假仁假义的呜咽着,哭诉没有平凡的布衣夫妻,“厮守到老!”刘庆苦笑着,那是他许久以前的愿望,只要和绥儿一起,天涯何惧,如今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一个人!
悲戚的中,他走出了邓府的大门,却见一个娇小的身影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长衣相候,也许,他还会有一丝阳光在等待着他,守护着他!
。。。
。。。
第五十二章 试探()
更多第五十二章试探
窦后站在窗口,向外看去,见郑众正指挥着宫人们在嘉德殿里忙来忙去。虽说他是请示了自己的,却也不胜其烦,叫了王银儿道:“你叫郑众进来,我有话问他!”
片刻间,郑众自外而入,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礼道:“后,莫是有何指示,我这就让他们改过。”
窦后打量了一眼郑众,他两鬓略见苍白,脸上却无一丝皱纹,无须的脸上,光洁无比,不由想起章帝时常见他在跟前的情景,一时晃忽,许久才道:“哀家不是叫你改,我是觉得吵得人心烦,你也知道哀家寡居,喜欢独处。虽说是想帮哀家改改这院中的景致,只是冬天将至,也没什么可看,不如开春再说如何?”
郑众笑道:“后,这停下来是不要紧的,只是已然铺张开了,这乱七八糟的摆满了院,不是也碍后的眼吗?”
窦后指着窗外摆开的石料和工具道:“郑众,哀家一直觉得你是一个有条理之人,怎么如今做事没有个主见?”
“臣不明白,请后明示!”郑众施礼问道。
“只怕你真的是不懂的,大凡工程都是在春日施工,哪有赶秋了再做的?还有,这进料的东西,也得有个计划,不能不问多少,一应运进宫来,万一用不了,浪费不说,也将宫中搅扰得厉害!先帝在时,便主张节俭,我本不欲来修整院,我寡居于此,修得再好,也没了心思看。不过即是皇帝的孝心,我也不能拒绝!这样吧,银儿,宣明殿空着,你一会便让人去打扫出来,哀家过几天就搬过去,省得看着这些东西头疼!”窦后说完,挥了挥手,让郑众退下。
郑众暗暗一笑,慢慢退出。他自那日去见了李郃,两人便商量出了对铂先是让皇帝对后大献孝心,为后修整宫殿,窦后嘴上答应,心中必会不以为然。她本寡居,又有男宠,自然不希望自己宫中人多,便会迁居别殿。天六玺尸中至宝,搬运时便可进言,不可轻动,以免损伤国体。窦后本也以为,不会离开几天,便会依从,到时候从中取事即可。
果然第一步的计划顺利完成。郑众笑着指挥众人继续着工程,并开始留意宫人们的动静。
王银儿是窦后从宫中带出来的贴身侍女,自小便陪着后,性情却与窦后迥然不同。她性格恬淡,心地善良,宫里宫外有什么大事小情,做不好,怕责骂的,都找王银儿来说情。她只要能帮的,绝不会推辞。
她安排好了婢女们打扫宫室,却发现由于长久无人居住,殿角已有破损,后怎可来这四面透风的居所安睡呢?不由皱起了眉头,又来找郑众商量。
郑众早惦记着让后快些搬赚听说殿角破损,立即找工匠星夜赶工,几天时间,不仅将殿角补好,内室也粉刷一新。
王银儿前后检视一遍,觉得还算满意,便重新打扫干净,恭请后移宫。窦后命人将天六玺用锦盒盛好,用明黄锻包着,便要起驾,在宫外的郑众早看到了天六玺,便小跑着过来道:“后慢住”
窦后停下轻辇,看着他问道:“何事?”
郑众深施一礼,说道:“后,天六玺何以在后宫中,陛下不是已经亲政了吗?”
窦后脸色一沉,一双精光四射的眸突然闪出了一丝杀意,“这是你一个当宦官的当问的吗?”
郑众忙跪倒在地,想了想之前与李郃商量的话,开口说道:“后,臣自小随明帝,后又随先皇,对大汉朝是忠心耿耿,虽说身为宦官,不该插手朝政,可是臣也明白,这六玺之理。”
“六玺之理?”窦后熟视郑众,许久,才道:“你说的六玺之理,是什么道理?哀家自先帝大行之后,管天下之事,这六玺自然在哀家手中,你今天说不出个道理来,哀家便治你一个干预朝政,扰乱圣听之罪。”
郑众听她这样一说,心中也开始打起了鼓。窦后,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女流,她久居宫闱,跟随先帝,又主理朝政,杀罚决断,何曾有半点含糊,军国大事尚且能处之有方,何况处理自己一个小小的宦官!只是箭已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他把心一横,说道:“后不知,自秦始有六玺,又名传国玺,世世代代,六玺皆存于奉先殿中,是为天的象征。此六玺皆为白玉制,螭虎纽,用都紫泥封。一曰皇帝行玺,用于封国;二曰皇帝之玺,用于赐诸王候;曰皇帝信玺,用于发兵;四曰天行玺,用于召大臣;五曰天之玺,用于策封外邦君主;六曰天信玺,用于祭天地鬼神。”说着,他口气一转,就得沉重又有点嘶哑。
“先帝大行后,后主天之权,无可厚非,但是此六玺乃天下至阳至刚之物,后虽贵为国母,却仍为阴体,若久掌六玺,不仅有损国本,于陛下不利,也对身体不利。阴阳之道,贵在调和。后寡居,又与此至刚之物同处,实则对凤体不利。臣虽是一介宦官,却也知阴阳之数。恕臣直言,后这段时候,是不是总是头晕心烦,身常感不适,病体久医不愈?”
郑众哪里懂什么阴阳之数,这些都是李郃教他所说。李郃早已想通其中关键,后久病,必有此因。如今让郑众娓娓讲来,却更增了几分可信。
窦后被他精亮亮的目光所镇,又听得他一番言语,只是沉思着,半晌才道:“哀家知道阴阳之理,但是,哀家一国之母,还怕这六玺之害?”
郑众又道:“不然,后您想,陛下已举成了成人礼和亲政礼,正是天下一统之象,万象归一,而后拿六玺就如同一匹想要狂奔的骏马,被人故意拉着走不得。后想最后这人会是一个什么下场?”
旁边的王银儿笑道:“那还不是被马拖着赚活活拖死?”
郑众笑道:“银儿姑娘说的正是这个理儿。后,陛下青春鼎盛,聪明无匹,后若久不将玺交与陛下,必会影响陛下治国,这后果,后想必比臣明白!”
窦后突然眯起了眼睛,看着郑众微微一笑,显得妩媚动人,声音中却带着杀气。“郑众,这话是谁教你说的?”
郑众心中一凛,坦然道:“后,这话是臣刚才看到六玺时想到的,并无一人教我!”
“哦,无人教你,你就敢如此大胆?这六玺在我这里是为了皇帝保管,这天下是我母的,哀家是母亲,无可厚非,要你这大胆的奴才在这里乱嚼舌根。”
郑众冷笑道:“臣是不敢管后和皇上的家事,只是这玉玺可非是家事,想是众位大臣也不知道后一直保管六玺之事吧,若知道了,后怕是要落一个不好的名声!”
“你大胆!”窦后勃然大怒,指着郑众道:“知道了又如何,哀家还怕这个?你一个管皇室园林的官员,好生做自己的事吧,哀家今日不责怪于你,是念在你是朝的老臣,若再多言,小心你的脑袋!”
王银儿见势不好,忙冲着郑众使了一个眼色,小声道:“后,郑大人说的有些道理,我也瞧着后这些日咳疾不好,是不是也和这有些关系,要不然,这样,我们去宣明殿只是暂住几日,这六玺嘛,就放在这嘉德殿里不动,若是后离了这玉玺,病情好转了,那九成就是这个原因,皇帝也大了,交给他也无妨。若是去宣明殿依然不好,就是这郑众胡说八道,危言耸听,再责罚他也不迟。”
她语声细柔,将窦后的一腔怒火又压了下去,“好吧,就依你,起驾!”
王银儿的一番话,让郑众心中一暖,没想到,自己语气过重,惹得窦后生气,而小小王银儿的几句话,就让事情又回到了正轨。想想真是捏了一把汗,暗暗后怕,一个不谨慎,险些满盘皆输!
忙向王银儿施了一礼:“多谢银儿姑娘,若不拭娘,后怕是真要了老臣的命了!”
王银儿嘻嘻笑道:“郑大人,我就是和和稀泥,大主意还得后拿,你们快些完工,后久居别殿,总不是事!”
“是是是,姑娘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