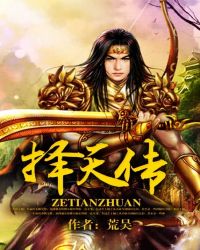高太尉新传-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门前老鸨本来还想趁讥再讽刺这个对头几句,听到曾老这两个字时便知道不对了。再看平时眼高于顶的几个官员点头哈腰地在那老人身边巴结,立时醒悟到来人便是曾布这位朝廷大佬。一瞬间,她的态度登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上前深深施礼不算,口中还打叠了一套套的奉承,满脸堆笑地把人引到了三楼。末了,见高俅最后一个跨进包厢,她还不忘自责补救道:“高大官人,我就是个嘴上没边的,您大人不记小人过别和我这妇人家一般见识”
“好了,谁有空和你计较这些!”眼尖的高俅突然看到对面晃过一个有几分熟悉的背影,连忙拉住那老鸨问道,“我问你,那个蓝衣公子是谁?”
“蓝衣公子?”老鸨满面疑惑地望去,谁知立刻啐了一口,“什么公子,那是我那些姑娘们倒贴的小白脸!靠着一张俊脸在这里招摇撞骗快一个月了,偏偏有人就喜欢这种调调!哼,要不是她们自己拿出来的体己钱,我才不会放任了她”
高俅见这老鸨一说便住不了嘴,顿时眉头紧皱连连摆手示意她住口,心里却着实疑惑。观那人背影,竟和自己见过的顾南有几分相似,可这种满城风声鹤唳的当口,顾南纵使真是辽国贵胄,也应该不会随意乱跑,更何况是这种人多嘴杂的青楼。再说那老鸨已经讲明了其人是小白脸,他也就懒得为此多费脑筋,一闪身进了包厢。
“伯章,这正主儿还没到,你和那老货多罗嗦干什么,没来由扫了兴头?”曾布显然兴致高昂,指着身边的空位示意高俅坐下,这才对其他人道,“你们大概也听过伯章的名字,他是曾经的苏门高足,如今遂宁郡王的师友,连太后和圣上也分外看重的。”
这些人大多是服绯官员,在朝中也算是有一席之地,换作往常,恐怕他们根本不屑理会高俅这种末品小官,但是此时有了曾布的介绍,他们却一个个端了笑脸,言不由衷地赞口不绝,好似高俅真是那等朝廷栋梁之材一般。
身处这种场合,高俅只得打叠起十万分精神应对,毕竟是七月大热天,他不一会儿便热出了一身燥汗。好在包厢四周角落中都摆放着冰盆,那老鸨又叫了几个绮年玉貌的侍女来打扇,后窗还不时传来一点凉风,这才勉强解了暑意。正在高俅满心不耐烦的当口,外间突然传来了一阵有如高山流水般的琴声。
那琴声既不似澄心琵琶的声声入骨,也不如云兰歌声的甜美醉人,更没有什么余音绕梁的神韵,听在耳中反而很有几分清冷彻骨的感觉。高俅恍惚中好不容易才分出几分精神,但见包厢中众人眼睛微闭击节不止,无不如痴如醉,不由暗叹京中处处有高人。
第二十二章 金蝉脱壳
一曲终了,入云阁内顿时传来了阵阵掌声,不乏有豪门公子在那里鼓噪叫好的。曾布虽不是初来,但如此琴艺还是第一次听见,略一思忖便唤来了老鸨。
“我且问你,适才抚琴的人是谁?”
那老鸨耳听大人物问话,神态顿时极为谦恭,陪着笑脸答话道:“回禀大人,那是含章,如今汴京之内仅次于澄心云兰的花魁行首。”说到这里,她情不自禁地瞥了高俅一眼,见其并未露出不快的神色,这才暗自松了一口气,又添油加醋地卖弄道,“这含章三个月前才到了我这入云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只是很少陪客,大人是不是包涵一下”
这番欲拒还迎的言语把高俅也说得心中一动,就不用说曾布等官员了。只见须发斑白的曾布狠狠灌下了一杯酒,似笑非笑地瞥了那老鸨一眼:“你这里的规矩无非就是解什么难题,罢了,我这里虽然都不是年轻人,但他们无不是过五关斩六将的科场才子,你把题目拿上来,我们也看看解得解不得!”
高俅见那老鸨飞一般地奔了下去,心中不由暗自称赞←在天香楼做的事情是让云兰摆足架子,除了每月一次献艺之外,任是谁的面子也得拿出真金白银或是文章诗词,十足十的待价而沽。而这含章却是在撩起人的心绪过后给你无限机会,至于能否一亲芳泽就难说了。正思量间,那老鸨气喘吁吁地捧着一纸信笺匆匆进门,口里还嚷嚷着:“含章听说是各位大人莅临,特地改了一个应景儿的题目,她待会弹奏一曲,若各位能听出其中的真实意境,她便立刻上来陪客,如何?”
曾布等人自然是连连叫好,高俅却在冷笑连连。要知道这大宋的士大夫最讲究风雅,这琴棋书画之道即便不能精通,但一首曲子的意境又岂能不知,看来那含章分明是有心给机会罢了。就在琴声响起的一刹那,阁内某处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然后所有人便听到了底下琴弦断裂的脆响,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此时谁也不知道。
高俅早在听到惨叫时便一个箭步冲了出去,就在二楼转角处,他看见一个粉衣女郎斜倚在栏杆旁,面色惨白地捂着嘴,两眼死死地盯着面前的那个包厢。见此情景,他立刻想起那是刚才那个蓝衣青年进入的房间,顿时脑际大震,来不及细想便奔了上去。在他身后,曾布等人也纷纷钻出了包厢,一时间,楼上楼下的无数目光都汇集到了二楼。
掀开那重帘子,一幅血腥的场景便呈现在了高俅面前。只见一个蓝衣青年脸朝上地躺在地板上,右手紧握成拳,左手则紧紧握着一柄匕首,而那匕首深深刺在胸前,染红了大片衣襟,地上墙上满是四溅出来的鲜血。
“怎么回事?”那老鸨踉踉跄跄地闯了进来,只看了一眼便容色大变,“这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天杀的小白脸怎么会死在这里,这不是有心害我么?”捶胸顿足地嚷嚷了几句,她突然想起曾布等人正在此地,顿时犹如抓到救命稻草般地转身冲了出去,看那风驰电掣般的速度,似乎身上的百多斤肥肉根本没重量似的。
“大人,大人,您可得给民妇做主啊!”不过顷刻功夫,那老鸨已是把曾布等人引了下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道,“这小白脸是这里常来常往的客人,有钱的时候一掷千金,没钱的时候这里的姑娘也经常倒贴钱养着他早知如此,我把他赶出去就好了”极度的惊慌和恐惧下,她已经完全语无伦次,只想把入云阁撇清出去。
曾布此时哪有功夫搭理这老鸨,喝令一声便示意随从把她拖了下去。面色凝重地查看了现场之后,他很快发觉高俅神色有异,连忙把人拉到一边问道:“伯章,怎么,你认识此人么?”
早在冲进门的一瞬间,高俅已是看清了其人面貌。和自己想象的一样,那正是顾南略带嚣张而又有些病态的脸,可是,无论如何他都难以相信真正的顾南已经死了。要知道,高明可是拍着胸脯对自己打了保票,那玉佩惟有辽国贵族方才有资格佩戴,而且由于其价值不菲,寻常密谍根本不可能轻易获得。此时此刻听曾布发问,他一连转过了好几个念头,最后才下定了决心。
“曾大人,此人正是在逃的顾焕章长子顾南。”高俅刻意压低了声音,几乎是紧贴曾布耳畔说道,“此事可大可小,便看大人如何处置,若是处置得当,这一次的辽国密谍案便能圆满结束,否则留了个尾巴恐怕会遭人诟病。”
曾布先是脸色一变,随即露出了一丝了然的笑容,随手招来一个随从吩咐了几句,这才神情自若地发话道:“此地出了命案,看来今日纵是想尽兴也不可能了。我已经着人通知了开封府,应该很快就会有人赶到。”
这些官员也都是官场中的人精,此情此景下哪里还有不知情识趣的道理,纷纷脚底抹油溜之大吉。这个时候,楼中其他人也颇有几分见势不妙,三三两两的便有人从侧门开溜,曾布却好像没看见似的毫不阻拦。待到阮大猷带着左右军巡使匆匆赶来时,入云阁中已经人影寥寥,只有一干姑娘在一边瑟瑟发抖。
向曾布点明了之后,高俅只觉心中格外轻松,此刻即便见到大批兵卒涌入,他也懒得搭理,干脆凭栏望起了无边春色←的目光扫过了底下那一大群姿色各异的女子,环肥燕瘦各具美态,媚骨天生却掩不住那股发自内心的自卑,只有角落中那个冷若冰霜的女子不在其中。只是一次目光对视,他便认出了那个花国之中的后起之秀,情知她定是含章无疑。
“含章姐姐,你在看什么?”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见含章目不转睛地望着楼上,不由很是不解地问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听说枢使曾大人就在楼上,你何不上去求求情?”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才懒得做那些无聊的事。”含章随口答了一句,目光却仍然专注地盯着楼上的高俅,许久,她那犹如寒霜一般的脸突然完全解冻,露出了一个犹如鲜花绽放般甜美的笑容。
城郊的一处庄园中,萧芷因听着下属的奏报,眉头不由紧皱,脸上怒色愈来愈浓。
“顾府被抄,章惇曾布争功,看来事情还真是越来越复杂了。若不是我正好离开,这一次岂不是要被宋人连锅端了?”他冷笑一声,这才低头望着两名下属。
阶下的两人乃是货真价实的契丹人,在大宋居住多年,无论身份忠心都相当可靠,他们俩才是萧芷因真正倚为柱石的心腹。此时此刻,两人对视一眼,左手的那人便出言道:“大人,顾焕章可是认识您的人,若是他扛不住严刑拷打,届时定会供出始末,待到那时便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是不是要不计代价将其”
“用不着!”萧芷因傲然一笑,流露出一种深深的自信,“作了顾焕章将近两年的便宜儿子,这个人我清楚得很,老奸巨滑爱惜钱财而又贪生怕死,,决计不会让自己陷入那种受刑的窘境←犯的乃是叛国重罪,若是被捕,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自绝!”
“可是据属下得来的消息,顾焕章乃是被人架走的,生死不知。”右手的汉子仍旧不放心,要知道,萧芷因身份贵重,绝对不能出半点闪失。“为了稳妥起见,属下已经派人将那名替身杀了,也好断了他人追查大人的路子。”
萧芷因点了点头,面上并无任何不忍的痕迹:“那家伙成天顶着我的名头在外花天酒地,全然忘了那么多钱就是为了买他那条命,你们做得很好,这种人死不足惜!”
第二十三章 美人高人
阮大猷得了曾布面授机宜,立刻先按着自杀的条例命人收殓了尸体,又招来入云阁的一群人恐吓了一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说能够把自己撇清出去,那老鸨当即赌咒发誓绝不在外胡说八道,曾布这才和阮大猷一同离去。
眼看四周无事,楼中各处也是一片冷清,高俅招来两个随从便欲起身离开,就在此时,楼梯上响起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不一会儿,那个体态肥硕的老鸨便气喘吁吁地奔了上来,来不及喘一口气便满脸堆笑地道:“高大官人请留步!”
“李妈妈还有什么事么?”高俅天生便厌憎这种女人,自然不会给什么好脸色,“今次我可是没给你使什么绊子,阮大人看样子也将以仇杀结案,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大官人这是哪里话,我感激还来不及,哪里还敢有什么不满?”那老鸨见高俅对曾布耳语了一阵,自己最担心的事情便迎刃而解,心里着实羡慕到了极点。那些大官她自知攀附不上,立刻打定了巴结奉承高俅的主意。“今日也没让几位大人尽兴,如今含章姑娘已经空了下来,大官人可有功夫去单独听听她弹琴么?”
“佳人相邀,我又怎会拒绝?”高俅颇感玩味地微微一笑便抬手示意道,“有劳李妈妈头前带路了!”
被那老鸨引入雅室时,高俅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含章脸上的寒意。此种情绪出现在一个倚栏卖笑的青楼女子脸上,登时让他有一种极为怪异的感觉。饶是如此,对方犹如清水芙蓉一般的美态仍然让他感到一阵惊艳,他甚至没有注意那老鸨悄悄退开,房门也被关得严严实实。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含章姑娘能够在短短数月间享誉汴京,果然名不虚传。”高俅施施然在含章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这才肆无忌惮地在对方浑身上下打量了起来,“不过姑娘的气质容貌与这这风尘之地格格不入,着实可惜了。”
含章初来汴京不过三个月,但早已经是看惯了无数恩客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丑恶嘴脸,因此刚刚在楼下时尽管似乎多注意了高俅一会,却不过是青楼女子常用的伎俩。此时听到高俅这般言语,她却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真姿态。“有什么可惜的,纵是傲雪腊梅也总有被人攀折的一天,又何况是身不由己的我?”
脱口而出后,她才发觉自己